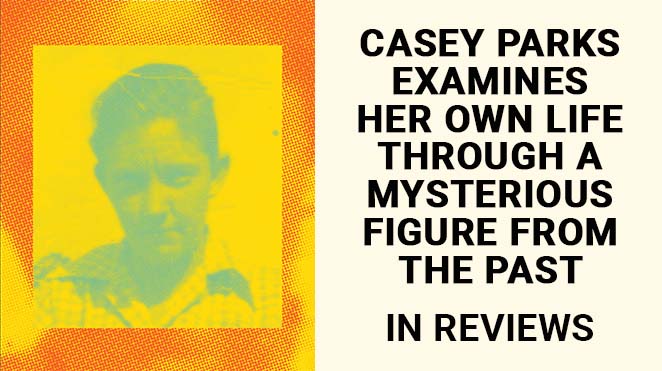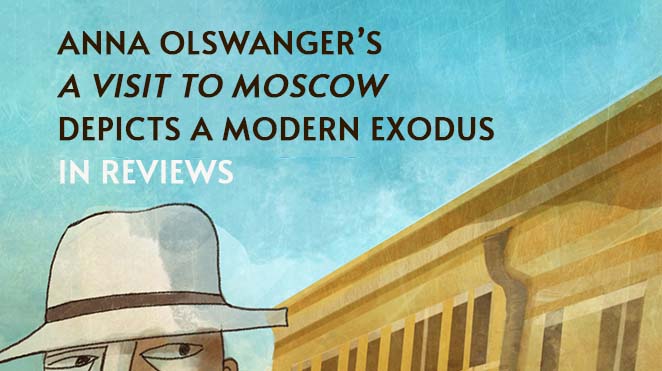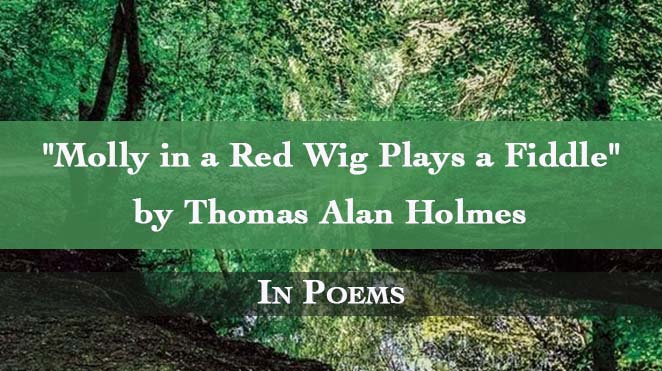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声称,反对民主的最佳论据是与普通选民进行五分钟的交谈。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哲学教授斯科特·f·艾金和罗伯特·b·塔利斯认为,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的。他们虽然承认目前专业人士和外行之间政治审议的糟糕状态,但他们坚持认为,适当的辩论对认知健康和民主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为什么争吵(以及应该如何争吵), Aikin和Talisse为富有成效的民主分歧设定了基本规则。
他们写道:“民主是我们根据理性管理认知生活的个人愿望的社会和政治表现。”当代民主的失败,可以追溯到我们没有能力适当地参与政治辩论。当代政治辩论沉浸在一大堆辩证的谬误中——其中大多数把反对派描绘成愚蠢、脱离现实,甚至更糟——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和扭曲,让民主妥协的果实在树上腐烂。Aikin和Talisse说,解决方案可以在合理的公众辩论中找到。只有针对我们对手的理由,而不是针对她自己的理由,并对这些理由给予适当的倾听,我们才能促进民主所依赖的互惠关系。
 艾肯和塔利斯最近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艾肯和塔利斯最近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你认为民主和理性的辩论是不可分割的。在民主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的人是一种责任吗?
Talisse字体这完全取决于“用心投票”的确切含义。你说得对,斯科特和我认为民主是理性的基本愿望的政治表现;简而言之,民主为追求我们的理性目标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我们最基本的目标是相信真实的东西,拒绝错误的东西。但事实证明,我们只有在一个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才能追求这个目标,这个环境使我们能够基于我们最好的理由去相信。为了让我们的信仰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访问到可靠的信息、数据和证据来源。此外,我们需要更多:我们需要理性地处理分歧;我们需要处理理性生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为了追求我们最基本的愿望,我们需要好好辩论。
在我们为什么争吵(以及应该如何争吵)斯科特和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社会,这样个人才能理性。但是,正如你的问题所揭示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可以以他们选择的几乎任何方式参与,甚至投票。因此,尽管民主社会使我们变得理性,但它也允许许多偏执、偏见和盲目的激情。但是,请注意盲目地多情不要把自己当作瞎子。他们把自己的激情用自己的理由来证明。
你提出的这类问题的一个有趣特点是,理性vs激情的关注通常来自于那些认为自己站在理性一边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谈论“用心投票”的人,往往是在谈论其他的人而不是自己。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在用头脑投票,而不是用心灵投票,至少不是盲目地我们的心。
现在来看第二点。我们需要民主才能变得理性,但这并不是说理性是冷漠的、冷静的、超然的、没有激情的。事实上,在我们为什么争吵(以及应该如何争吵)斯科特和我的研究表明,适当的争论可以是情绪化的、大声的、激烈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不礼貌的。也就是说,正确的论证不是这样的反对充满激情的承诺。所以,回答你的问题,那些根据自己的心投票的人并没有责任。其责任在于以一种对理由和争论不敏感的方式投票——一个人可以表现出大量冷静、冷静的理性,同时仍然非理性地固执。对民主的真正威胁来自于那些无视其政治对手提出的理由和论点的人,那些自以为是和独断专行的人,那些认为其政治对手是这样的人根据事实本身愚昧的愚蠢的、无知的、愚昧的或叛国的
米兰当前位置如果真正的民主在对立观点之间的辩证法中蓬勃发展,你如何解释政治妥协如此频繁地导致没有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中间地带这一事实?
Aikin例如,没有人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妥协肯定是糟糕的交易,这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中间事情的结局并不总是这样。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辩证交流都必须遵循我们希望达成中间立场的思想。很有可能有一方完全错了,不得不撤离他们的整个阵地。辩证设置的重点是找出分歧双方有共识的地方,以及双方有什么可辩护的地方。当然,这不仅仅是评估你的对手的问题,还需要你以同样的批判性观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知道并诚实地知道什么是有充分支持的,什么是没有支持的。
我还认为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买家对妥协感到懊悔。事后看来,你总是会将妥协的结果与你希望的结果进行比较——也就是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当然,你会认为妥协,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不是好的结果。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比较集——你还需要考虑其他的选择。对比一下,对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而你什么都得不到。或者把它与完全没有妥协,什么都没有做比较。很明显,妥协不是第一选择,但考虑到其他选择,妥协是最好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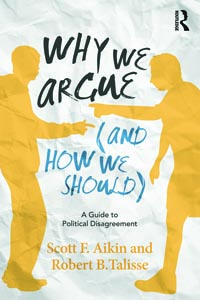 重要的是,好的论据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什么值得妥协,什么不值得妥协——它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对手和你的立场。糟糕的妥协现象往往是由于糟糕的争论而产生的。罗伯特和我一直很担心人们通常的想法:一个人的政治对手是恶毒的、可恨的、不可理喻的。当然,如果你对你的对手有这样的看法,你将无法与他们辩论,任何与他们妥协的想法都是糟糕的。但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人们的动机比纯粹的贪婪和毁灭国家的欲望更微妙。如果我们能和同胞们一起,从我们正在努力促进公共利益的想法开始(但我们对促进公共利益的方法有分歧),那么我们的妥协将开始看起来更合适。
重要的是,好的论据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什么值得妥协,什么不值得妥协——它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对手和你的立场。糟糕的妥协现象往往是由于糟糕的争论而产生的。罗伯特和我一直很担心人们通常的想法:一个人的政治对手是恶毒的、可恨的、不可理喻的。当然,如果你对你的对手有这样的看法,你将无法与他们辩论,任何与他们妥协的想法都是糟糕的。但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人们的动机比纯粹的贪婪和毁灭国家的欲望更微妙。如果我们能和同胞们一起,从我们正在努力促进公共利益的想法开始(但我们对促进公共利益的方法有分歧),那么我们的妥协将开始看起来更合适。
米兰字体你显然认为两极分化会导致错误的观点。但我想知道,一个观点极端的群体是否可能在辩论中负责任?
Talisse字体这里有一个区别。“极化”有两种含义。有时,我们用“极化”来表示对立双方之间的距离太大,以至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点,因此没有妥协甚至对话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无疑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政府的僵局和瘫痪。但这个词还有另一种含义,这是斯科特和我最感兴趣的。有一个被充分研究和记录的现象叫做“群体极化”。在这个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并不能描述一个人的信仰和她的对手的信仰之间的智力距离;相反,它描述了个人信仰的方式变化或转变当一个人只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时。
想法很简单:假设安通常支持堕胎,但认为需要一些严格的法律法规来限制18岁以下的女性堕胎。如果安花几天时间只和那些支持堕胎的人谈论她对堕胎的看法,可以预见的是,她的立场将开始转变,不知不觉地转向安,转向一个认识到不需要那些法律限制的人。整个提倡各种赞成堕胎观点的群体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只在自己之间讨论,这个群体的中间观点将转向更极端的赞成堕胎的观点;它“两极分化”的意思是走向最极端的版本种类从视图开始。这种现象在各个政治派别都有发现,而且教育、财富、性别和地理的差异似乎并不影响这种倾向。群体极化现象的关键特征是信念的转变不由理由和争论引起的;相反,这种两极分化只是由群体动态推动的。和这是令人担忧的特性。
你当然是正确的,那些持有可能被视为“极端”观点的人可能是有争议的美德;事实上,极端的观点甚至可以正确的!再一次,两极分化的担忧涉及到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教训是,那些把自己隔离起来,不必考虑反对意见的人失去控制超过他们自己的思想。斯科特和我有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当你不知道真相的时候,论证和推理都很好。但是一旦你知道了真相,和那些你不同意的人交谈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真相,而那些不同意的人只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还要费心和他们说话呢?”群体极化现象表明这种思想是深刻的、悲剧性的错误。使自己远离反对意见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失去真相。
米兰当前位置民主革命——例如,在法国和美国,以及最近在罗马尼亚和尼泊尔——本质上似乎必然是极端主义的,要求全盘否定对方的价值观,而不是辩证的方法。在你看来,革命实际上是与理性民主对立的吗?
Talisse有很多要说的,但简短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在没有民主,或只有名存实亡的民主的情况下,革命才是正当的。只有当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推翻专制政权,而且是建立民主统治时,革命才是正当的。列举支持历史上伟大民主革命的理由,是为了表明民主的缺失和建立民主的必要性。
当然,现在革命者之间有很多关于“民主”的谈话只是这是出了名的困难,尤其是在短期内,要确定任何一场革命是否实际上是正当的。同样,要区分一个民主社会是什么也是困难的民主严重失败一个号称民主的专制社会。同样,反对暴君的革命是正当的。然而,当他们的民主社会处于民主状态时,公民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使之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严重的失败民主是复杂而困难的——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这些问题上阅读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等人的作品。
但如果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民主起义反对残暴的独裁者,你说革命是正确的为前提对现行政权的价值观的公然拒绝。斯科特和我都赞同这一点。我们的观点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在美国,我们必须与政治对手进行辩论。这是在假定,我们的对手是我们的民主公民同胞,我们可能与他们存在深刻分歧,但他们对基本民主和宪政秩序有着共同的基本承诺。斯科特和我看到的担忧——这是我们写作的动机之一我们为什么争吵(以及应该如何争吵)——我们当前的政治气候鼓励公民蔑视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
这种想法似乎是,理性和负责任的政治分歧是不可能的,因为可能只有一种理性和负责任的政治观点。只要看一下流行政治评论书籍的标题就能知道这个故事:自由主义是一种精神障碍;共和党的噪音机器;如果民主党人有脑子,他们就会是共和党人;共和党对科学的战争;等等。在流行的政治话语中,常见的信息是,那些不同意你观点的人因此是愚蠢的、盲目的,甚至更糟。这是一种危险的、严重反民主的信息。然而,它是数十亿美元的大众政治评论产业的统一命脉。
米兰你想对社会上那些厌倦了政治的人说些什么?我听到他们说,生命是短暂的,他们不想把它花在玩别人操纵的游戏上。
Aikin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经常感到不安。关注政治,尤其是关注过多的修辞、spin和普遍的仇恨,是令人疲惫和悲伤的。罗伯特和我经常对我们当前的政治话语状态感到绝望,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是,我们可以放弃关注,让一切都去死吧。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诱惑正是基于我们所主张的那种思想——好的政治是关于理性的公平交换,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因此,当我们对游戏被操纵的事实感到绝望,并试图放弃的时候,这就证明了罗伯特和我一直主张的观点(政治应该适当运行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做得不好。因此,我们对政治实践的共同沮丧,表明了政治的深层理性规范。每个愤世嫉俗者都有一颗理想主义者的心。
第二,注意到一些关于背弃政治、无视政治、任其发展的诱惑。只有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能现实地采取这种态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讨论的结果将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是好是坏。如果有人可以这样说:我不关心政治,因为这是一个被操纵的游戏;我不再注意了,这个人有特权不受讨论的后果的影响。你怎么能得到这种特权?简短的回答是:通过让游戏更多地向有利于你的方向倾斜。结果,由于政治讨论以一种丑陋的方式进行,所以对其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一种操纵和不公正制度的共谋形式。
所以,是的,无论如何,人们应该体验丑陋的政治交流的恶心,并感受到结账的诱惑。那说明心智健康。但重要的是要克服这种诱惑,让人们离开,保持联系,让讨论继续下去,对正义保持警惕。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民主就是工作。
米兰△您承认您的观点经常受到象牙塔naiveté的指责,但您也清楚地认为,即使在理性的民主国家,人们也必须亲自动手。你会如何用正确的论证方式来教育美国民众?
Talisse当前位置确实,我们经常被指控为naiveté与众不同的学者。但这种指控让我们困惑。我们对推理在我们认知生活中的地位的描述几乎完全来自于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做了.斯科特和我都认为好好辩论很重要,我们也都这么认为因为人们表现得好像他们认为这很重要.
如今,几乎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在讨论/辩论论坛上呈现的。这是为什么呢?斯科特和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了解人们持有的政治立场背后的原因很重要,了解不同观点的支持者如何回应批评也很重要。我们的总统竞选是由辩论推动的。为什么?斯科特和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推理很重要。我们的新闻媒体总是在用夸赞理性的认知美德的词语来描述自己无旋转区;公平;平衡;坦率的谈话;信任;清洁度;独立;等等。
为什么所有这些都吸引了与理性相关的熟悉的认知美德?因为原因、证据、辩论和论证不仅仅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善于辩论是认知存在的一个目标。因此,重要的是,在我们为什么争吵(以及应该如何争吵)斯科特和我喜欢不设法把一些高雅而贫乏的论证模式强加到普通人的日常对话中。我们不是讲课人们是这样争论的。相反,我们向我们的读者展示他们已经认可的论点的概念然后试图揭示,我们在哪些方面,无法达到优秀论证的标准。
事实上,很多我们为什么争吵(以及应该如何争吵)致力于识别一系列的论证模仿小块的假冒难以区别于真实事物的推理。但这并不是一个实施学者对普通推理努力的标准。所以,斯科特和我从非学术的实践和对辩论的态度开始,从这些概念中引出正确的辩论,然后尝试检验我们在尝试实践它们时所遇到的危险。这在我们看来不像是象牙塔企业。
Aikin:让我继续履行我们在书中所作的承诺。我们都教逻辑课,也在学院之外做了很多实践,展示了我们所看重的辩论技巧。几乎每一个和我聊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开同一个玩笑:逻辑和政治?好运!但是,在开了这个玩笑之后,他们立即欢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问题是,我们是哲学教授,我们有解决问题的学术模式,那就是:写一本书,然后讨论这本书。现实情况是,我们国家对话的质量和基调都有一些令人沮丧的地方,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罗伯特和我认为人们渴望一个更好的模式。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接下来的内容是一个更好的讨论模式。
我们认为,教育是关键。要想很好地辩论,你不仅需要一些技巧,还需要知道很多事实。你必须具备科学素养,了解辩论的历史,熟悉对手的观点,并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缺陷。你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政府;你必须有文化素养。
这是很大的开销,我们认为导致好的话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文化的断裂。几乎没有共享的知识。事实上,这是一个反馈循环——文化越分裂,政治话语就越不和谐,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文化缩减。保守派和自由派不认为他们可以与对方对话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未真正尝试过。那是因为他们除了分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谈论的。因此,各方只不过是互相讽刺而已。其结果是,你对自己关心的问题的历史了解得越多,你就越能就政治问题进行辩论——你会了解政府机构及其角色,你会知道双方是如何改变主意、做出妥协的,你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观点。
标记:非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