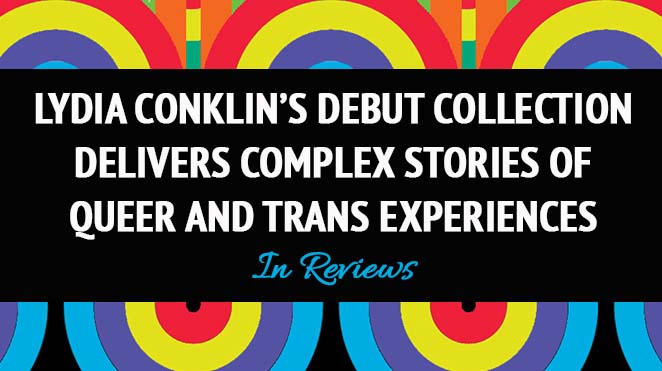每个星期,当米兰通讯在我的收件箱里,我总是很高兴看到熟悉的朋友在米罗区而且孟斐斯传票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三本小说由谢尔比富特在书架上的页面顶部。

没有人这样描写孟菲斯彼得•泰勒.他的短篇小说《达芙妮的情人》(Daphne’s Lover)的开头一段,每次读都让我兴奋不已:
我和我的朋友弗兰克·莱西(Frank Lacy) 13岁时,还穿着喇叭裤。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通往他在中央大道(Central Avenue)的家的水泥台阶上。我们在宽阔的楼梯中间歇脚,两边看守着一只比真人还大的水泥狮子,它是用比台阶更多的砾石混合物浇筑的。突然,弗兰克以一种上下起伏的声音脱口而出:“啊,文顿!啊,Goodbar !啊,哈伯特!”这是我的家人居住的孟菲斯老式的安南代尔区的街道名称,离时尚的中央大道只有几个街区。“多么高贵的老街道啊!多么高贵的名字!弗兰克说。当然,他是半开玩笑的。然而对弗兰克来说,我的社区有一种神秘的光环....
我在那些街道上长大。他们在我的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报童:
在我居住的孟菲斯地区,所有街道的名字都用漂亮的蓝色瓷砖镶嵌在每个角落的混凝土里。我知道所有的街道,但我喜欢每次走到一条时在脑海里念一下名字。文顿。哈伯特。卡尔。梅尔罗斯。Goodbar。博地能源。街道就像我的朋友,我不需要和他们说话。
我一想到孟菲斯就会想起我遇到的那个下午谢尔比富特.
20世纪70年代末,我和妻子住在靠近东公园路的门罗2200街区的一所小房子里。每天早上4点去上班孟菲斯Press-Scimitar下午1点左右送我回家。我偶尔会在下午散步,这样贝蒂下班回家时我就不会在打盹了。

有一条路要经过东公园路谢尔比·富特住的那些大房子。这是在90年代早期,由于PBS的肯·伯恩斯内战纪录片,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前。我正经过富特的房子,房子被大橡树掩藏着,这时我听到了一台割草机正在转动的声音。接下来,他又用优雅的南方腔调说了一连串的脏话,这让他的咒骂听起来几乎像贵族一样。富特转过街角,推着他那台没启动的割草机向车库走去,我认出了他。后来我看了肯·伯恩斯的采访,才知道富特的写作室就在车库楼上。
“有问题?”我问。即兴开始谈话不像我的风格,但看到这位著名作家给了我灵感。
“我不会开始的,”他说。“我对这些该死的玩意儿了解不多。”
“介意我看一下吗?”
“请自便,”他说。
我检查了一下有没有汽油。它做到了。我试着转动了几次,它似乎没有火花。“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取出火花塞吗?”
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修理厂,拿了把钳子回来。永远不要试图用钳子把火花塞拔下来,但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我掏出一块手帕,把插头的陶瓷部分包起来,开始把它取下来。
“我的院子里的人发现自己又被关了起来,”富特说。“我从来没有运气去做这些事情。”
地狱的装置.被监禁.这些都是作家的文字,只有富特的糖蜜般的表达才能恰如其分。他点燃了长管烟斗,坐在车库旁边的一堵矮矮的砖墙上。他的手指被墨水弄脏了。后来我还了解到,他大部分的写作都是用一根浸针完成的。
我终于拔下了插头,插头的尖端浸满了油和汽油。我用手帕的残渣擦了擦。“让我们看看现在能不能擦出火花来。”我说。我把火花塞的电线放在插头上,并把插头的尖端放在金属割草机外壳旁边。我让他慢慢地拉启动绳。我看到轻微的火花穿过缝隙跳到金属上。“这就是我们的火花,”我说。我把插头插回去,拧紧。割草机拉了十几下就开动了。
“所以,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火花,”他说。“我想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
他说他很乐意为我的麻烦付给我一些钱,但他不想关掉割草机回到里面去拿钱包。他让我晚点去,但我说我很高兴能帮上忙。我从来没有自我介绍过。我没告诉他他的内战系列在家里读了第一卷的一半。
十多年后,我从来没有错过过PBS的纪录片,主要是为了有机会听到富特优美的南方拖腔口音,带着三角洲的壮美。即使是现在,当我感到无所事事和懒惰时,我也会在YouTube上看几分钟谢尔比·富特(Shelby Foote)大谈内战的视频。
有时候,那小小的火花就是我所需要的。

版权所有(c) 2016由Vince Vawter。版权所有。在转向小说之前,孟菲斯人文斯Vawter当了四十年的报社记者。他和妻子住在田纳西州路易斯维尔大烟山山麓的一个小农场里。他的第一部小说,报童她被评为2014年纽伯瑞荣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