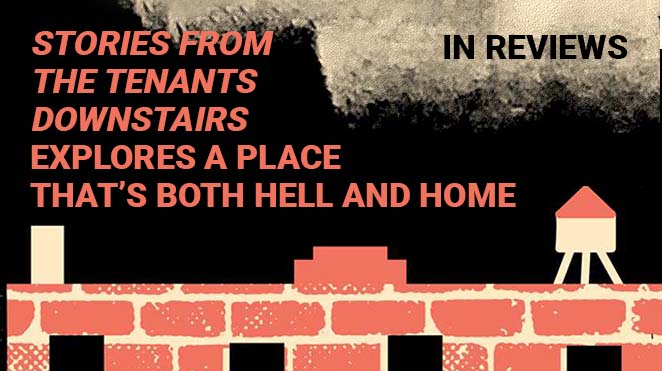我还在斋月期间倒时差,把脸埋在气垫里,抵御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光线。那是星期三,我在纳什维尔的第三天。我给远在拉合尔的母亲打了电话。
 通常当我们交谈时,木玛会躲到她的床上,远离我父亲电视上的激烈争吵和我哥哥扩音器的刺耳声音。但那天,由于开斋节,她接受了我在Facebook上的视频请求,并把所有人召集到客厅。当时是晚上,拉合尔正在下雨,网络连接很弱。像素化的家庭片段挤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没有实体的四肢、部分面部、牙齿上的口红、我姐姐用指甲花画的手、我父亲衰老的脸颊。
通常当我们交谈时,木玛会躲到她的床上,远离我父亲电视上的激烈争吵和我哥哥扩音器的刺耳声音。但那天,由于开斋节,她接受了我在Facebook上的视频请求,并把所有人召集到客厅。当时是晚上,拉合尔正在下雨,网络连接很弱。像素化的家庭片段挤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没有实体的四肢、部分面部、牙齿上的口红、我姐姐用指甲花画的手、我父亲衰老的脸颊。
“驼峰日快乐,”我说。
实际上,拉合尔的开斋节都不是。由于伊斯兰日历的特殊性,今年巴基斯坦的开斋节是在周四,我的家人还在为这个节日做准备。我的父亲和哥哥在谈话中离开,开车去了城外平原上的山羊市场,离节日还有几周。他们今年可能会养只羊,我母亲说,用传统的方式。她喜欢现代生活方式——不乱,不麻烦。她不停地说着无聊的后勤工作,家庭八卦,说管家回他的村子去了,一直拖着电话,直到我告诉她我要走了。
她没有说的是她想念我,她知道我不可能那么想念她,她责怪我在大学的四年里离开了她,责怪我变成了一个她有时都认不出来的人,责怪我回家待一年,好像要履行一些必要的职责,责怪我再次离开。我走之前她说的那些话。我们现在能讨论的只有:给客人做粉丝还是米布丁?冠军还是请客吃饭?哪家餐厅,什么颜色的衣服?
 挂断电话后,我决定穿上我的白色纱丽来纪念这个节日。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在城里谁也不认识。在母亲的建议下,我在网上找了一间可能会做开斋节祷告的清真寺,发现纳什维尔伊斯兰中心已经结束了祷告仪式。无论什么。反正我和教授的会议快迟到了。
挂断电话后,我决定穿上我的白色纱丽来纪念这个节日。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在城里谁也不认识。在母亲的建议下,我在网上找了一间可能会做开斋节祷告的清真寺,发现纳什维尔伊斯兰中心已经结束了祷告仪式。无论什么。反正我和教授的会议快迟到了。
我很担心我今天穿的衣服会被绿山的邻居们读到,于是我穿上了擦得锃亮的皮鞋,背着好市多(Costco)双肩包,戴上了太阳镜,试图消除任何可能被它察觉到的威胁。在我去公交车站的路上,几辆车放慢了速度,在我大步走过时徘徊。我希望我住的那条街上有人行道;我一次又一次地抚平我的克米兹。我练习让我的口音更像美国人,当我对公车司机说“早上好”的时候。
我上了公共汽车,在后面找到一个座位。几站后,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和一个男人上了车,坐在一起。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说“开斋节穆巴拉克!””。但他们还是挤在一起,窃窃私语。感觉过去了;我转而看着窗外。顾客们拿着手机,拖着脚步从煎饼储藏室出来,排成一条蜿蜒的队伍。我想,那最好是改变人生的煎饼。
会议结束后,回到我那一站,我坐错了车。当我意识到我的错误时,天已经开始下雨了。我在下一站下了车,确定了我的位置;不知怎么的,我来到了离纳什维尔伊斯兰中心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我不是特别虔诚,但这似乎是个征兆。我在蒙蒙细雨中撑着一把大伞一路前行。
“漂亮的裙子!有人从车里喊道。

纳什维尔的伊斯兰中心坐落在纳什维尔最时尚的社区之一——也因此成为了中产阶级社区——的商业中心。当我穿过12大道时,太阳出来了。男人们光着身子,只穿着莱卡短裤,跑在我前面。经过了华丽的公寓、复古的精品店、瑜伽馆、时髦的年轻酒吧、写着“我相信纳什维尔”(I BELIEVE IN NASHVILLE)和“让音乐不要战争”(MAKE MUSIC NOT WAR)的壁画,还有一个农贸市场,我来到了伊斯兰中心(Islamic Center)。该中心位于咖啡馆/酒吧旁边,是一个方形的平面,有一个高高的山墙屋顶。一颗小星星和一弯新月像风向标一样从楼顶高高挂起,不太令人信服地宣布了这座建筑的身份。它看起来更像一个谷仓。或一个教堂。
清真寺前矗立着许多招牌,其中最显眼的一块提到了这座建筑的名字,并说它建于1979年。这个社区那时是什么样子的?这栋建筑见证了街道因扩张而被拆除,房子卖给了商人,大业主清理了这片区域(没有混乱,没有麻烦),老邻居们被重新刷成了时髦的粉红色。老人们走了,新人们搬进来了。

大楼可能想知道,那个每天把手推车推到路边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加油站怎么了?即使在它自己的骨子里,它肯定也看到了它的教派的变化,从几乎纯粹的非裔美国人,到大量的移民信徒,说着奇怪而不和谐的语言。他们也是新来的,旁边是纹身的潮人,长发的音乐家,穿着莱卡短裤的男人。它可能会想,当它看到破坏者在夜里靠近它,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喷漆罐时,发生了什么?或者一只被屠宰的猪的内脏。或者一桶猪屎。或者一桶汽油。
这都是你编的。也许从来没有人故意破坏。我争辩说,也许这些只是警示语,所有这些标志:一个警告破坏者,一个威胁警察和监控摄像头,一个宣布禁止火器,一个恳求这是上帝的房子,上帝教导爱与和平。我从没在南方见过清真寺。我想知道,那天早些时候,当一个穆斯林孩子和家人一起走进屋里做开斋节祷告时,当她拼出这些标语时,她会作何感想。
在里面,等候区散发着潮湿胶合板的味道。地板是廉价的油毡。监控摄像头悬挂在屋顶上,就像稳稳的手枪。墙上贴满了更多的警告,还有更多关于祈祷和程序的陈腐告示,信仰宣言,《古兰经》的语录,清真屠夫和餐饮商的广告。大厅是锁着的。办公室都是锁着的。在巴基斯坦,清真寺总是开放的,一位伊玛目总是在这里,有时是老邻居坐在里面,有时是伊斯兰学校的男孩在读书或玩耍。我在散步时说服自己,中心一定会为开斋节做些什么。至少伊玛目还在。我从没在南方见过清真寺。
我走出中心。还能做什么呢?
外面,在12 South闪闪发光的店面橱窗前,又开始下雨了,我发现自己走到了清真寺旁边的咖啡店/酒吧。
下午两点的欢乐时光。牌子上写着。酒保是个留着胡子的白人,身上有纹身,还有个啤酒肚。我注意到他在打量我的衣服;他笑了。我询问了三种当地的啤酒,它们在欢乐时光卖二送一。
 “你去吗?他敷衍地看了一眼我的巴基斯坦身份证后,高兴地问道。“还是新来的?”
“你去吗?他敷衍地看了一眼我的巴基斯坦身份证后,高兴地问道。“还是新来的?”
“是的,三天前刚到这里。”我说着,把我的借记卡递给他。
“你觉得怎么样?”
“这很好。老实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是啊,变化太大了。大多数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感到惊讶。”他把啤酒递给我。“好吧,欢迎来到纳什维尔!”
“干杯。”我说,然后把我的啤酒放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我对与酒保的偶遇感到奇怪的高兴,几乎是沾沾自喜。也许我以为我已经模糊了他对我的界定。
易卜拉欣,被他对真主的奉献逼疯了,在山上屠杀了他的儿子伊斯梅尔。但当他摘下眼罩时,他看到血淋淋的双手下面,是一只公羊的食道。你被耍了,那只是个测试!安拉喜欢考验他所爱的人,他的方式是神秘的。正因为这个故事,每年的宰牲节,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会屠宰牲畜,把肉分给家人、朋友和有需要的人。
在咖啡馆/酒吧里,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就在我恢复日常生活节奏之前——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我和Muma视频聊天时忍住眼泪的母亲,她把儿子献给了这个无神的大世界。我试着想象宰牲节那天拉合尔的街道上,满是被屠宰动物的鲜血。
在空调的猛烈冲击下,我穿着白色的纱丽卡米兹,看着酒吧窗外纳什维尔的街道,沥青被雨淋得很软。
[本文原载于2019年3月1日。]
 版权所有(c): Hassaan Mirza保留所有权利。哈桑·米尔扎(Hassaan Mirza)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小说艺术硕士一年级学生。哈桑来自巴基斯坦拉合尔,毕业于鲍登学院,学习英语和汉语。他是《纽约时报》虚构和创造性非虚构类栏目的助理编辑纳什维尔审查.
版权所有(c): Hassaan Mirza保留所有权利。哈桑·米尔扎(Hassaan Mirza)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小说艺术硕士一年级学生。哈桑来自巴基斯坦拉合尔,毕业于鲍登学院,学习英语和汉语。他是《纽约时报》虚构和创造性非虚构类栏目的助理编辑纳什维尔审查.
标记: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