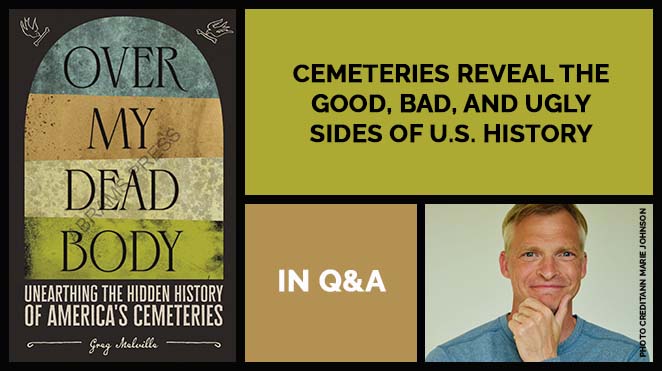粘土的上升《燃烧的国家:国王遇刺后的美国》这本书详细描述了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后肆虐美国城市的骚乱。《崛起》利用丰富的资料来源,包括第一手的回忆,描绘了一个不是在哀悼中团结起来,而是在愤怒和恐惧中分裂的国家。在对街头混乱时刻的描述的同时,还出人意料地深入了约翰逊的白宫,在对内乱的警告的同时,也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明显失败感到痛苦。他写道,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表明,骚乱是“许多趋势的暴力碰撞,微妙的和不那么微妙的,在国民心理中蔓延。”
骚乱发生时,瑞森还没有出生,但他对骚乱的兴趣既是个人的,也是职业的。他的母亲当时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办公室职员,随着暴力蔓延,许多普通人纷纷逃离这座城市,她也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在军队服役,被派去保护芝加哥郊外的一家军工厂不受暴徒的侵害。
 瑞森长期居住在纳什维尔,毕业于蒙哥马利·贝尔学院,曾在《华尔街日报》担任编辑新共和国.现在他住在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是执行主编民主:思想期刊.
瑞森长期居住在纳什维尔,毕业于蒙哥马利·贝尔学院,曾在《华尔街日报》担任编辑新共和国.现在他住在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是执行主编民主:思想期刊.
米兰:在这本书的介绍中,你谈到了你父母在骚乱中的经历。还有其他灵感吗?
上升:嗯,我是在芝加哥生活,在90年代生活在华盛顿,2003年之后生活,看到城市是如何迅速挤满了骚乱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乎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被重写的故事。我可以走出去,看到新的建筑拔地而起,而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那些体现了这些鲜活记忆的人,正在变老,离世。这一事件很可能会被忽略,人们只会模糊地知道:“是的,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出现了暴力反应,是的,有政治因素在其中,但我们真的没有太多记忆。”
米兰:你认为写与你有个人联系的历史有潜在的陷阱吗?
上升:我认为(我父母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自从我写了这本书,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说:“我曾在美国军队服役。我和你父亲的经历非常相似。”另一些人说,“我在华盛顿;我是成千上万试图逃离这座城市的人中的一员。”我的父母并不是在讲述我所继承的某种独特经历,而是让我接触到一个非常普遍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普遍的故事。
当然,过度个性化的故事,或者将其作为客观历史的基础,是有缺陷的。与此同时,我认为,只要你对自己所陈述的内容诚实,利用家族历史来探究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如果它以回忆录或个人历史或家族历史结束,你需要在开头说,“这是我写这个的原因;这是给我灵感的东西;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只要你直截了当,我不认为有很大的风险。
米兰:你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与你之前关于暴乱发生的想法不一致的地方?
上升:我当然有了一些想法,我的发现改变了它们,挑战了它们,但我认为这是任何历史作品的正常过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完全重新思考我在做什么。事实证明,白宫里发生的事情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有趣得多。我以为这将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故事,事实上,它与林登·约翰逊的个人悲剧密切相关——它发生在他决定退出竞选之后不久。他对马丁·路德·金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的看法——这一切都成为了故事中非常有趣的一部分,这是我没有真正预见到的。
米兰:约翰逊似乎将骚乱视为对个人的背叛,或对他所信仰的谴责,对此你感到惊讶吗?
上升:起初我很惊讶,但我对约翰逊了解得越多,这就完全说得通了。政治是他个人的事。他只是个政治动物;他没有另一面。大多数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但看到他的反应如此发自内心,令人惊讶。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在新政世界观、自由主义国家世界观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而他亲眼目睹了这种世界观在他的监督下分崩离析——不完全是这样,部分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很难不把这件事当成是针对他个人的。
米兰:他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导致了婚姻破裂?
上升:越南就是其中之一。我不认为他在种族关系方面犯了很多错误。他所犯的错误是认为只要给马丁·路德·金或其他一些领袖施加政治压力,他就能控制这场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可以帮助运动,运动当然也可以帮助他,但这不是一种可以控制的东西。
即使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或多或少平等的社会之后,比如说,北方的白人市长们也没有努力实现平等。
当更激进的年轻一代领导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60年代SNCC的领导人——出现时,他根本不理解他们。对他来说,这个运动不仅没有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发展,而且还在变形,我猜,在某种程度上,它在表达一些一直存在的东西。激进主义一直是民权运动的一个元素。甚至在民权运动之前,部分黑人争取平等的努力就带有激进的色彩。仅仅是在60年代中期,某些人和某些事件与媒体的关注相吻合,让人觉得,“哦,哇,以前没有武装分子的地方出现了武装分子。”
约翰逊一点也不明白,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不明白;但对他来说,我认为,他投入了如此多的努力,并相信他可以以某种方式塑造社会和美国政治舞台,看到这一切都分崩离析,看到这一切都落在他身上,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个人化。
米兰:你是否认为这些骚乱暴露了旧式自由主义在概念上的弱点,一种盲目?
上升:嗯,是也不是。我认为这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弱点。即使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或多或少平等的社会之后,比如说,北方的白人市长们也没有努力实现平等。像芝加哥市长戴利这样的人完全愿意让贫民窟成为贫民窟。我认为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创造的美国社会的一个功能,而且,不可避免的是,绝大多数住在贫民区的非裔美国人开始要求平等,开始要求快速的社会变革。当体制未能实现这一点时,他们开始以其他方式表达自己,比如骚乱。
监禁率急剧上升。人们找不到机会搬离市中心。我认为我们国家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
也就是说,我认为自由主义国家,因为它承诺要改变这些事情,所以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做不到。没有哪个系统能够如此迅速地实现变革。然而,自由主义国家说:“是的,我们可以。”那是一个白日梦。我认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一些研究过“大社会”的政治学家说,就内城项目而言,它只花费了实现其目标所需的1%。(自由派)承诺了很多,他们立法了很多,但他们没有兑现。所以他们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试图阻止的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旦发生,他们就会受到指责。
米兰:你认为这种夸张的期望现在正在产生吗?还是说我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
上升: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我认为,一方面,我们没有太大的变化。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仍然有相同数量的贫民区人口。在华盛顿,自1968年以来,在内城黑人的工作机会和受教育机会方面,我们一直停滞不前。监禁率急剧上升。人们找不到机会搬离市中心。我认为我们国家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我们成功地在贫民区周围建起了一道墙。我们成功地在它周围画了一条线,所以一个大都市的其他部分不依赖于它。它可以坐在那里,与社会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 A long as it’s policed and controlled—almost in a military style—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米兰:你认为我们对内城恶劣条件的容忍,以及对军事化警务的容忍,是由你在书中谈到的法律和秩序的反弹所促进的吗着火的国家?你认为白人公众被灌输了“我们会救你于水火之中”的观念吗那些人”?
 上升:我知道,我认为种族主义有点像水。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你试图把它推到一个地方,它会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它会找到新的表达方式。今天,吉姆·克劳的种族主义和城市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很难放在同一句话里谈论。它们显然是相关的,有相同的历史根源,但它们的表达方式是如此不同。今天,我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它变成了一个阶级问题,把它伪装成一个阶级问题。如果镇上有穷人区,那就是他们的的错。这不是体制的错。这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城镇的贫困地区也是黑色的城镇的一部分。这些都是相关的问题。不可能忽略其中一个,只看另一个。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上升:我知道,我认为种族主义有点像水。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你试图把它推到一个地方,它会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它会找到新的表达方式。今天,吉姆·克劳的种族主义和城市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很难放在同一句话里谈论。它们显然是相关的,有相同的历史根源,但它们的表达方式是如此不同。今天,我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它变成了一个阶级问题,把它伪装成一个阶级问题。如果镇上有穷人区,那就是他们的的错。这不是体制的错。这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城镇的贫困地区也是黑色的城镇的一部分。这些都是相关的问题。不可能忽略其中一个,只看另一个。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米兰:回到书中,如果你有机会和约翰逊交谈,你会问他什么?
上升:如果我能和约翰逊谈谈,我想知道他认为马丁·路德·金的死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有说太多,除了陈词滥调。为什么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他就派助手们四处奔走,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立法方案,却在周末结束时变得沮丧,把整个计划扔进了垃圾堆?这是他对失败的承认吗?
米兰:有没有你试图采访的对象不想谈论那些日子?
上升:是的,尤其是那些晚上以某种方式在街上游荡的人。我找到了一些在报纸文章中发现的人,虽然有些人与我交谈,但大多数人都很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有人试图挖掘一个可能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的故事。当时在场的一些名人比尔·克林顿太忙了,他是乔治敦大学的大四学生,暴乱后是一名救援人员。但令我惊喜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抽出时间陪我。
米兰:当你在各地谈论这本书时,你是否发现黑人和白人对骚乱的看法往往不同?
上升:是的,在种族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尽管主要是在老一辈之间。一些白人批评我对白人工人阶级过于严厉,还有一些年长的黑人批评我把金死后的暴力诋毁为“骚乱”,而实际上这是一场“叛乱”或“革命”。我想受到双方的抨击证明我做了正确的事。
不过,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我遇到的大多是过去被称为“建制自由派”的观点:骚乱当然是犯罪活动,但他们表达了对一个声称为内城穷人服务、实际上却压制他们的体制的合理不满。我想说,这在自由派和保守派读者中都是正确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欣赏随后的右转。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把骚乱视为完全消极的现象。特别是在城市黑人读者中,他们对骚乱所产生的草根组织和积极分子精神表示赞赏。当然,他们对骚乱感到遗憾,但他们明白骚乱的结果是复杂的。
标记:非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