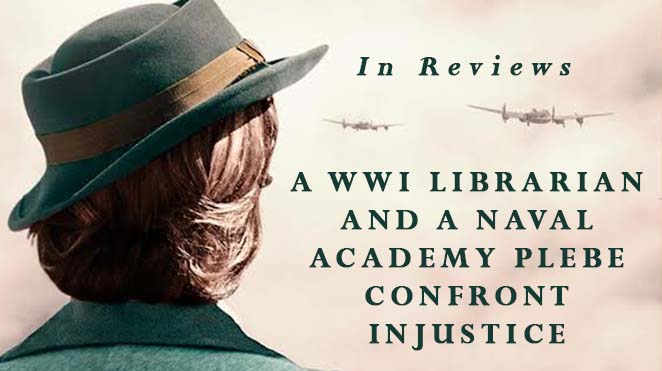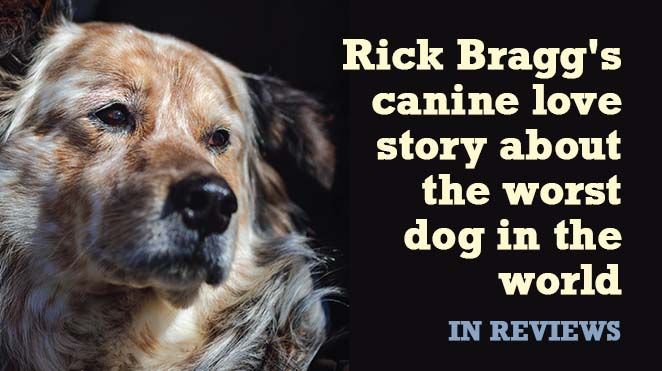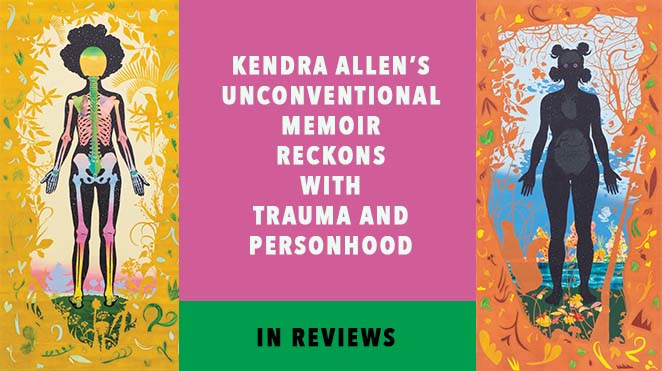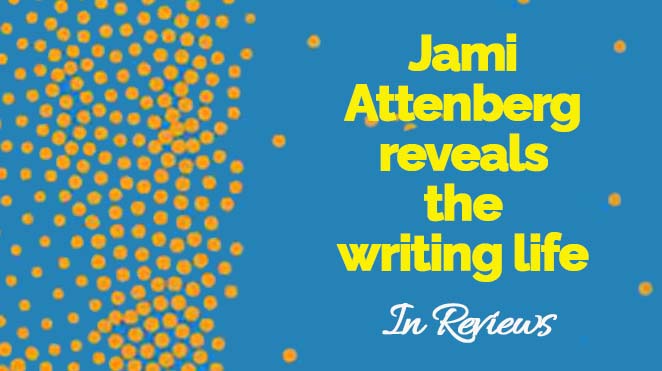李·史密斯有点像个替身。她的许多小说和短篇小说乍一看可能只是以迷人的南方特色为特征——阿巴拉契亚的风景和故事,把有时会变得暴躁的女士们组合在一起,以及礼节和欲望之间的冲突。这些传统的南方元素确实弥漫在史密斯的作品中,但就像任何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一样,她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材料的表面。史密斯笔下的人物也在纠结于他们混乱的内心世界。有时它们充满了悲怆;在另一些地方,它们闪烁着邪恶的幽默。这些冲突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展开,引起共鸣。史密斯创造的虚构世界可以将熟悉的世界重新塑造成新的东西,这些重新塑造的南方世界的叙事声音闪耀着同理心、精确和智慧的光芒。她的作品多如复杂,多视角小说口述历史而且魔鬼的梦想四部短篇小说集,包括她最近的一本书,达西太太和蓝眼睛的陌生人.

史密斯在维珍的煤矿小镇格伦迪长大,周围都是“真正会讲故事的人”
这是一种口头的传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呼应。除了小说作家的身份外,史密斯还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坐在法院的长凳上这本书是格兰迪的口述历史。)从霍林斯大学(Hollins University)毕业后,她做过报社记者和教师,包括在纳什维尔的哈珀斯霍尔学校(Harpeth Hall School)任教。她现在和她的丈夫,非虚构作家哈尔·克劳瑟一起生活和工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斯堡。
史密斯是南方作家协会和北卡罗莱纳州文学名人堂的成员,并获得了许多奖项,如罗伯特·佩恩·沃伦奖、托马斯·沃尔夫奖和弗吉尼亚州的终身文学成就奖。音乐被称为不错的女孩这部电影于2010年在百老汇外首映,部分取材于史密斯的故事。她的十三小说,地球上的客人,将于今年10月出版。
在2月21日现身孟菲斯大学之前,史密斯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字体在描述您毕生对故事的热爱时,您曾写道:“叙事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重要,就像空气一样重要。”随着这些年你的成长和改变,你与叙事的关系是否也发生了改变?具体来说,现在的故事对你有什么新的作用吗?也许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作家还没有发现的?
李史密斯叙事性仍然“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必要”,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也许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这就是我做.我想我写小说就像别人写日记一样。这一直是我记录我的生活的方式,也是我试图理解它的方式。我当然是不我笔下的人物——尽管他们经常会经历一些我在写那个故事时所经历的事情。当我读一个古老的故事时,我能准确地记得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处理什么——当我写它的时候。但我现在的故事和我以前的故事大不相同,就像我和写这些故事的年轻女子大不相同一样。
年轻作家的故事往往更像诗歌:他们直接取材于童年时期的伟大戏剧和创伤,追求强烈的强度。在我这个年纪,比起顿悟,我对“长期”更感兴趣。所以我后来的故事,比如我最近收藏的《House Tour》或《Stevie and Mama》(我最喜欢的!达西太太和蓝眼睛的陌生人都是关于长久的婚姻,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我年轻的时候不可能写出这些故事。现在,写故事通常是一种记忆而不是探索的方式。对我来说,时间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主题:衰老、期望与现实的差异、记忆的可靠性、历史的相关性....我比以前读了更多的历史书。
 米兰你的角色经常因为大量的变化而卷入冲突。有些人,比如奥拉·梅口述历史,是年龄较大的女性反思几十年来个人和文化的变化。还有一些年轻女孩,比如《火舌》(tongue of Fire)中的凯伦(Karen)和《无底洞》(Live Bottomless)中的珍妮(Jenny),被家庭和身份的剧变轰炸。虽然他们常常无法控制这些巨大的力量,但他们尽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是什么让处于巨大变化中的角色产生了如此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米兰你的角色经常因为大量的变化而卷入冲突。有些人,比如奥拉·梅口述历史,是年龄较大的女性反思几十年来个人和文化的变化。还有一些年轻女孩,比如《火舌》(tongue of Fire)中的凯伦(Karen)和《无底洞》(Live Bottomless)中的珍妮(Jenny),被家庭和身份的剧变轰炸。虽然他们常常无法控制这些巨大的力量,但他们尽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是什么让处于巨大变化中的角色产生了如此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史密斯字体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它直接触及了写小说的核心。我曾听伟大的作家多丽丝·贝茨(Doris Betts)在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上课时说,在她开始写故事或小说之前,她总是花很多时间思考她笔下的人物,想象他们的生活,“直到我知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然后,她说,“我写的是发生了不同事情的那一天的故事。”
想想看,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变化的可能性进入故事的世界,或者在一个人物的思想中(例如,他是一个失去信仰的牧师),或者在他的环境中(银行威胁要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者他意外获得一笔财富,或者他的女儿宣布独自怀孕,或者一个迷人的邻居刚刚请他帮她搬一些箱子,因为她搬到隔壁)。那天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小说中冲突重要性的最好的描述。事实上,冲突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所有类型的散文叙事的一个因素。我们有得到了它。冲突是抓住我们的读者,吸引他,让他不断翻书的元素;悬念取决于冲突。所以,是的,我的角色总是面临着变化——我试图抓住他们生命中的转折点,在这些转折点之后,一切都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米兰你是如何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创造声音的?
史密斯我生长在一个真正会讲故事的家庭。因为我对故事的第一感觉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所以故事总是以人的声音出现在我面前——不总是主角的声音,有时是故事本身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我耳边悄悄讲故事。特别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声音对我来说非常容易——也许太容易了。所以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必须确保这个声音有一些有效的东西要说。我也需要弄清楚情节,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不这样做,声音可能就会取而代之。
我对这些故事的理解有点像“方法表演”。
我写这些故事有点像“方法表演”——我称之为“预写”。我花了很多时间用铅笔和记事本,记下世界上关于我的叙述者的一切——他或她现在多大了?他在哪里长大的?他是个快乐的孩子吗?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发生在他身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的教育情况,经济状况,爱情生活如何?他想要现在是什么时候?最害怕的?爱最吗?最讨厌什么?他是宗教吗?政治吗?一直到这个叙述者,这个男孩或女孩,真的在我的脑海里走来走去,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那时——只有那时——我才会让他在我耳边低声讲故事。到那时,我的叙述者真的准备好说话了!我只能这么做才能跟上。 It’s like taking dictation.
米兰在你的文章《把黛西小姐逼疯;或者,《失去南方的思想》,你承认那些在南方文学传统元素中长大的南方作家——例如,古怪的亲戚,或者沉浸在历史和神话中的家乡——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自己材料的这些核心方面“可能已经过时了”。作为一个南方作家,你是如何战胜clichés的?
史密斯字体这是新作家或年轻作家——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样在传统的南方乡村或小镇长大的人——必须面对的最大困境之一。一方面,他们的写作老师告诉他们,“写出你所知道的”——这是一句老话,永远正确,因为你所知道的(你自己的真实生活)很可能是你能接触到的最真实、最引人注目的材料。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的经历已经被世界上许多最好的作家写过了,以至于你的生活细节在你开始之前就已经陈腐了,那该怎么办?
让我们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有抱负的年轻阿巴拉契亚作家,你的父亲真的在煤矿工作,你的祖母真的坐在门廊上吸着鼻烟或抽着烟斗,并想出了明智的格言,你的母亲真的会说方言,你的妹妹真的很乱,你的疯狂叔叔真的住在阁楼上——如果他真的有一只负鼠当宠物呢?由于媒体和以前的文学作品的影响,阿巴拉契亚的材料已经是一个刻板印象的雷区。刻板印象的问题在于,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往往是真实的。但如今,要把一个抽烟斗的老奶奶或一只宠物负鼠写进小说里而不受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刻板印象的问题在于,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往往是真实的。但如今,要把一个抽烟斗的老奶奶或一只宠物负鼠写进小说里而不受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的年轻作家如何才能写出他所知道的东西,并使其具有独创性呢?一种方法是使用有趣的语言或叙述的声音或创造性的讲故事的策略——这就是我在写我的小说时试图做的口述历史让多个说话者讲述小说的不同部分,相信读者能把它们拼凑起来。丹尼斯·贾尔迪纳经常在小说中做同样的事情风暴天堂而且不安宁的地球杰恩·安·菲利普斯(Jayne Ann Philips)最近也参加了云雀和白蚁.安·薄饼在她的小说中使用了极具创新性的语言这天气很奇怪这涉及到山顶移除采矿。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年轻的作家可以写一个话题,比如以前没有被广泛讨论过的山顶移除采矿,因为在阿巴拉契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每分钟都有一个新的故事。如今,许多关于环境和毒品的新故事都出自阿巴拉契亚,这两个紧迫的问题近年来由罗恩·拉什(Ron Rash)和塞拉斯·豪斯(Silas House)等人出色地解决。我们总是可以创造新的东西,但这需要仔细观察、一些思考和独创性。
米兰:你似乎擅长刻画具有强烈恶作剧意识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天生的特质还是来之不易的技能。你认为这个女人是南方的典型吗?或者你只是特别喜欢那些总是制造麻烦的角色?
史密斯我的角色比我勇敢。他们倾向于充满激情地生活——“全速前进”,这是我一直喜欢的老短语。他们总是做错误的决定,做我不会做的事情。但他们也经常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尽管他们往往比我敢于表达的更强烈。当然,他们总是有麻烦,通常是某种“女孩的麻烦”——我也喜欢这个古老的短语。所以,你是对的:尽管我写过各种不同的角色,但这个原型在我的作品中出现的次数可能比其他任何原型都多。她是“好女孩”——尽管她经历了生活中的一些艰难时期,但她仍然勇敢、诚实、有活力、努力工作、生活艰辛、爱艰辛,非常独立,但始终忠于她的家庭。(她爱她的孩子,她仍然叫她的祖母“Mamaw”。)这是你经常在乡村歌曲中听到的声音,比如(洛蕾塔·林恩的)“你不够女人(要带走我的男人)”。
 我爱这些女孩!事实上,我和三个好朋友合作了一个音乐剧,名字叫不错的女孩包括吉尔·麦考克尔和我自己的独白和小品,纳什维尔词曲作家马特拉卡·伯格(Matraca Berg)和马歇尔·查普曼(Marshall Chapman)的歌曲,所有这些都被剧作家保罗·弗格森(Paul Ferguson)塑造成戏剧。不错的女孩几年前在百老汇外演出,现在在全国其他剧院演出。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它将于8月18日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的易货剧院上映。
我爱这些女孩!事实上,我和三个好朋友合作了一个音乐剧,名字叫不错的女孩包括吉尔·麦考克尔和我自己的独白和小品,纳什维尔词曲作家马特拉卡·伯格(Matraca Berg)和马歇尔·查普曼(Marshall Chapman)的歌曲,所有这些都被剧作家保罗·弗格森(Paul Ferguson)塑造成戏剧。不错的女孩几年前在百老汇外演出,现在在全国其他剧院演出。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它将于8月18日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的易货剧院上映。
米兰你的第一部小说,狗灌木开花的最后一天,出版于45年前。你是如何长期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对新的创造性可能性的接受能力的?
史密斯:当然,我的角色也随着我一起变老了。我写了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版,狗灌木开花的最后一天那是我在霍林斯大学的毕业论文。它的主角是一个奇怪的、想象力过度的九岁小男孩——很像我小时候在弗吉尼亚州格伦迪长大的那个孩子,那时我的几个最好的想象中的朋友住在连翘花丛下,我和我的狗米茜经常去那里拜访他们——因此得名“狗丛”。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像九岁的孩子一样思考。现在,我的孙子们都比我大,我不能。
我已经用完了我的童年,就像我用完了我的大学经历和我大部分的成年生活一样。但幸运的是,成年人的生活也包括报纸报道和口述历史,这两个伟大的窗口打开别人的生活反正比我自己的要有趣得多。事实上,现在很少有作家能在书的封面上列出像丛林飞行员、大型动物猎人或脱衣舞女这样令人兴奋的事情。不,坦白地说,我们更多的是在编写程序中教学。我们有孩子;我们有账单要付。
所以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必须停止写我们知道的东西,这是他们在创意写作课上一直告诉我们要做的,而写我们能学到的东西,我们能想象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开始了解安妮·泰勒所暗示的巨大快乐,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写作时,她说:“我写作是为了拥有不止一个的生活。”我也做。让我告诉你们,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最大的荣幸。我一生都在写那些与我不同的人:家庭主妇和妓女,19世纪的学校教师,驯蛇者和女士布道者,乡村音乐歌手和美容师,例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在成长过程中认识的山上的许多年长妇女,她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总是很英勇。我过得很愉快。
米兰关于你即将出版的小说,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吗?地球上的客人?
史密斯:标题地球上的客人来自1940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给女儿斯科蒂的一封信:“疯子永远只是地球上的客人,永远的陌生人,他们带着他们看不懂的破碎的十诫。”当然,我们都只是“地球上的客人”——这部小说的背景设定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家著名的精神病院,旨在审视理智和精神错乱之间的细微差别。谁是“疯子”,谁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对女人和疯狂特别感兴趣,也对艺术和疯狂之间的共鸣特别感兴趣。从1936年到1948年,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在阿什维尔的高地医院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12年,作为一名精神病人,她和其他8名女性一起死于一场有史以来最灾难性的医院大火。她的尸体是通过她烧焦的芭蕾舞鞋辨认出来的,因为才华横溢却饱受困扰的塞尔达仍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舞蹈家、作家和视觉艺术家。在地球上的客人我为未解的火灾之谜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以及一组虚构和真实的人物,以及一系列导致悲剧的事件。我的叙述者是一个更年轻的病人,一个名叫埃瓦琳娜·杜桑的钢琴伴奏,她在小说的开头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我的故事,菲茨杰拉德先生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也不是尼克·卡罗维的故事——但尼克·卡罗维是叙述者,不是吗?任何故事最后都不总是叙述者的吗?”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2月20日。]
标记:非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