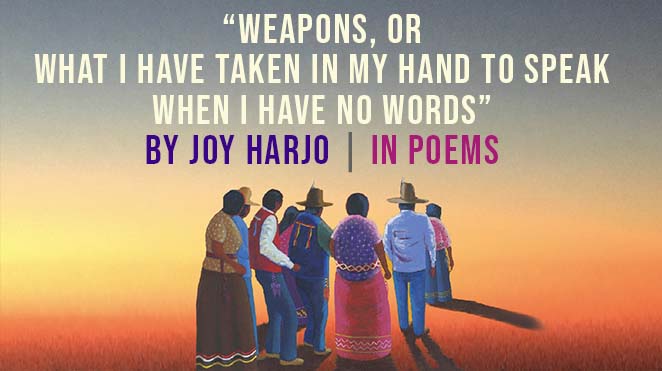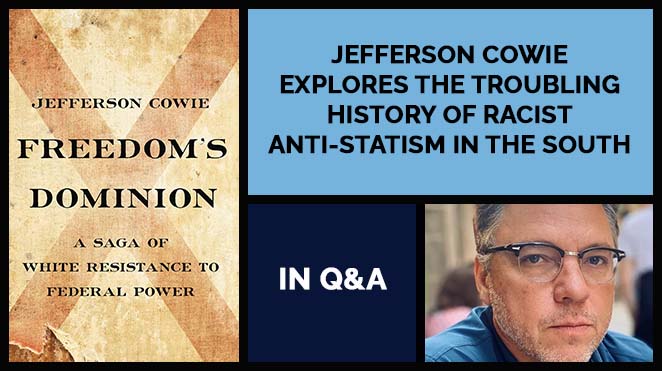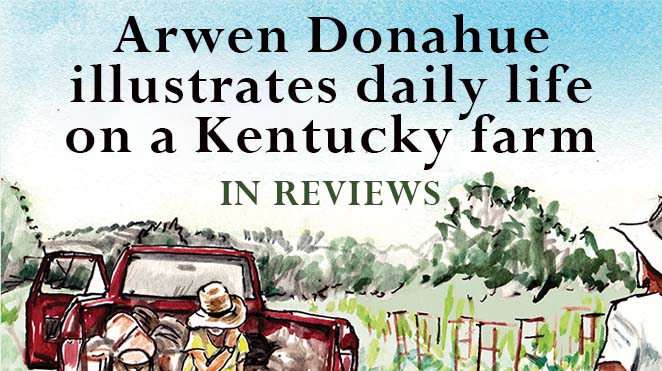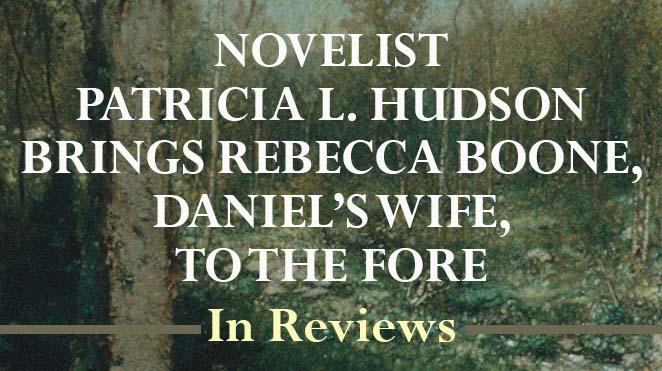夜里的某个时候,发电机的汽油用完了。醒来时的寒冷唤醒了我对乡下祖父母家冬天早晨的记忆。壁炉没能熬过夜晚。这是一种穿透寒冷、使人谦卑和困难的感觉。那种冷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可怜。

我在伊拉克摩苏尔住了六个星期,这间狭窄的小房间一直是我的家,只有我的军用手电照明。这是一种严酷而艰苦的生活,但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作为一名陆军飞行员的生活有一种方式可以消除对身体舒适度的担忧。我有我需要的东西:家里的朋友寄来的书和一张薄薄的、破旧的床垫,上面盖着很久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发给我的旧陆军毛毯。
***
我的伊拉克战争开始于第2-33中队,这是一个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值得信赖的机械师和20多岁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整齐的团体,他们接到了执行任务的通知。我们被征召去支援伊拉克西北部的联军。我们的任务是解救驻扎在“基韦斯特”(Key West)的一个部队。基韦斯特是一个古老的伊拉克喷气式战斗机基地的美国名字,听起来很有异国风味。这些空军飞行员把他们在这漫长的一年里学到的一切都教给了我们。他们无法让我们理解的是,即将到来的一年,喜悦、兴奋、恐惧和悲伤的幽灵将造访我们——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高空走钢丝,你必须亲自体验。
我被派到一个为摩苏尔陆军总部服务的双舰支队,摩苏尔位于基韦斯特以北约30英里处。在那里的任务很早就开始了,通常在黎明之前,一直持续到异常漆黑的夜晚,飞过伊拉克北部贫瘠的荒地沙漠。我们从叙利亚边境飞往伊朗边境,运送部队,疏散伤员,递送邮件和物资。有时我们载着政治明星,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直升机后座上的样子有多不协调,他们穿着借来的防弹衣,戴着超大的头盔,脚上穿着昂贵的意大利乐福鞋,戴着一副俏皮的太阳镜。
保护我们营地的是101支队的伞兵。作为一种禁卫军,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许多人来自美国社会的底层,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军队的自力更生生活是为了做得更好。大家都明白,他们会做需要做的事情,那些与美国政策相关的繁重工作。这是一项混乱而又残酷的工作。他们是我们手下最勇敢的人。我们一起住在巴格达北部由萨达姆总统府改建的军营里。
***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在这里很难让你的大脑安静下来,所以很难入睡。随着黎明到来的是例行公事:起床,穿衣服,然后飞……很多。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有着直接的期望——飞行每一个任务,每一天,每一天。没有人会说不。外面弥漫着战场上陆军生活的柴油和帆布气味,我看到我的飞机正在加油,机械师正在修理正确的发动机。清晨的炮击产生的浓烟顽固地悬在空中,一种苦涩、刺鼻的气味证明这次部署不是一次训练演习。枪手们用难以打开的棕色塑料袋吃早餐。他们不拘小节,毫不费力,几乎随意,工作效率很高。我很高兴他们站在我们这边。 This was one of those mornings when I recognized how far I was from home and how long I was going to be out here.

当天一份简要介绍我们任务的简报开始了。在过去23年的军事飞行生涯中,我在世界各地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现在坐在我熟悉的驾驶舱里,感觉这一天并不会是糟糕的一天。在早晨的出击之后,寒冷黑暗的黎明被令人愉快的初冬曙光所取代。我坐在蓝天下的地上吃午饭。圣诞节快到了,假期过后我们就可以说下个圣诞节我们就回家了。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最后一次有快乐的想法。
当我的船员们在冲刺中绕过拐角时,他们的表情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就说明了这一点。食堂发生了大爆炸,需要我们疏散伤员现在.我跑到停机坪,拉上我的飞行装备,启动引擎,机组人员蜂拥而至。升空后,以最快的速度飞行,在屋顶高度的城市上空呼啸而过,我们瞬间就进入了现场。我们的收音机里不停地播放着袭击的细节……还有关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消息....
***
走近摩苏尔的临时医院,我可以看到炸弹袭击者的工作成果。帐篷被撕碎得很厉害。医护人员照料伤员;另一些人则准备了那些厚厚的灰色袋子,以便日后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当有人挥手让我们进去时,我的船员们不顾危险,跳出来帮忙,因为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这几乎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时间放缓。医护人员似乎很匆忙,但把躺在起落架旁担架上面色苍白的男子抬上飞机花了太长时间。子弹在我们周围弹来弹去,但不知怎么的,我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被击中。坐在驾驶舱里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我祈祷他们快点,免得我们的攻击者走运。我抑制住了自我保护的冲动,做了别人对我的期望,等待着。最后,医护人员猛地打开货舱门,把一名伊拉克男子放了下来。他瘦削、布满皱纹的脸暴露出他熟悉战争和苦难的生活。喊着指令“把他带到巴拉德去!”——美国一家大型创伤医院的所在地——送我们上路。

我起飞,用力向右倾斜,向医院驶去。有足够的燃料以“最大功率全速”运输到巴拉德,这很重要,因为在严重受伤后的瞬间,速度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在一小时内跳过125英里。剩下的就交给上帝和外科医生了。
我在沙漠中疾驰而过,又低又快地紧贴着地面,直到远离城市。这防止了恐怖分子用廉价的外国仿制的美国导弹击落我们。然而,不久,一个新的威胁将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前方的高处,厚厚的灰尘正在形成风暴。
虽然有时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但伊拉克的天气对飞行来说其实是温和的。但当沙尘暴来临时,就很危险了。我们这一天的航行将会遇到由深褐色的沙尘和沙漠碎片组成的高耸、汹涌的石柱。摆在面前的是一项考验飞行技巧、勇气和勇气的艰巨考验。
我迅速爬到了3000英尺的高度,这似乎能让我们翻过山顶,但那只是幻觉。继续向上,很难判断能把这东西弄干净的高度。一开始我觉得五六千就够了。当高度计上的度数达到7000时,地面被遮住了。天空和地平线模糊了,我的世界坍塌在驾驶舱里,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仪器上。我向上飞翔,寻找一片空地,一个不会出现的避难所。到了一万英尺的高度,我觉得再高也没有意义了。我们被埋在这个高海拔的棕色迷宫里。没有无线电联系,也没有雷达。我们被孤立了。
在离巴拉德50英里的地方,湍流开始出现。我们的船在飞越沙漠中旋转的碎片时受到了严重的撞击。沙子冲击着挡风玻璃,机身在压力下剧烈震动。维持控制变得很困难。俯仰和翻滚会导致眩晕和定向障碍,这是一个潜在的致命组合。这是一场专注于脆弱工具的斗争。慢慢地,当我们继续向东南行驶时,暴风雨减弱了,我们开始瞥见棕榈树和下面的村庄。当塔台允许我们接近紧急医疗降落台时,安全着陆似乎开始成为可能。
***

战区的军队医院是令人伤感的地方。年轻、强壮的人,刚开始生活,就来这里等死。那些在战斗中严重残废的人,那些永远不会失去肢体或视力的人,来到这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忘记是不可能的。
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避开了风暴的余波,而着陆的地方则幸运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当我们的起落架伸出最后几英尺着陆时,艇长用“我宁愿幸运也不愿出色”的表情看着我。看上去很年轻的医护人员走近飞机,他们不知道我们克服了什么困难才来到这里。他们的工作经验、技能和效率来源于做了太多这样的事情。在轰鸣的引擎声中,他们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芭蕾舞般的手势和动作相互交流。我就知道时间太长了。当我们从暴风雨中走下来时,我心中的希望消失了。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带走?延误不是一个好迹象。慢慢地,他们飘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命运完成了任务。 A gurney appeared and two young soldiers unfolded one of those gray bags, and then the matter was callously concluded. It was just that simple.
尚未执行的任务要求我们消除这种悲剧。我们从平坦的沙漠平原上升起,在初冬的琥珀色微光中离开了巴拉德。太阳落在遥远的西方地平线上,把我们丢在一个没有灵魂的、漆黑的深渊里。牧羊人的营火在广阔的田野上摇曳着。越过山脊,我开始辨认出古代摩苏尔的灯火辉煌。我们在只有在遥远的沙漠才能看到的星空下静静地飞行。
***
在最后接近我们的基地时,支撑我这一天的肾上腺素消失了。现在想到了家。要过几个小时,也许几天,我才能联系上家人,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这是一个致命的行业。多年来,他们已经有了这种感觉。我们基地的通讯将被关闭,让军队有时间以传统方式通知阵亡士兵的家属。近亲不需要从网上得知真相。到明天早上,更多的美国人的生活将被永远改变。

地勤人员急不可耐地为第二天的直升机做准备,他们领着我进去。有微笑、拍背和拥抱,标志着我们与自己的人民愉快地交流。在这里,没人关心那个伊拉克人,他们只关心我们自己。我避免听取汇报,因为我知道事后会有时间让那些事后猜测的人来审视我。今天,我们做得太过分了,却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简单明了。
***
我们静静地独自完成任务后的例行程序,然后一个接一个走几米的路回到我们的营房,接受我们为清晨发射准备的任务。用手电研究图表,计算燃料需求,取货时间,以及我们明天要去的着陆区域,这让我继续前进。现在看来,322号任务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它留下的悲伤依然挥之不去。天气又冷了。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但一旦我睡了,我就会梦见更多的航班去巴拉德。

版权所有©2022迈克尔·伍德德。版权所有。迈克尔·伍达德出生在纳什维尔,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接受教育。最近,他结束了漫长的美国陆军医疗直升机飞行员生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完成了三次战斗任务。他和妻子特蕾莎住在肯塔基州的伊丽莎白镇。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