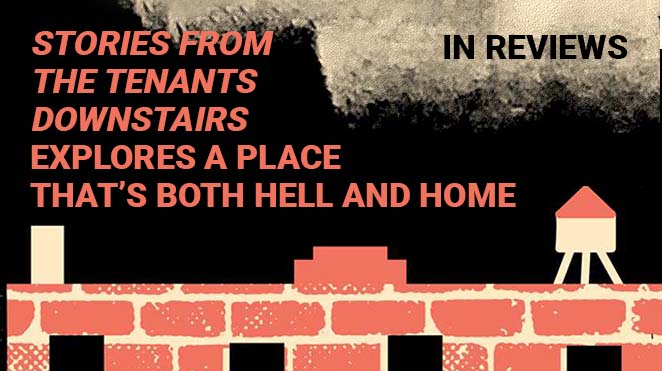仔细考虑威尔·坎贝尔的见证,就好比想象一个另类的现实:民权运动与乡村音乐产业融合在一起,宗教和政治之间流行的界限不复存在。作为一名词曲作者、小说家、牧师,以及为被监禁的、被边缘化的和不知道如何对待的人不懈倡导的人,坎贝尔挑战了所有的类别。我们今天看到的两极分化在他身上没有立足之地。
 作为马丁·路德·金、克里斯·克里斯多夫森和沃克·珀西的亲密伙伴,他代表了没有走的全党派道路——他是田纳西州的预言者,从市场、教会和国家利益冲突的缝隙中滑过。2013年,88岁的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去世,这一消息登上了《?》杂志的头版《纽约时报》.但到那时,这位曾被称为“乡下人中的阿奎那”的纳什维尔人已经不在大多数纳什维尔人的视线中了。
作为马丁·路德·金、克里斯·克里斯多夫森和沃克·珀西的亲密伙伴,他代表了没有走的全党派道路——他是田纳西州的预言者,从市场、教会和国家利益冲突的缝隙中滑过。2013年,88岁的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去世,这一消息登上了《?》杂志的头版《纽约时报》.但到那时,这位曾被称为“乡下人中的阿奎那”的纳什维尔人已经不在大多数纳什维尔人的视线中了。
作为与Will D. Campbell的对话在汤姆·罗尔德斯(Tom Royals)编辑的新书中,他指出,这是一个可悲的疏忽。威尔·坎贝尔以精确、幽默和深切的同情,讲述了推动我们新闻循环的灾难和矛盾。坎贝尔曾陪同学生穿过愤怒的暴民,努力整合小石城的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在60年代为自由乘车运动提供咨询和支持,在70年代为被监禁的三k党成员提供服务,在80年代作为厨师与韦伦·詹宁斯(Waylon Jennings)一起旅行,他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他对上帝和国家的爱以深刻的现实主义、希望和哀叹为特征:“我纳税。但我并不庆祝,”他在1984年说。“我为此感到懊悔。因此,在7月4日这一天,我敲响了钟声,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哀悼这个我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国家的耻辱历史。”
坎贝尔仍然是我们对民族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一旦你开始说,‘上帝使这个国家伟大’,那么你就可以为太阳底下的任何事情辩护,包括把人们的杂碎从他们的耳洞里吹出去,”他说。在坎贝尔看来,对这种疯狂行为的必要纠正是“至爱社区”,它是对既定的邪恶制度的一种活生生的替代。在坎贝尔看来,“教堂”是一个无限活跃的动词,以各种方式唤起人们的共鸣。
与Will D. Campbell的对话让我们一窥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包括他广受好评的回忆录)蜻蜓的哥哥他说:“我很久以前就发现,我们互相学习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允许的情况下,愿意尽可能多地展示自己,但这从来都不是很多。”“因此,我们没有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坎贝尔关于必须说你所看到的,坚持它,让事情顺其自然的洞察力——我们后来发现——是来之不易的。当管理人员抱怨他的激进主义时,他沉默而顺从地离开了密西西比大学的牧师职位,他后悔了。当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在纳什维尔的午餐处静坐中被捕,面临被范德比尔特神学院(Vanderbilt divine School)开除时,他最初倾向于听从院长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Nelson)的建议,悄悄退出,以避免制造麻烦。坎贝尔发现了一个更长远的游戏:“你不能让他们摆脱困境,”他建议道。“你必须离开,吉姆,但要让他们把你踢出去,这样他们和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机构的地位和目的。”按照坎贝尔的建议,劳森确实迫使范德比尔特采取了行动。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坎贝尔关于必须说你所看到的,坚持它,让事情顺其自然的洞察力——我们后来发现——是来之不易的。当管理人员抱怨他的激进主义时,他沉默而顺从地离开了密西西比大学的牧师职位,他后悔了。当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在纳什维尔的午餐处静坐中被捕,面临被范德比尔特神学院(Vanderbilt divine School)开除时,他最初倾向于听从院长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Nelson)的建议,悄悄退出,以避免制造麻烦。坎贝尔发现了一个更长远的游戏:“你不能让他们摆脱困境,”他建议道。“你必须离开,吉姆,但要让他们把你踢出去,这样他们和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机构的地位和目的。”按照坎贝尔的建议,劳森确实迫使范德比尔特采取了行动。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正如坎贝尔所见,在公共精神的运动和制度的静态顽固之间的这些澄清的交流是正义的突破发生的地方。在一次采访中,他讲述了黛安·纳什在纳什维尔市政厅的台阶上与市长本·韦斯特的对峙。当纳什问韦斯特是否认为设立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是正确的时,韦斯特回避了直接回答。“你认为它是基督教的吗?””她坚持。“不,我没有,”他最后承认。
坎贝尔认为,这一时刻是对公司机能失调的决定性打击,也是对人人都渴望的正直的邀请。乍一看,什么是“基督徒”,什么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会让人想起一个逝去的时代。但是,当政治人物通过宣传白人民族主义言论来赢得选举,同时宣称与地方教会有关系时,当这些教会没有明确说明他们的使命与政治上有权势的成员的使命在哪里一致或不一致时,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就是威尔·坎贝尔的证人尤为必要的地方。他担心没有具体化的信仰(或宣称的信仰)——没有耶稣的基督。“令我困扰的是,对信仰的强调会对门徒产生怎样的影响。它否定了门徒的身份,真的,”他说。“一旦我做了我想做的相信然后我就可以脱身了。”
对坎贝尔来说,“钩”永远是对日常细节中真实的人的真正的爱的工作。没有细节的信仰是死的。当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和为他们服务的民选官员似乎在躲避各种具体形式的攻击时,坎贝尔坚持不懈的优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大卫黑暗是《人生苦短,何必假装不信教,质疑一切的神圣性,每天的启示,《美国的福音.他住在纳什维尔,在田纳西女子监狱和贝尔蒙特大学任教。
大卫黑暗是《人生苦短,何必假装不信教,质疑一切的神圣性,每天的启示,《美国的福音.他住在纳什维尔,在田纳西女子监狱和贝尔蒙特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