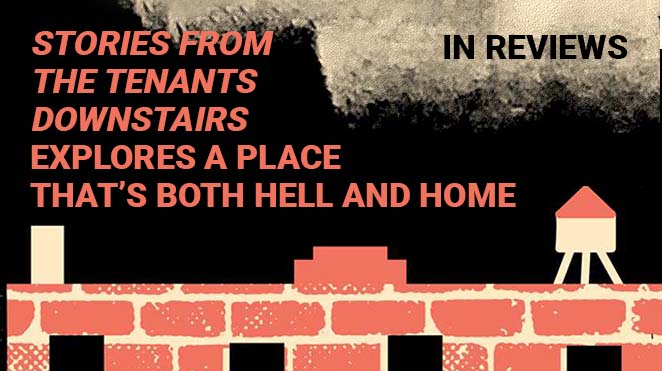“胡说八道!她说。“吸引他们的是书店。他们去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书店温暖、明亮、安全。他们安慰。如果我有精神疾病,被赶出了某个州立机构,我也会去书店。”
然后她补充说,“我相信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在店内举办活动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她无力地试图安慰我,结果反而加深了我长期以来的怀疑。我开始想象一个满是女人尖叫、拍照、向尼古拉斯·斯帕克斯扔内衣的商店。他们仔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喜欢他给他们的每一刻,让他们远离没有他的枯燥生活。如果这些粉丝可以被称为精神疾病,那也只是一种轻微的普遍疾病,是由于孤独而生的,或者更糟糕的是,嫁给了一个真正不了解她们的男人。
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为他的主人公们提供了安慰,因为他们总是遭受失去爱的痛苦,但在每本书的结尾都能找到更深、更丰富的爱和满足。谁不想相信,如果他们无私的丈夫或男友去世了,会有一个不仅倾听,而且关心的人,在一旁等待着更丰富、更美好的生活呢?
尽管我真的很想相信我的编辑,但她说的任何话都无法消除我内心的痛苦,她似乎在说,我被神经病挑出来接受特殊待遇。
也许她是对的,商店为破碎的群众提供了完美的培养皿。然而,事情似乎不止于此。毕竟,我曾经写过一个情感脆弱的女人,她重新埋葬了死者,并在她的后院建造了一个墓地。是关于南北战争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我不想吸引边缘人,我在想什么?
不,真相就在我面前,从我在当地书店的第一次活动开始,两个明显有问题的忠实读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了谁是最后一个见我而大吵一架,最后女人赢了。在一片混乱中,当工作人员把我从侧门领出去时,我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漫长的签售会。
他们似乎是凭空冒出来的。本应是普通的、普通的图书活动在世人面前变成了三环马戏团。最疯狂的人总是想排在最后,想吸引我的注意。要知道,我说的不是那些排着队告诉我他们的祖先参加过内战的普通人。他们都是很好的、可靠的人,只是热爱历史或“他们的人民”或“他们的人民”的历史。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不,我说的是其他人,那些给我“特别信息”的人。别人听不到的信息,只能悄悄的传递。当我在签名售书时,他们会走到我身后,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开始用方言祈祷。还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裸照摊开,提醒我大多数人最好穿上衣服。这么说吧,尼克·斯帕克斯拍的裸照肯定更好看。
有些人会在我为他们的书签名时和我握手,但不知何故,他们忘记了发行。他们跟着我到我的车那里,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些毫无意义的故事。他们经常说要把自己的生活抛在身后,和我一起旅行,或者拿着séance去找回我写过的死者。
死人——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死人。来自第六感没有我的把柄。也许他能看到他们的事实让他属于另一个联盟,但根据我的追随者,我身边到处都是死人。
第一次有人提到死者时——不久之后,似乎所有书店的活动都被他们挤走了——我开玩笑地回答说,很遗憾,他们中很少有人还在买书。我很快就学会了不要拿死人开玩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死者似乎从不容忍冒犯,或者即使他们有冒犯,也只对自己保密。不,只有那些活着的人,那些给我带来“特别信息”的人,他们似乎把幽默感放错了地方,把他们的思想放在了同一个地方。
不知怎的,当她抱怨尼克·斯帕克斯时,我意识到我的编辑没有理解。尼克·斯帕克斯(Nick Sparks)的问题(如果他有问题的话)无疑是由他的信徒的性欲引起的。我应该很幸运。那些应该体面地穿着衣服的人的裸体照片,不像我在他们的书上签名时,手里拿着一条不固定的内裤。也没有人留言让我在酒店的酒吧见面。就像我说的,我收到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死者。
话说回来,也许她是对的。也许是我把一切都炸毁了。毕竟,我是一个小说作家。重点是,我需要放松,享受那些花时间来参加商店活动、买我的书、用方言为我祈祷的人。
于是,我们前往上西区一家大型连锁店参加平装书的签售会。幸运的是,在那个社区里,应该有一大群去北方寻找财富的南方人,但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根。但话说回来,这里是纽约,这里应该有一群健康的不健康的人。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人群大约有60人,当然,其中有很多南方人。他们是11月份穿牛津布或格子法兰绒衬衫配卡其裤的人。他们的衣着和举止似乎都很得体。幸好我错了。我的编辑需要看到我能吸引一群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读者。
一旦开始,这一事件似乎就进行得很顺利。在店里做了这么多次,我睡觉都能做。就像观众面前的任何人一样,我满足了他们的美好祝愿,活动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我把它开放给问答环节。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他的头发是我见过的白人中最好的——一半牙买加人,一半杂耍——鲍勃举起了手。当我向他致谢时,他说他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问题要问我。他让我等他问完两个问题再回答。
从他开口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问题;这是一次暗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相信轮回。我站在那里等着他的下一枪,我已经麻木了。从人群的衣着来看,很明显房间里有不少猎鸭人,而我就是这家伙的鸭。
他问我是否在富兰克林战役中牺牲了。
我停顿了一下,直到他让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说,不,我不相信轮回。说着,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尖叫道:“好了,我想我们已经知道你对我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了,是不是?”
我点点头,然后转向观众,问他们对我的书是否还有其他问题。我的新朋友不容忽视。他仍然站在特别活动区中央,怒吼道:“如果我告诉你我是1968年4月24日在越南岘港被杀的,你会怎么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到死都会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不假思索地转过身来答道:“酷!”我知道这不是正确的回答,但有时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其他答案。
他尖叫着回道:“这可不酷,伙计!我流了四个多小时的血,最后把体内的每一盎司血都抽干了,然后死了。我记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冷,但剧痛最终导致了我的死亡。我以最高的荣誉被安葬在阿灵顿,而你只能说‘酷!’你是什么变态啊?”
在那一刻,我有机会采取高尚的方式,谦卑地道歉,但我没有。
我等他喘了口气,回答说,作为南方人,有一种独特的南方方式来使用“酷”这个词。我补充说,南方人经常用“酷”这个词来回应诸如“你母亲刚刚去世了!”或“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我尽量不去理会观众中那些南方人脸上困惑的表情。也许我的回答会奏效,我们就可以继续了。但是不,我的新朋友连这个都不打算给我,他生气地说:“我不相信你!”
现在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我和我死去的,转世的,患有精神疾病的朋友。我问在场的有多少南方人,大概有二十来个人胆怯地举起了手。我问他们,作为南方人,他们不是经常用“酷”来回应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吗?在那一刻,他们谁也不想待在那里。见鬼,我们都不想去那里。但我没有退缩,我要带着我的每一个南方同胞一起走。他们不情愿地加入了我的弥天大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赢了。我让那个疯子永远闭嘴了。胜利是甜蜜的。
现在,重新控制了房间,我问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还没来得及问问题,杂耍鲍勃就跳了起来,问他是否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不等对方同意,他就问:“你知道是谁杀了肯尼迪吗?”
我深吸一口气,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
他热切地问道:“谁?”
我屏住呼吸,打量着他说:“我不会告诉你的。”
活动结束了,书店的人领着他走了。我在书上签名,认真地听人们讲述他们参加南北战争的祖先。
我的编辑手里拿着大衣,静静地等着我。我们在感谢店员的帮助后离开了商店。我们在街上走着,她说:“我可能错了。也许你真的没有吸引尼克·斯帕克斯的观众。”
摘自集合:威廉森郡的作家,由CPO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c) Robert Hicks 2009。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