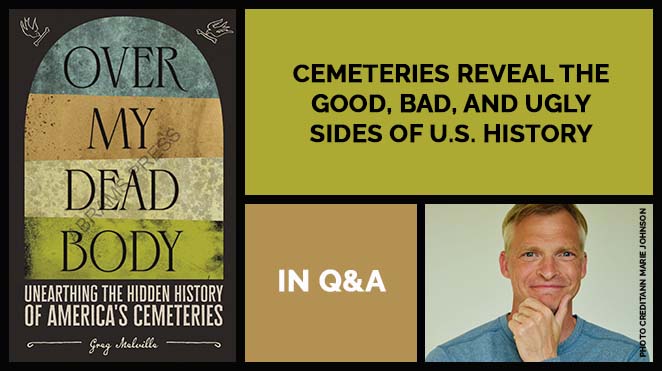一个15岁的女孩放学后和周末除了躲在卧室里跟着詹尼斯·乔普林的唱片尖叫,或者戏剧性地背T.S.艾略特的诗,草莓香的香味缭绕在空气中,还能做什么呢?
那是1972年,我的生活就像一片Kozmic Blues的荒地。我父母把全家流放到纳什维尔南部的一个农场;最近的镇上有一家米妮·珀尔炸鸡店,一家廉价商店,法院地下室还有一个灯光昏暗的图书馆。至少我在书的天鹅绒般的潮湿中有了家的感觉。我无拘无束的瑞恩神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是一所天主教高中,但仍然保持着一种不知悔改、不顾一切的氛围。女孩们穿着短裙格纹制服,我们给她们戴上摇摇晃晃的耳环、心情戒指和叮当作响的银手镯。为了向詹尼斯表示敬意,我在头发上炫耀粉红色的羽毛,但老师和校长却只字未提。
公立学校的通行证、尼龙长筒袜和没有蓝色牛仔裤让人震惊。啊,粉红的羽毛;哦,小女孩布鲁斯;啊,四月,最残酷的月份!如果不是我的生物老师卡鲁瑟斯夫人的话,我的人生将会陷入绝望的境地(当时我正进入生存阶段)。她穿着灰色的裙子和夹克,一整年都很健壮,她可以把青蛙拍到钢板上,然后津津有味地挥舞着手术刀解剖它。但到了四月,她扔掉了那件夹克,换上了一件白色衬衫,上面有花瓣状的褶边和珍珠纽扣。她的声音在冬天里很僵硬,就像她一闻到野洋葱的味道就把窗台抬高一样,当她回忆起青春期在树林里长途跋涉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
卡鲁瑟斯夫人给全班布置了一个似乎难以应付的任务:收集25个野花标本,根据它们的拉丁名和常用名称进行识别,压制,并将它们组合到一个笔记本上,如果更多,还会有额外的学分。她又加了一句告诫:漂亮而稀有的女士拖鞋(凤仙花下毛竹如果被发现,它必须不受打扰地留在它秘密的肥沃栖息地。即使是艾略特,他的紫丁香是在冬天的死寂之地培育出来的,还有他的风信子姑娘,也会引起他的兴趣。我拿着一本袖珍《田纳西野花野外指南》,离开了那间满是熏香、蜡烛和塔罗牌的封闭房间,跌跌撞撞地走进了40年前伊甸园的遗迹,那是我家65英亩农场的一部分。
迷路从来不是我的烦恼。一条长满草的小路在一片黑莓丛茂密的田野中蜿蜒而下,沿着一条峡谷向下延伸,一直延伸到谷仓附近。我散步时,家里的狗跟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路上有些地方像石头一样光滑。我不止一次迷路,发现了一个沼泽池塘,奇怪的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有一个五英尺高的墓碑,刻着一个树桩的形状,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我说到哪里了?我是否冒险进入了纳撒尼尔·霍桑阴暗的森林地带?谜题仍然存在:我一直不知道这块石头和它的主人是如何到达他们最后茂密的安息之地的。
我六岁的妹妹和母亲,正沉浸在路易斯和克拉克的三卷本历史中,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从纳什维尔搬来对我们三个人来说尤其艰难。按照达尔文的标准,我们适应能力差,在社会上被孤立,注定要灭绝,但我们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社区。
我姐姐擅长侦察四叶草。它们像魔法一样出现在她沾满泥土的手上,但她的运气用光了,而我和我们的母亲也有极限:女士的拖鞋,植物学家版本的传说中的独角兽,仍然是虚幻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带着天使般的白色花瓣和血色汁液的血根植物、延铃草、天坛杰克,还有我母亲最喜欢的荷兰人马裤:名不其名,白色和淡黄色的小花朵——更像维多利亚时代女士在微风吹拂时晾晒的裤子,而不是绅士的裤子——沿着弯曲的茎轴倒挂着跳舞。当我研究它们的命名法时,一本25磅重的韦氏词典把这些花压平了。詹尼斯保持沉默,T.S.在床底下无精打采。
在项目截止日期的前几天晚上,这些野花从它们隐藏的地方冒了出来,每一朵都被轻轻地压在薄纸之间,晾干。我用镊子和外科医生稳健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叶子、茎和花头粘在干净的白纸上。我回想起我发现许多花的确切地点。我知道在一棵巨大的老橡树下,野生鸢尾花在哪里盛开,我也知道血根花圃的秘密藏身之处。
我翻了翻《野外指南》,现在这本书已经折了角,又脏又脏,我要确定我的证件是正确的,然后用保鲜膜把纸角固定好,放进一个蓝色笔记本里。我的勤奋令我吃惊。我想,这让卡罗瑟斯太太大吃一惊。她的评价,做得很好这是她用清脆的小字体写的——我的心怦怦直跳。
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装订整齐的收藏,并为自己获得a++的成绩感到自豪。上次搬家之后,我就放手了。那些野花,还有许许多多野花,我都烂熟于心。
我以前就读的两所高中早就被拆除了,一所被汉普顿酒店取代,另一所被监狱取代。我的父母留在了县里,搬到了鸭子河上方岩石峭壁上的一所房子里。卡鲁瑟斯太太在楼梯上绊了一跤,粗鲁地赶走了一个学生伸出的手。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死的。
t·s·艾略特(T.S. Eliot)的文字和珍妮丝(Janis)的哀号让青少年被流放的迫切浪漫变得更容易忍受,而这种浪漫已经消失。我仍然在读艾略特的书,虽然没有那么紧张,但耳朵更敏锐了,理解也更深刻了。詹尼斯的声音在我听来仍然是挑衅的,尽管现在似乎也夹杂着失望,也许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尽管如此,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四月,最残酷的一个月,卡鲁瑟斯太太向我灌输了一种对森林的秘密和乐趣的终身热爱,以及幸福漫游的习惯。女士的拖鞋能永远躲着我吗?
版权所有(c) Anne Delana Reeves 2010。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