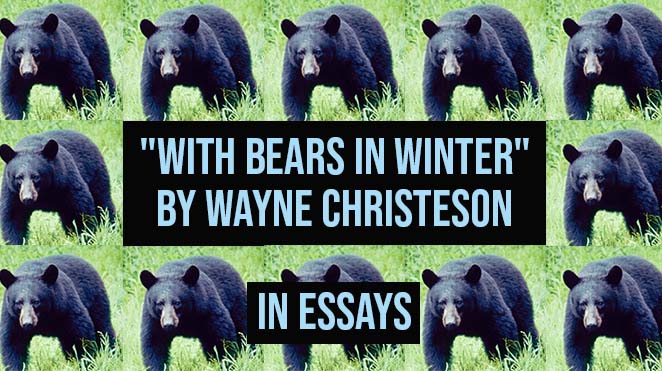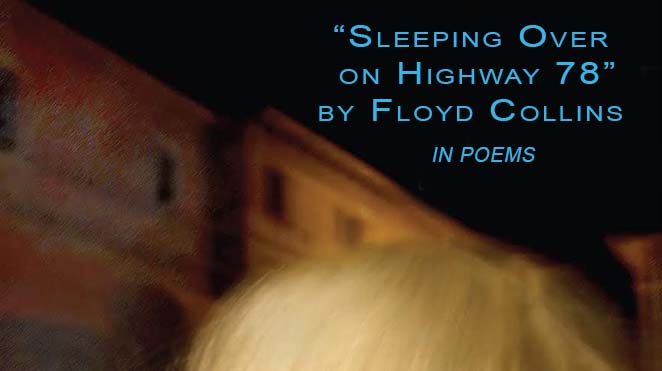从今天早上爸爸和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我就等着我们生锈的75年的LeMans抛锚。爸爸把他的工具箱放在后备箱里,旁边放着一壶咖啡,他的衬衫口袋里有硝基药丸。前座上放着妈妈给我们装了三明治的面包袋,下面放着一张破旧的AAA地图,接缝处又薄又毛茸茸的。我把替补乐队的唱片塞在一个装满衣服的黑色垃圾袋和后座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些记录。我没有东西可以玩。

我们正驱车前往密歇根州上半岛的大学城马奎特(Marquette),迎接我大一的开始,这是瓦戈家族历史上其他瓦戈家族从未做过的事情。开车的时候,每过一英里,我都感到更加羞愧。我父亲老了,我们很穷,而我才18岁,想在一个我从未熟悉过的地方重塑自己。我感觉就像独自坐在过山车上,不停地滴答、滴答、滴答,直到最高点,朝着第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大瀑布走去。
我们离城市越远,我越开始意识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白人垃圾,要去我只在爸爸和我之间的地图上指过的地方。学校肯定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然后把我送回底特律,直到我死。我们要去一个我这辈子一直被老师和附近的小混混们说不属于我的地方,在接下来的30年里,文斯的儿子和孙子都在8英里路的文斯派对商店里买两片薯条和一杯激浪(Mountain Dew)作为午餐。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来自这个地方,属于这个地方,我还不知道我永远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但就目前而言,笼罩在我家乡上空的下水道臭气已经过去了,爸爸继续往北走:弗林特、萨吉诺、海湾城。我的羞耻感越来越强烈。咔嚓,咔嚓,咔嚓,你这该死的混蛋。
在海湾城北部的某个地方,我在打瞌睡。我梦见爸爸比现在酷,我也比现在酷。我梦见我们是前方道路上安静的主人和坚忍的伙伴。他是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而我是他希望我成为的古老的儿子。我和他踏上了横穿美国的新道路。

在我的梦里,我们在去西部的路上打零工。我们住在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和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所在的德克萨斯沙漠里,破旧的汽车旅馆挂着垂直的霓虹灯,老板是坚强、安静的女人,名字像拉弗恩(Laverne)或西尔玛(Thelma)。后来,当汽车行驶到麦基诺大桥以北时,我想象着我们身处内布拉斯加州的狭长地带,在那里,难以启齿的家庭秘密被锁在一个又一个家庭牧场的大门里。那里一家餐馆的老板雇了我们,我当厨师,爸爸做杂工,直到我们攒够了继续生活的钱。晚上餐馆打烊后,我们疲惫而微笑地坐着,一边吃着冰凉的汉堡和派,一边谈论我们到达海岸后的生活。
我醒来时,像一束光在松林中向西移动,穿过兔子形状的半岛,离大湖只有几个街区。我的梦想被和我美国化的姓氏一样古老的松树窒息而死。大约一小时后,那辆旧庞蒂克沿着41号美国公路的最后一座小山驶向马奎特。这不是1940年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的黑白自由,而是1984年中西部的特雷特彩色(technicolice)对我的压迫。我们住进了小镇另一边高速公路旁的一家廉价的木制汽车旅馆。我们谈论天气和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之后我们会在散发着体味和空气清新剂味道的橙色床罩上吃。
我们都知道明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这样他就能早起了。我们会把我的一些东西搬到我的宿舍,然后爸爸会把庞蒂亚克调转车头,回到我们属于的地方。他会摆脱我,但我的存在带来的负担和压力仍然会从我在巴洛街的小卧室里散发出来。
我将摆脱他,但我个人的耻辱,以及挂在我年轻肩膀上的沉重的公共耻辱,将在许多年里来来去去,缩小又壮大。但因为我年轻,而他不年轻,只有他会意识到我们明天要做什么,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他会走的,我会独自一人在马凯特,带着我的包衣服和我的唱片,没有东西可以放。

版权所有©2020 by Lou Vargo。版权所有。卢·瓦戈在底特律出生长大。2003年,他从德克萨斯州来到纳什维尔。他和妻子、女儿、继女、狗和猫住在纳什维尔东部。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