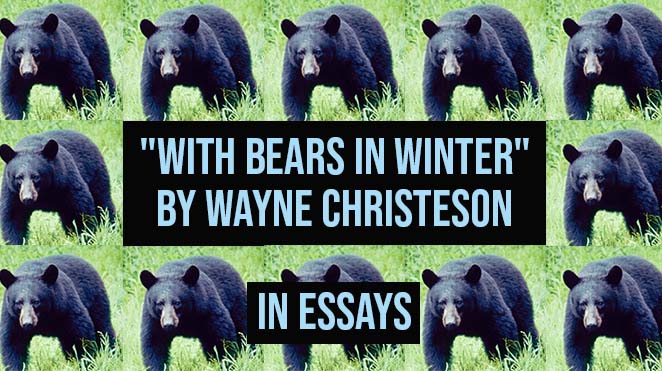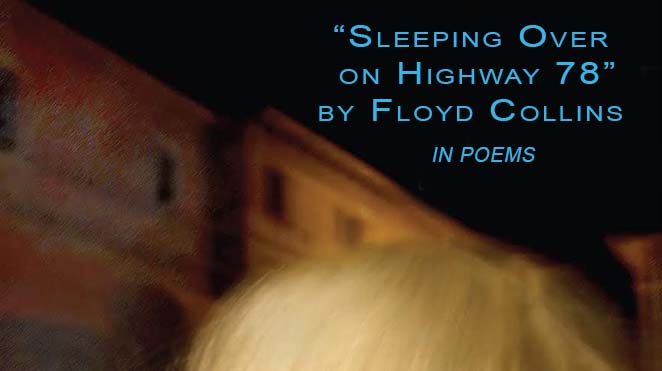我最早的一些记忆与内疚有关。伴随着内疚而来的是对地狱的恐惧。当我长大到知道我应该做个好人时,我知道我做不到。这种恐惧和内疚大部分来自我的祖母,我叫她梅梅。我记得很久以后,当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在她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恐惧,而且更加强烈。她也不可能一直表现得很好。

我们应该从耶稣洁净的宝血中找到安慰,我相信我们做到了。有一点。然而,当我刚为我的罪祈求宽恕时,我就发现自己做了其他需要宽恕的事情。回首往事,我发现我的罪过虽小(如果可以描述的话),但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一个罪过都是巨大的。
我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信徒。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了这么多。这主要意味着避免,戒酒,诅咒,婚前性行为。甚至连性的想法都是一种罪过。当然,我不知道性是什么,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但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情侣接吻时,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看到情侣接吻时,我感到一种罪恶的快感。禁忌中有某种刺激的东西,所以即使我努力抵制它们,它们也会把我吸引进去。也许比我从未被警告过还要严重。
我的玩伴主要有两类人:一是我的表兄妹,二是为爸爸卖毛线刷子的人的孩子。爸爸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场经理了,这让我觉得很有优越感。这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孩子是第二组的两个,迈克和拉唐娜。他们都比我小,所以我不能怪他们把我引入歧途。不,很明显是反过来的。我只比迈克大一岁左右,但在当时,一年似乎是永恒的。我想尝试和某人接吻,而他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人选。我狡黠地建议玩过家家,拉当娜扮演我们的孩子,我扮演晚上等待她丈夫(迈克)回家的家庭主妇。当他来的时候,我想在门口见他,然后冲到床上亲吻。
我的想象到此为止,但不知怎的,即使在那时我也知道,在床上这种顽皮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迈克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我回忆起的情感洪流中,羞愧和内疚超过了兴奋和快乐。我们放弃了这个游戏。
是晚了还是早了?我不能肯定——隔壁的男孩说如果我给他看我的,他就给我看他的。我感到震惊,但并不不快。我们迅速地脱下裤子,在我仔细看之前又把裤子拉了起来,仍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第二天,我建议我们再做一次。
他的母亲从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后面走出来,我羞得满脸通红。我再也没提过。
我的沉默和羞愧并没有阻止我的想象,但它确实结束了我开始的性探索。每次见到大卫的母亲,我都感到畏缩。如果她告诉妈妈怎么办?因为,尽管大卫的母亲用不赞成的目光看着我,但我知道妈妈的反应会更糟。
妈妈没有和我谈论性——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但她仍然毫无疑问地向我传达了那些禁忌的事情。禁入比不淑女更糟糕,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例如,有坐或站的方法。表兄弟姐妹绝对不能被视为男朋友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出于某种我能感觉到但不理解的可耻的原因。
有一次,雨下得很大,刺痛了我们的皮肤,我的表兄妹杰西·雷(Jesse Ray)和威尔迪(Wildie)和我正在小拖车的床上打牌,家里有些人就睡在湖边。我们把床单盖在头上,卡片在床单下面看不见了。妈妈走进房间,冲我们尖叫,好像我做了什么卑鄙的事被抓住了似的。我羞愧地缩了缩,就好像我有过一样。
后来,当我们玩捉迷藏时,威尔迪想和我躲在同一个地方,把他那黝黑的硬邦邦的身体贴在我的身上,我逃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我中了枪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这条路上有毁灭。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继续犯罪。还是因为我觉得死亡和地狱之火离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并不是说性的想法是我唯一的内疚来源,绝对不是。我还记得嫉妒。一天,拉唐娜来陪我玩,她爸爸和爸爸在谈生意;她拿着一个崭新的、亮闪闪的黑色漆皮钱包(可能是塑料的,现在我回头一看),有拉链和漂亮的粉红色镶边。我是多么渴望得到那个钱包啊!因为她比我小几岁,我巧妙地和她谈妥了一笔交易,我带着漂亮的钱包出现,而她得到的只是一些我根本不在乎的旧玩具。奖品在我手里,我永远不会喜欢拿着它。只看了一眼,我的胃就因为突然的恶心而翻腾起来,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我欺骗了她,骗走了她这么珍贵的宝藏。很明显,我正在走向地狱。

当贝尔城小教堂的牧师波普修士把他瘦削的身躯抬到他闪亮的黑鞋尖上,靠在讲台上,用手指着会众谈论罪恶和诅咒时,我知道他是在指着我。当然,我周围那些戴着帽子、穿着最好的衣服的成年人,从来没有犯过一次罪。只是我从内到外都有缺陷。
当我走路的时候,我的蕾丝花边小袜子在我的玛丽简鞋里和我的脚下到处都是。我避开波普修士的眼睛,弯下腰想把它们拉出来,但收效甚微。我多么羡慕街对面孤儿院的女孩们只穿着鞋子,不穿袜子,把t字带挂在后面,这样她们的鞋子就像成年女士穿的高跟鞋。
“请放松。”我求妈妈让我这样穿背带。
“你太年轻了。绝对不是。”
“我不比克拉拉·贝尔年轻多少。”我指出来。“她总是这样穿她的衣服。而且不穿袜子!”
“她没有妈妈告诉她更好的。把自己和那些可怜的小孤儿相比绝不是个好主意。”
做完礼拜后,孤儿院的负责人默多克先生会取笑我。“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回家吗?”
我躲在妈妈的裙子后面,紧紧抓住她穿着长筒袜的腿。“不!”
虽然我很羡慕这些女孩,是的,嫉妒她们,但我知道我不想住在那里。我想,如果我和他们呆在一起一次,我就会被困在那里一辈子。我在想这是不是孩子们掉进去的坑。他们曾经有过像我这样的父母吗?
尽管我有很多问题,但我很少说出来。爸爸妈妈都不鼓励他们,他们的回答总是让我感到愚蠢或羞愧。而且通常没有更好的消息。同时,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嫉妒,因为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把这与我对我所拥有的缺乏感激之情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罪过。
 有趣的是,现在爸爸妈妈都快80岁了,我却不停地问他们问题——问他们的过去,问他们对前几代人的记忆,还有我的童年。他们心甘情愿地回答,唤起早已遗忘的记忆,让彼此填补空白。我之前的印象正确吗?在我小时候,他们真的是太忙了,或者太专注了,对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太不自信了,以至于懒得回答我吗?或者他们会高兴地回答吗?奇怪的是,涟漪能改变一切。
有趣的是,现在爸爸妈妈都快80岁了,我却不停地问他们问题——问他们的过去,问他们对前几代人的记忆,还有我的童年。他们心甘情愿地回答,唤起早已遗忘的记忆,让彼此填补空白。我之前的印象正确吗?在我小时候,他们真的是太忙了,或者太专注了,对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太不自信了,以至于懒得回答我吗?或者他们会高兴地回答吗?奇怪的是,涟漪能改变一切。
当我回头看到那个曾经是我的女孩——她曾经是我,不是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同一个人。人们管那个女孩叫黛比,或者黛比·简,有时也叫黛比·珍妮,或者就叫珍妮,他们说那个女孩早熟,因为她这么年轻,词汇量却很大,尽管她的杜威叔伯伯会说:“那个女孩比她表现出来的要老得多。”
除了梅梅以外,人们不常说我是罪人。不,他们大多称赞黛比·简。很多记忆都不是我的,而是别人告诉我的关于我自己,关于她的事。哪个才是真正的黛比?是那个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罪恶和羞耻程度的女孩,还是另一个?那个女孩很自信,确信她长大后会有所成就,也许会取得伟大的成就。
那时,世界还没有告诉她——或者向她展示——她太矮,或者太聪明,太健谈,在运动中太不协调,鼻子太长,等等。她学会了不那么自信,退缩到幕后,为自己的缺点道歉。做我自己。然而,我仍然困惑于不同的身份究竟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怀疑现在的我是两种情况的混合体:我记得的事情和别人告诉我的事情。
我想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反思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与最终出现的自己无关的版本,或者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这是否正常。当我回忆起曾经的自己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像她们中的一个认为的那么聪明,我也不像另一个认为的那么邪恶。

版权所有©2021 by Debra Coleman Jeter。版权所有。黛布拉·科尔曼·基特她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名誉教授,已经出版了三本小说、一本回忆录和一本教科书。她的作品也发表在职业女性,新女性,自我,家庭生活,精明的,基督教的女人,美国婴儿.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