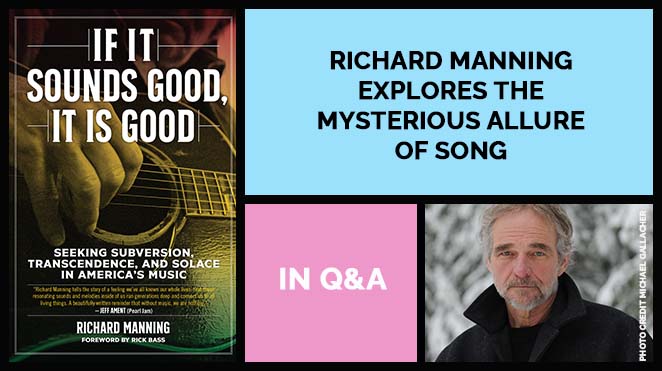美国南方的吉姆·克劳时代涉及的不仅仅是种族隔离法和被剥夺选举权的选民。正如玛格丽特·a·伯纳姆在用已知的手在美国,吉姆·克劳制度是由暴力强化和定义的。伯纳姆专注于1920年至1960年这段时期,写出了种族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精细历史,同时分析了更广泛的法律缺陷和不公正。

伯纳姆是东北大学法学特聘教授和民权与恢复性司法项目主任。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NAACP law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1977年,她加入波士顿市法院,成为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门第一位非裔美国女性。2021年,拜登总统任命她为民权悬案记录审查委员会成员。她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问题米兰:
米兰:从更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角度来看,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种族暴力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它有什么功能?
玛格丽特·a·伯纳姆:种族暴力限制了南方黑人的公民权。当然,剥夺公民权划定了包容和排斥的界限,但种族暴力使这些界限变得更加坚硬、尖锐和坚固。事实上,这些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剥夺公民权导致了种族暴力——南方各州和联邦政府官员被不包括黑人公民在内的选民赋予权力——但种族暴力也加剧了剥夺公民权。
虽然W.E.B.杜波依斯指出“黑人在乔治亚州是一个必须骑‘吉姆·克劳’的人”,但我在书中指出,黑人也是法院大门为其关闭的人。有目的的和无情的,随意的和平常的,暴力可能在任何时候爆发,因为最微不足道的原因-不脱帽,或说“先生”,或在人行道上占太多的地方,或激怒商店的店员。迄今未被探索的档案显示,黑人受害者在这些攻击面前是无助的。如果你与白人邻居争吵,或与公交车司机“打架”,你可能会因此被杀,简单明了。
 米兰:这本书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你如何撰写一篇既分析法律结构又分析普通人的历史?
米兰:这本书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你如何撰写一篇既分析法律结构又分析普通人的历史?
伯纳姆:在15年的时间里,我和一群学生一起收集了2.5万份关于吉姆·克劳时代针对黑人的杀戮的文件。我们建立了这些文件,以识别不同时间和地理的模式,我们与家庭会面,分享我们学到的东西,并吸收他们的记忆。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联邦记录,主要来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以及NAACP等倡导组织的记录。虽然我们关注的是法律史,但由于我们调查的时候有很多近亲还活着,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是为了它的“生活史”。
米兰:为什么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不保护南方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是法律问题、文化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
伯纳姆:联邦检察官有法律权力起诉这一时期的种族暴力肇事者,但他们缺乏政治意愿。将暴力干涉宪法权利定为犯罪的联邦法律是在重建时期通过的,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搁置,即使在那时,也很少适用。直到1939年,司法部才设立了一个部门来处理种族暴力问题。直到1946年,联邦检察官才根据这些重建法令打赢了一起反黑人暴力案件,并在上诉中成功辩护。更多的时候,司法部听从了当地检察官的意见,因为他们不愿把这些案件交给缺乏同情心的陪审员。
米兰:可以说,法律的底牌是对南方黑人不利的。然而非裔美国人仍然可以打出他们的牌,对吧?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时代,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
伯纳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激进派,反抗都有多种形式。事实上,杀戮本身往往是对受害者个人对抗黑人的决心的回应。1944年,一名名叫布克·斯派塞的士兵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被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杀害,因为他批评了吉姆·克劳座位。1947年,一名刚回来的老兵蒂莫西·胡德在阿拉巴马州的贝塞默被杀,当时他拒绝了公共汽车的后部。1943年,穿着制服的威利·李·戴维斯(Willie Lee Davis)在乔治亚州的Summit被一名警察杀死,当时他告诉警察不要虐待他,因为他宣称,“我现在不是你的人,我是山姆大叔的人。”
无论是日常的还是地下的,在葬礼上,在点唱机里,就像在传单和社论中一样,对吉姆·克劳的抵抗渗透了黑人文化,贯穿了与白人个人和白人权力结构的整个社会关系。反抗是肯定和创造黑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米兰: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用已知的手最能引起你共鸣的是什么?
伯纳姆:埃德温·威廉姆斯的死让我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我们见过他的很多家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当他被杀时,他们还是孩子,就在现场。他们现在已经大四了,当我们寻求合作时,他们已经把这场悲剧抛在脑后。1943年,埃德温·威廉姆斯和家人住在新奥尔良附近的阿尔及尔。那年4月的一个工作日,当他从教堂回家时,三名白人水手袭击了他,并在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的注视下将他砍死。陪审团宣布被起诉的一名男子无罪,海岸警卫队立即将他派往战场。甚至有一场审判标志着某种程度上的进步,但无罪释放,正如它所做的那样,与这个时代的其他数十人相呼应,突显了黑人受害者必须爬上多么陡峭的山才能获得正义。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威廉姆斯的儿子如今是他们1943年所属教会的高级牧师。
米兰第十六章: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你讨论了赔款的概念。对黑人暴力和不公正的受害者的赔偿可能是什么样的?
伯纳姆:这段历史仍在我们身边。只要稍加努力,我们就能找出那些受到吉姆·克劳暴力影响的家庭。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些事件发生时有权得到什么,我们也大致知道他们被剥夺了什么。我们可以计算他们的损失,就像计算日本血统人士的损失以满足1988年《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的条款一样。州和联邦立法者现在应该采取行动,在受害者的后代还活着的时候,纠正这些伤害——如果不是政府政策和做法造成的,也是促进了这些伤害。

亚兰Goudsouzian是孟菲斯大学比佐家族历史学教授。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人物与时刻:1968年美国大选与党派政治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