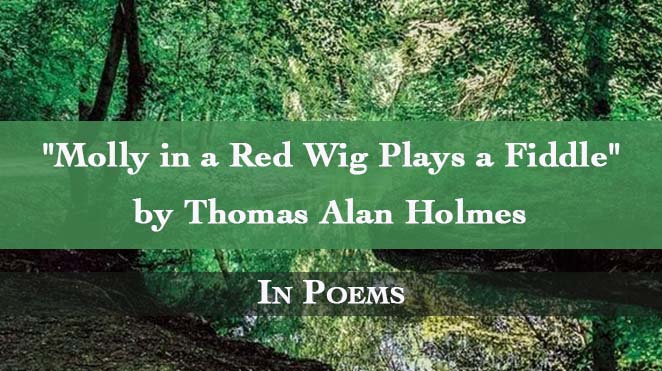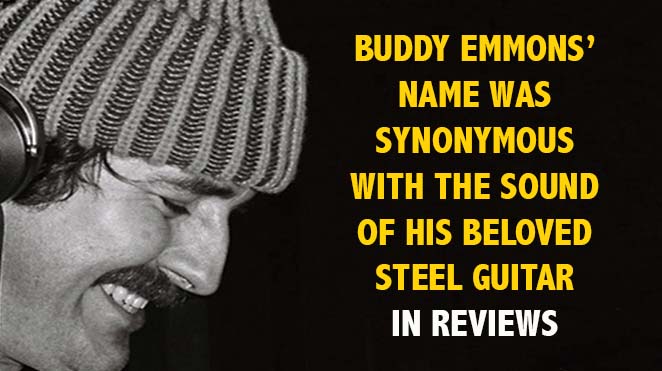从米兰档案: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3月27日。
***
在纳什维尔的六月中旬,就在夏天变得难以忍受的炎热的前几天,我和查理·斯特罗贝尔坐在车里,向河边驶去。在纳什维尔长大,信奉天主教,就意味着至少要认识一些斯特罗贝尔家族的成员。早在我和查理成为朋友之前,我就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失去的东西。我们在去体育场旅馆的路上,去拜访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即将得到自己的公寓。在开车的时候,查理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丹·理查森神父的故事。丹神父是北纳什维尔的Assumption教区的牧师,查理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它离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不远。
“丹神父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查理说,他自己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我们住在离教堂不远的街道上,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助手了。”
Assumption是一个教众年龄较大的教区,查理记得葬礼一个接一个地举行。每次葬礼,丹神父都做同样的布道。“我们一字不差地知道。我们可以跟在他后面念。”查理说。尽管他现在已经69岁了,离他当祭台童的自己已经很远了,他还是开始背诵:
“丹神父会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死亡做准备。当我们死的时候,上帝不会问:‘查理(安、莎莉、约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赚了多少钱?你有多少套房子?“‘上帝只会问我们两个问题:‘你爱我吗?和“你爱你的邻居吗?”’我们可以想象查理(安,莎莉,约翰,填空)会如实回答,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我的邻居。’上帝就会说:‘做得好,你这又好又忠心的仆人。现在你们要进天国去。’”
 查理一想到这事就笑了。”他钉每一次.他的声音很柔和,节奏也很完美。尽管我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它总能抓住我。这是令人悲伤的,特别是如果我认识那个死去的人,但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积极和充满希望的信息。我们来自上帝,我们回归上帝,所以死亡从来都不可怕。”
查理一想到这事就笑了。”他钉每一次.他的声音很柔和,节奏也很完美。尽管我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它总能抓住我。这是令人悲伤的,特别是如果我认识那个死去的人,但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积极和充满希望的信息。我们来自上帝,我们回归上帝,所以死亡从来都不可怕。”
查理这时才意识到他已经错过了出口。我们俩都没有注意到州际公路,也都没有感到遗憾。这给了他时间来完成这个故事。
“即使在我长大成为牧师后,我也不能叫他丹。总是丹神父。我总是对他说,‘今年圣诞节你准备送我什么礼物?’他会说,‘一座桥’,因为无家可归的人住在桥下。”丹神父是爱尔兰人,他总是被人取笑。
“当他去世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我们进行了私人谈话,一种父子间的谈话,我告诉他我有多爱他。然后我说,‘现在我要做你的牧师了。’然后我做了他的全部例行公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死亡做准备的,当我们死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丹,你赚了多少钱?’他会问两个问题:“你爱我吗?”和“你爱你的邻居吗?”我知道你会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我的邻居。”神必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吧。“‘
令我震惊的是,我们年轻时学到的东西,那些我们从未想过需要的东西,往往使我们能够满足以后生活对我们的要求。“我已经成长为我自己,”查理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些生活经历。”
查理向每一个靠在门边或趴在大厅里的男男女女打招呼。他向前台的一个女人宣布了我们去拜访罗恩和希德的计划,那个女人声称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告诉她他是查理·斯特罗贝尔,说他在等着。“哦,”她微笑着点头说。
在它最好的时候,体育场旅馆一定是一个便宜的汽车旅馆,对方球队的球迷可以在足球比赛结束后在那里过夜。但是,现在任何一个在那里订了房间的足球迷都可以不用下车就能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把车停在前面,查理停了下来,看了看坐在台阶上的那些人,然后又看了看我。“我会让车一直开着的,”他说,试着计算他可能会在里面呆多久。“你把门锁上,等着。”
当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和他一起去时,他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哦,那太好了,”他说。他把手伸进后座,拿出一个双炉电炉。体育场旅馆是我当警察的父亲所说的廉价旅馆,是按周收费的最低档次的汽车旅馆。查理向每一个靠在门边或趴在大厅里的男男女女打招呼。他向前台的一个女人宣布了我们去拜访罗恩和希德的计划,那个女人声称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告诉她他是查理·斯特罗贝尔,说他在等着。“哦,”她微笑着点头说。她告诉了我们房间号,并指引我们去电梯。罗恩和希德很快就要搬进他们自己的公寓了,那是一间没有火炉的公寓。 They would need a hotplate. We took the one we had upstairs.
多年来,走廊里的地毯经历了人类的每一次灾难,现在都用漂白剂解决了,使它变成了一幅长长的抽象画。在昏暗的黄色灯光下,一排紧闭的门,每一扇都发出独特的音乐节拍,包括我们正站在前面的那扇门。我看见一只眼睛在窥视孔里打量着我们,然后抽离了。我走到一边,确信自己一定像个假释官。“希德,”查理叫道,语气就像一个顺道来拜访的亲戚那样愉快而执着。“这是查理。把门打开。”他等着,然后又敲了敲门。
等了很长时间,终于门开了,一只黑眼睛从烟雾中探出头来,然后门开得更大了。“父亲!那人说着,给了查理一个拥抱。(查理可以不取这个头衔,因为他认为这个头衔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如果这个词父亲为了让大家感觉好一点,他接受了。)
 希德和罗恩是盐和胡椒瓶,希德一头深棕色的头发,蓄着浓密的棕色胡子,罗恩一头褪了色的红头发,灰白的胡子长到一半的胸口。两人都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背心和棒球帽。两个人的体重都不可能超过100磅,他们的上臂并不比手腕大。我们进行了介绍,他们和我握了握手。尽管他们不愿开门,但他们显然很高兴我们来了。房间里有两张没有整理过的床,床中间有一堆烟灰缸,一台控制台电视机正在播放乡村音乐。一辆购物车靠墙停放着,整齐地包装着,里面的东西用防水布盖好,系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罗恩说着,拍了拍马车。“明天有人来帮我们搬家。”
希德和罗恩是盐和胡椒瓶,希德一头深棕色的头发,蓄着浓密的棕色胡子,罗恩一头褪了色的红头发,灰白的胡子长到一半的胸口。两人都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背心和棒球帽。两个人的体重都不可能超过100磅,他们的上臂并不比手腕大。我们进行了介绍,他们和我握了握手。尽管他们不愿开门,但他们显然很高兴我们来了。房间里有两张没有整理过的床,床中间有一堆烟灰缸,一台控制台电视机正在播放乡村音乐。一辆购物车靠墙停放着,整齐地包装着,里面的东西用防水布盖好,系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罗恩说着,拍了拍马车。“明天有人来帮我们搬家。”
“你保持清醒吗?”查理问,他的声音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是,他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如果他们不是,他仍然爱他们。
“是的,爸爸。”希德说。
“四天,爸爸。”罗恩说。
查理试图引导他们谈论干净有多好,虽然他们显然想取悦他,但他们的心不在这上面。他们计划安顿下来后找份工作,也许是洗碗。罗恩摘下棒球帽,把头发往后梳,露出额头上一条长长的伤疤。“不过我不知道,”他说。“自从我被击中后,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保持清醒吗?”查理问,他的声音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是,他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如果他们不是,他仍然爱他们。
查理把电炉给了他们,他们对这还在盒子里的新东西感到惊奇。他们谈起了搬家的事,查理答应给他们办公交卡。当我们终于准备离开时,两个人又一次拥抱了他,并保证以后会好好表现。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住在离我们五扇门远的地方,他总是惹事生非,所以我们去敲那扇门,敲了很长时间,但尽管门外音乐声震耳欲聋,无论怎么叫也不能把人引出来。
“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看到的最好的样子。”当电梯颤抖着下降到一楼时,查理高兴地说。“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很好,你不觉得吗?”
我以前没见过他们的眼睛,但我被两个人的甜蜜所打动,更被他们看上去的疲惫所打动。无家可归是一种既疲惫又危险的状态。
查理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喜欢向募捐者讲述——他与无家可归者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他还是圣名教区的年轻牧师时,他为一个敲他教区长门的人做的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在那之后不久,下一步就来了,正如他在当地一神教会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
“他是我的恐怖分子。他踢开了纱门。他把教区里的每个人都骂了一顿。他希望一切都能为他做好。我母亲过去常对我说,‘幸福是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会告诉她,如果他是我去天堂的门票,我也不想去。教区里的每个人都怕他。”
他们在教堂的停车场,睡在我的窗下,那天晚上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我没有想太久,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我会说服自己放弃。作为一名牧师,我知道这样一个决定的后果远比简单地给十几个人一个晚上的住宿要严重得多。明晚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做什么?然后下一晚,下一晚,一直下去?一个简单的决定可以变成一生的承诺。教民们会怎么说?或主教吗?或者是你的邻居吗?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这是该做的事。 Like Scarlet O’Hara, I found myself saying, “I’ll worry about that tomorrow.” So I invited them to spend the night, and they’ve been with me ever since.
就在他努力满足这些迫切需要的时候,多伊·阿伯特来了。
“他是我的恐怖分子,”查理说。“每天早上他都把我叫起来要早餐。他是圣名的常客。他踢开了纱门。我们不得不把那扇门换了三次。他把教区里的每个人都骂了一顿。他希望一切都能为他做好。我母亲过去常对我说,‘幸福是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会告诉她,如果他是我去天堂的门票,我也不想去。教区里的每个人都怕他。”
除了玛丽·霍伍德。她是教区的管家、秘书和簿记员。她在55岁时开始工作,养育了12个孩子。和多伊在一起时,她的语气总是平静而恭敬的,而多伊也以恭敬的语气回应她。他们互相倾听着。
就在那时,我读到了多萝西·戴说过的话。她说她想做的是爱穷人,而不是分析他们,也不是改造他们。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就像灯亮了一样。我想起了霍伍德太太。我意识到多伊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要爱的兄弟。我当场决定,我要爱他,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一夜之间他就变了。他停止了咒骂,停止了暴力。我觉得我们成了兄弟。我是他的仆人,他是我的主人。他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
 查尔斯Strobel成立旅馆的房间以及1986年设立的人类发展校园,作为无家可归者的学习中心、休息中心、庇护所和救济中心。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他几乎一周七天都能在那里找到。最初,它是由当地各教派教区组成的一个组织,在寒冷来临的时候,它欢迎无家可归的人来吃顿饭,并在那里过夜。他们的第一个建筑传统上很沉闷,有一些用于互助会和艺术项目的教室,淋浴,衣服,和一个祈祷的地方。查理的主要天赋可能是他为穷人服务的能力,但他也拥有同样必要的天赋,能够与董事会、当地政府、警察、各种宗教组织以及有钱支持他的愿景的人合作。他的激进观点是,无家可归的人不需要在低矮黑暗的地方接受服务,一无所有的人应该能够站在拥有一切的人旁边,抬起头来。现在的校园建筑是崭新的,看起来也很时髦,它的玻璃和钢铁结构与几个街区外的纳什维尔的昂贵公寓一样时髦。查理对待无家可归者一贯的尊严终于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得到了体现。校园的宗旨是,通过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我们的校园强调圣经中的爱和社区的理想,为纳什维尔的信徒提供了一个直接回应我们中间的破碎和被剥夺公民权的机会。与穷人相交是我们宗旨的核心.
查尔斯Strobel成立旅馆的房间以及1986年设立的人类发展校园,作为无家可归者的学习中心、休息中心、庇护所和救济中心。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他几乎一周七天都能在那里找到。最初,它是由当地各教派教区组成的一个组织,在寒冷来临的时候,它欢迎无家可归的人来吃顿饭,并在那里过夜。他们的第一个建筑传统上很沉闷,有一些用于互助会和艺术项目的教室,淋浴,衣服,和一个祈祷的地方。查理的主要天赋可能是他为穷人服务的能力,但他也拥有同样必要的天赋,能够与董事会、当地政府、警察、各种宗教组织以及有钱支持他的愿景的人合作。他的激进观点是,无家可归的人不需要在低矮黑暗的地方接受服务,一无所有的人应该能够站在拥有一切的人旁边,抬起头来。现在的校园建筑是崭新的,看起来也很时髦,它的玻璃和钢铁结构与几个街区外的纳什维尔的昂贵公寓一样时髦。查理对待无家可归者一贯的尊严终于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得到了体现。校园的宗旨是,通过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我们的校园强调圣经中的爱和社区的理想,为纳什维尔的信徒提供了一个直接回应我们中间的破碎和被剥夺公民权的机会。与穷人相交是我们宗旨的核心.
这基本上意味着我我是校园服务的对象。这个中心让我有机会体验查理生命中巨大的快乐——有机会直接回应我们中间的破碎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
“你所要做的,”他告诉我,“就是对生活可能不公平的可能性给予一点理解。”
好运气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把它等同于个人的好,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很好,而别人的生活不太好,我们就会认为他们一定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自己的好运。我们常说自己是被祝福的,但除了别人没有被祝福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呢?上帝拣选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去爱更多的人。我们有责任互相关心,在不公平的情况下创造公平,在过去可能不存在的地方寻求平等。尽管查理自己也经历过不公平,但他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他的激进观点是,无家可归的人不需要在低矮黑暗的地方接受服务,一无所有的人应该能够站在拥有一切的人旁边,抬起头来。“你所要做的,”他告诉我,“就是对生活可能不公平的可能性给予一点理解。”
查理的父亲在46岁时死于心脏病,他留下了四个年龄在8岁到4个月之间的孩子。后来,查理的母亲玛丽·凯瑟琳·斯特罗贝尔(Mary Catherine Strobel)在一场房屋火灾中失去了母亲,16岁时失去了深爱的父亲,在消防局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月薪185美元。她还照顾过两个姑姑,莫丽(Mollie)和凯特(Kate),莫丽当时81岁,凯特78岁。玛丽·凯瑟琳对她丈夫的死和随后的苦难的解释是,这一切都不是上帝的错。上帝,和他们的父亲,会一直守护着他们。
在马丁·斯特罗贝尔的新陪伴下,上帝从天堂看着孩子们,而凯特阿姨和莫丽阿姨则在白天看着他们,而玛丽·凯瑟琳则在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容易相信耶稣的话,‘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一样,’”他说到他的姑姑们。“这让我在逻辑上更进一步,我相信上帝爱我们,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就像任何忠诚的仆人一样——因为我从莫丽姨妈和凯特姨妈那里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他给我讲了《路加福音》第17章中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如果一个仆人做了所有要求他做的事,然后高兴地做得更多,他就被称为“无用的仆人”(或者“无利可图的仆人”,或者“不值得称赞的仆人”,这取决于翻译)。这是一种如此深沉、如此包罗万象的爱的状态,以致仆人迷失了自我,以致无价值变成了一种超越。“他们是没用的仆人,”查理说,想起了他的姑姑和母亲。“他们只想为我们服务,这意味着我们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为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他们从不惩罚我们。我从来不记得他们叫我帮他们做家务。”查理问我是否在听他的,因为在毫无价值中发现成就的概念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不是星期日布道的内容。当然,我能想到许多例子,在这些例子中,那些被服侍过的人没有动力去服侍别人,但如果被深爱能让我们深爱,那么,是的,我理解。
“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不是很好吗?”他对我说。“无用的仆人?”
我告诉他我还没到那一步,但我可以把它看作一件值得向往的事情。
这是一种如此深沉、如此包罗万象的爱的状态,以致仆人迷失了自我,以致无价值变成了一种超越。
“我不太愿意这么说,”他说,然后停顿了很长时间,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打算继续说下去,“很多人都在自己的信仰上挣扎,但对我来说,上帝从来不是挣扎的对象。我对我来说一直很挣扎,但我从来都不能真诚地相信上帝不存在。”
这是他一整天中唯一犹豫要告诉我的事。他觉得,如果承认对那么多人来说如此困难的事情,不费力气就来到了他的身边,并一直陪伴着他,那可能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行为。
在酒店房间的大厅里,墙上有一个有650多片树叶的树雕塑。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在纳什维尔去世的无家可归的男人或女人的名字,每一片新叶子的加入都丝毫没有动摇上帝的存在。1986年12月,查理的母亲玛丽·凯瑟琳·斯特罗贝尔(Mary Catherine Strobel)在纳什维尔西尔斯(Sears)的停车场被一名来自密歇根的逃犯绑架,并被杀害,这是这场最终夺去6条生命的杀人案的第一个受害者。
但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故事的记忆是,她当时在客栈的房间里工作,被一个流浪汉杀死了。人们说玛丽·凯瑟琳创办了《客栈里的房间》,查理接手她的工作是为了赎罪。通过将她的谋杀归因于她自己的联想,人们可以安全地远离这种随机的暴力行为。查理经常被问到在他母亲去世后他是否会继续他的工作。“如果以前值得做,”他说,“为什么现在不值得做呢?”
“很多人都说,她不应该那样死去,”她的儿子在葬礼弥撒上说。“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说法:‘神不爱惜他的独生子,将他交出来,他的儿子清空自己,谦卑自己,甚至顺服地接受死亡,死在十字架上。“在妈妈的死中,我们全家相信,她的善良和温柔所遭受的邪恶,正如她的方式,会带来巨大的交流与耶稣。那么,我们怎么能质疑它的进程呢?这似乎与耶稣自己的死亡形式相符。为什么说到愤怒和复仇?这些话和我们母亲的想法是不相符的。”
“当然,她的死改变了我们所有人。”那天下午,我们离开罗恩和希德后,他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在去医院看望一位曾经无家可归的妇女的路上,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正努力照顾她的孙子孙女。“但可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母亲的去世让我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从那以后,我更加一心一意地想着我的人生应该做些什么。”
在人的一生中,有父亲和儿子、父母和孩子、仆人和主人、被宽恕者和被宽恕者,在不同的时刻,我们被要求扮演一个角色,然后扮演另一个角色。当我们做对了,我们就在心中树立了基督的榜样。当我们终于回到客栈的房间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天还亮着,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查理一生的成就包围着我们,不是眩目的建筑,也不是门前的鲜花,而是向四面八方散开的人群。这是他们感到安全、感到被爱的地方。这些是他服务的人。
版权所有©2013安·帕切特。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最初发表于不止于一切:天主教作家论良心英雄,从圣女贞德到奥斯卡·罗梅罗凯瑟琳·沃尔夫(Catherine Wolff)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