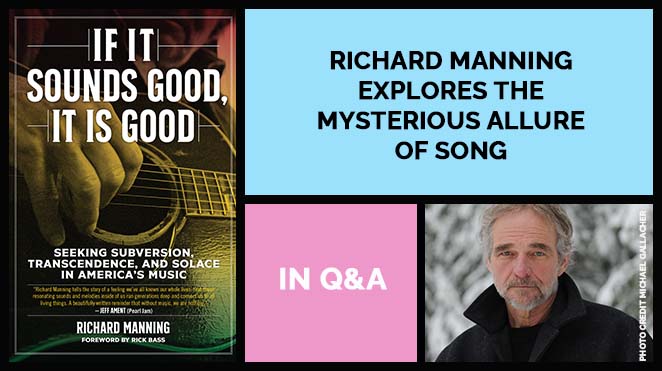第一次有人拿枪指着我的时候,我22岁,皮肤晒得很黑。(我过去常说“只有一次”,但考虑到美国的现状,我保留了选择的余地。)

我在斯普利特拜访我的祖父。斯普利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座古城,最初是一位罗马皇帝的退休之所,但在近2000年后成为克罗地亚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不久就被称为“前南斯拉夫”,1993年夏天,它正处于内战的血腥痛苦之中。
我的父亲来自斯普利特,而我和我的母亲一样,出生在塞尔维亚,在我访问的时候,塞尔维亚正在与克罗地亚作战。需要注意的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说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口音,我在美国长大,吸收了父母同样的口音(想想布鲁克林和利物浦这句话)。南斯拉夫人在我小的时候觉得这种混搭——以及我分不清口音的事实——很可爱。巴尔干战争爆发后,情况有所好转。
所以,当我到了克罗地亚,我祖父告诉我假装自己是一个只会说英语的游客,以免我体内的塞尔维亚人被她打得屁滚尿流,或者更糟。“但是人们怎么能分辨出来呢?”我颇有微词。他从眼镜上方盯着我,平静地重复道:“游客。”
斯普利特是国际记者和救援组织的非正式总部,这使这座城市相对安全。对塞尔维亚来说,攻击它就意味着攻击整个世界。50英里外,人们被屠杀,但在斯普利特,战争似乎离我们有多远,这是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如此超现实,以至于我无视了祖父的命令。一个与法西斯、纳粹作战,并在三个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知道什么?每天我都去海滩,晚上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或者在俱乐部里与我的表弟和他最好的朋友跳舞,我曾经暗恋过他们。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海滩上。这是黄金时间,当炎热终于平息,当地的老年人通常会去游泳,但那天不去,因为某种原因。在战时,我确实想到一个人在那里可能是危险的,但以我有限的智慧,我把这个想法像一只讨厌的虫子一样击碎了。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海滩上。这是黄金时间,当炎热终于平息,当地的老年人通常会去游泳,但那天不去,因为某种原因。在战时,我确实想到一个人在那里可能是危险的,但以我有限的智慧,我把这个想法像一只讨厌的虫子一样击碎了。
我在离水面几百码远的地方注意到一个士兵在海滩上脱得只剩内裤。我继续游泳。几分钟后,他来到我身边:“你是新来的。父母就这么让你一个人出去了?”他眨了眨眼。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看起来几乎没有青春期。这家伙至少30岁。我转身朝荒芜的海滩走去,但在此之前,我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告诉他,我不住在斯普利特,他警告过我不要说话。他跟在我后面。
回到岸上,我开始用力擦干身体,以至于被地毯烫伤了。他靠近了。A-foot-and-a-half-away关闭。
在哪里做了我住吗?他想知道。
“西雅图”。
“该死的姑娘,太远了。你们家是本地人吗?”
“是的。”
“你在那里上高中?”
“没有,我刚从大学毕业。”
“该死的女孩,我还以为我手上有个14岁的孩子呢!”
“我知道。”
他毫不在意,又眨了眨眼睛。“你在西雅图有什么娱乐活动?”
我开始胡言乱语——关于表演课、雨、垃圾音乐,以及这家新开的咖啡连锁店占据了整个城市。听了这话,他的脸色变得凶巴巴的,我只能用毒药来形容。我找到星巴克唯一的巴尔干股东了吗?

他慢慢弯下腰。他折叠的迷彩服下面躺着一个皮套。他不再眨眼,平静地取下了枪,甚至更懒洋洋地对着我的鼻子挥了挥。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么难听的塞尔维亚语。
我几乎被这个愚蠢的问题逗笑了。他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我想,礼仪可能规定了枪尖的人不能嘲笑枪尖呃.
我冷冷地笑了,那是一分钟。直到我突然想到:三年级!
我在4岁的时候搬到了美国,和很多移民的孩子一样,我拒绝在我的新国家说母语。即使父母试图贿赂我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也会用英语回答。但是我——和我的懒惰——不能被一天一个冰淇淋筒所收买。然而,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住在华盛顿特区和南斯拉夫大使馆附近,我每隔一个星期六就在那里学习当地的语言、西里尔字母、一战、二战的史诗战役……
我尽可能随意地向那个士兵解释我的补习教育,责备那些疯狂的塞尔维亚老师——为了强调,我往地上吐唾沫——我说话的方式。我补充说,我的克罗地亚父母和我,不幸的是,当我在100%克罗地亚人的家里长大时,从不说克罗地亚语。
他站在那里沉思,还在转着枪。我抖得太厉害,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我若无其事地收拾东西,悄悄朝马路走去。
“嘿!”听到他的声音,我愣住了。我慢慢地转过身,想着,我就是这样死的.湿漉漉的,光着脚,晒得黝黑。
大脑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嗯,我的大脑是。滑稽的,真的。在我的恐惧中,我的神经元忘记了穿人字拖的命令,但它们可以形成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报纸能提到我那可爱的金黄色尸体.
他的枪对着我,那个士兵露出一种恶狠狠的微笑。“如果你想对你的舌头进行种族清洗,你知道到哪里来找我。”
他眨了眨眼睛。
我们回来了!我差点又要拥抱他了因为他只是个恋童癖。几乎。相反,我轻松地笑了笑,挥了挥手,匆匆离开了。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回家的,路上经过了半英里的汽车和人们,他们一定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穿着比基尼的年轻女子会带着衣服和人字拖。
当我飞进屋时,我随手锁了四次门。祖父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我把比赛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叠好报纸,摘下眼镜。这是专门为智力特别差的人准备的手势。
“咖啡。”他平静地说。
“原谅?”
”卡瓦胡椒是克罗地亚语咖啡的意思。你说kafa这是塞尔维亚语。这就是他发火的原因。”
我的颤抖变成了抽搐。
“你的意思。我可以。有。死亡。为了一个f?”
“是的。”
“字母f。”
“是的。”
从那个夏天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巴尔干战争的恐怖已经消退,对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它已成为一段鲜活的历史,对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它已成为教科书式的历史。再一次,我说话的方式在我的祖国引发了笑声和微笑。
但在我的另一个祖国美国,我仍然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连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都分不清,那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起初它使我困惑,后来它使我沮丧。现在,我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如果你要问,我就问你肤色、信仰、口音——是什么使战争成为可接受的理由?

版权所有©2020 Natasha Senjanovic。版权所有。娜塔莎·塞扬诺维奇是一名获奖记者和前公共电台主持人,她出生在前南斯拉夫,在美国长大,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度过。她是这个项目的创建者女人喜欢性.她目前住在纳什维尔。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