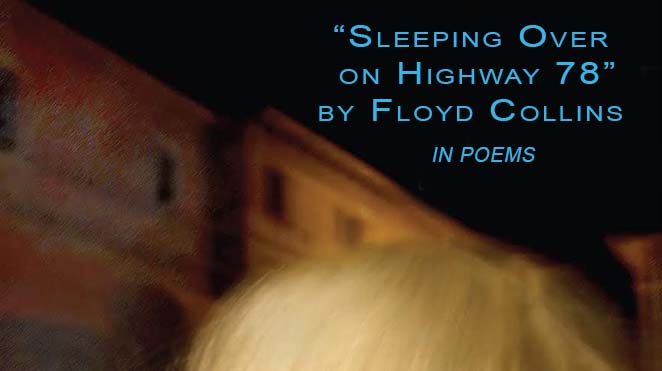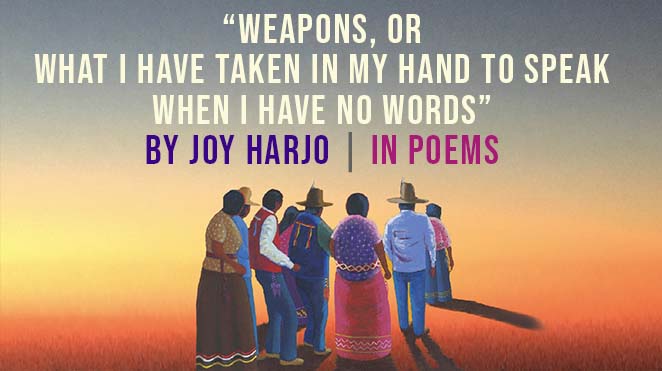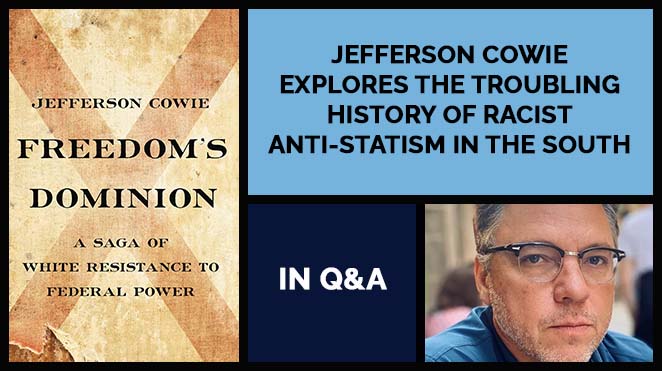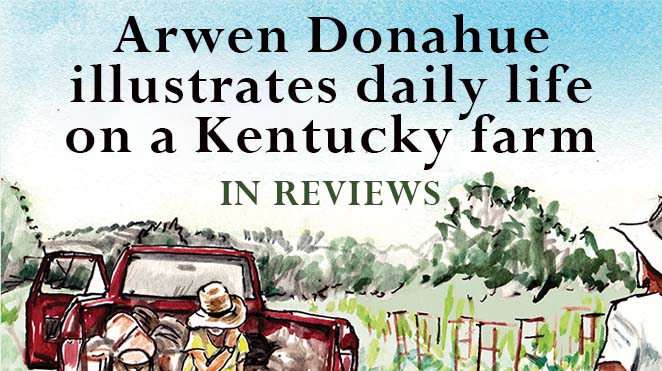如果查理觉得好玩,他会在背上盖上一条毯子,咆哮着爬过满是灰尘的松木地板,假装自己是一只准备“吃掉”孙辈的灰熊。有几次,在我们的母亲发现并禁止这种做法之前,他会在睡觉前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我们挤在小床头柜周围,他把眼镜、《圣经》和装假牙的淡绿色盘子都放在那里。带着一点戏剧性,他会把手伸进右眼睑后面的肉缝里,取出一只陶瓷眼睛。他在12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床弹簧事故失去了一只真眼睛,之后就一直戴着。画着瞳孔和虹膜的乳白色蛋黄在查理放它的床头柜上的一杯水中上下浮动。它斜眼看着我们,毫无生气,却带着嘲讽的意味,让女孩们尖叫着离开了房间,男孩们假装勇敢,恳求查理让他们拿着它。
 一张查理和莫德的黑白照片挂在他们位于田纳西州乡下的小农舍的墙上。这是1918年春天拍摄的订婚照。莫德穿着一件灰色的亚麻衬衫,一条皱褶的羊毛裙略过脚踝。她长长的黑发在颈后盘成一个发髻。她庄严的表情暗示着她对前方困难的预感,仿佛她在18岁时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将经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生下9个孩子。
一张查理和莫德的黑白照片挂在他们位于田纳西州乡下的小农舍的墙上。这是1918年春天拍摄的订婚照。莫德穿着一件灰色的亚麻衬衫,一条皱褶的羊毛裙略过脚踝。她长长的黑发在颈后盘成一个发髻。她庄严的表情暗示着她对前方困难的预感,仿佛她在18岁时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将经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生下9个孩子。
查理和莫德在坎伯兰河岸边的一处宅基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第一个孩子是在他们结婚那年生的。随后又有8个。百日咳夺去了其中一个婴儿的生命,而频繁的洪水最终夺去了房子。
莫德姓莫斯,似乎是这个名字塑造了她,她的性格是根据属和门的规律发展起来的。她看起来脆弱而无根,喜欢阴影而不喜欢光明,她在喧闹的家庭边缘安静地绽放。她很少微笑,但当她一个人在厨房里把手放在盛有温暖洗碗水的水槽里时,她哼着她最喜欢的赞美诗。莫德在那些时刻的满足使查理确信,她不会消失,事实上,她的心已经与她的身体、婴儿和潺潺的黑水构成的小太阳系之外的一种力量联系在一起。
查理是基督教堂的热心信徒,在20世纪40年代,他坚持要搬到离纳什维尔更近的地方,这样家里最大的孩子就可以上大卫·利普斯科姆学院了。他和莫德买下了160英亩农田,毗邻Donelson镇附近的石头河。当他们的农舍还在建造时,这家10口人就挤在河边的一间小屋里。他们被告知,安德鲁·杰克逊建造这座建筑是为了用作钓鱼小屋。莫德看着水上涨,想象着它像火焰一样拍打着用作前廊的石灰石石板。新房子将建在远离洪水的安全地带。她再也不用把羽绒床垫拖到二楼,免得弄湿了。她再也不需要把孩子们捆起来,催着他们往高处走了。
但是水还是找到了他们。20世纪60年代,政府迫使查理和莫德离开后,他们建造并计划住在农舍里,直到他们的死亡被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淹没。当石河被珀西·普里斯特水坝截流时,他们的农场是1.8万英亩洪水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和莫德在购买土地时并不知道,这个名为斯图尔特渡口水库的大坝项目于1946年投入使用,目的是防止坎伯兰河发生洪水。大坝于1968年完工,水位一寸一寸地上升,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梦想,由此形成的湖泊吞噬了田纳西42英里的乡村。老杰斐逊镇的居民和在河周围肥沃洼地耕作的农民被迫接受任何补偿,把他们的家园拱手让给饥饿的河水。
 查理和莫德搬进了纳什维尔一个女儿家隔壁的小房子。莫德失去了她的花园、她的鸡群,失去了农妇认为理所当然的广阔天空,失去了那些大得足以让她的悲伤倾泻其中的开阔空间。查理忙于教堂的事,也越来越多地忙于照顾莫德,因为搬家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莫德是个瘦小的女人,岁月和损失把她削成了骨头。
查理和莫德搬进了纳什维尔一个女儿家隔壁的小房子。莫德失去了她的花园、她的鸡群,失去了农妇认为理所当然的广阔天空,失去了那些大得足以让她的悲伤倾泻其中的开阔空间。查理忙于教堂的事,也越来越多地忙于照顾莫德,因为搬家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莫德是个瘦小的女人,岁月和损失把她削成了骨头。
她在1月阴冷的天气中去世,享年68岁,离我12岁生日还有三个星期。为了避开聚集在殡仪馆里的大人们,我偷偷溜到为家人准备的房间里,准备第二天的葬礼。折叠椅排成一排,前面有一扇双扇门,这扇门通向礼堂的前面,一家人可以看到棺材和讲坛,在那里我们可以躲避参加葬礼的人好奇的目光。我们可以默默地哀悼。
查理不知道我在那里,独自从礼堂后面走到我的视线范围内。他看上去老了,肩膀耷拉在西装外套下面,瘦长的步态中有一丝拖沓。他站在敞开的棺材前,莫德躺在那里,脸色苍白,穿着黑色的亚麻布紧身上衣,花枝乱展,灰黑色的头发被一顶用银别针固定住的普通羊毛帽子遮住。他盯着她,仿佛她随时都可能跳起来,帽子就会从头上掉下来。仿佛他的悲伤中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有一种她一生所没有的活力似的。
查理的脸被聚光灯照亮,他的手放在打开的棺材边缘,他的手指擦着丝绸衬里,安静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查理的悲伤表明了他被夺走的一切,多年的岁月、莫德的抑郁和水冲走的一切。到莫德去世的时候,那株生长在农舍门廊旁、每年母亲节都在草坪上撒满淡粉色彩纸的传家宝玫瑰已经融化成浮木了。他们放牧的绿色田野正在分解:土壤变成了沉积物,景观变成了湖床。
田野的轮廓和农家厨房的温暖深深印在我的心灵里,埋在一代人身上的东西可能会在另一代人身上复活。对土地的爱像DNA一样通过血液传递,查理的爱在我体内开花,融合成一种需要,对自己土地的追求成为想象生活的脚手架。
现在土地所有权更难实现。城市生活的不断进步使农村地区的土地更有价值,因此也更难以获得,这既使农村社区受到祝福,也使其受到诅咒。纳什维尔的城市扩张不断向外蔓延,就像扔进池塘的石头产生的同心涟漪。在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反向迁移中,我离开了城市,来到了农村,像查理一样,被广阔的绿色牧场所吸引,与农场生活的循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我的农场离坎伯兰足够远,对公众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但又足够近,处在在沼泽浅滩过冬的鹅的飞行路线上。它们排成队形经过我的花园时,互相哀号鼓励。我们家三代人都在种植莫德的粉色玫瑰灌木,现在它已经长成了四丛大灌木,在我的车库里伸展开来,在每个母亲节的时候把它们淡粉色的花瓣抛向微风。

版权(c) 2020年由Cynthia Ezell。版权所有。辛西娅这时警报声响起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农民和作家。她的文学作品从人类关系和环境的交集中浮现出来,反映了一种与土地和地点的亲密关系。她的作品已刊登在南方文学的死骡学派,新方向杂志,深度野生杂志,皮酒袋.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