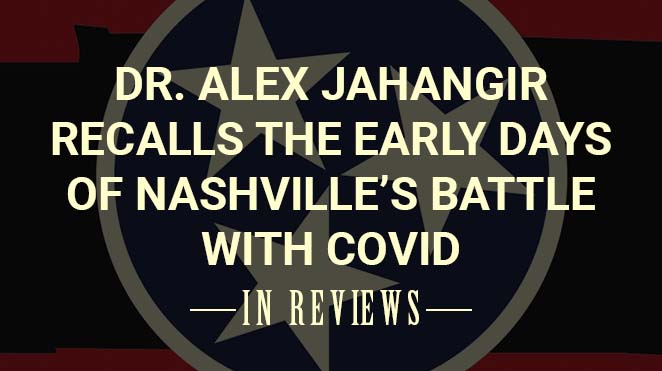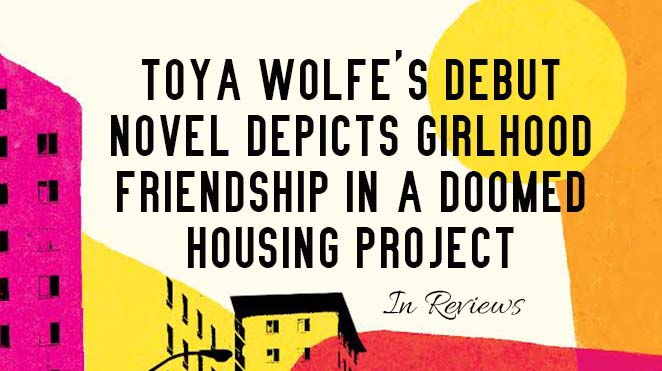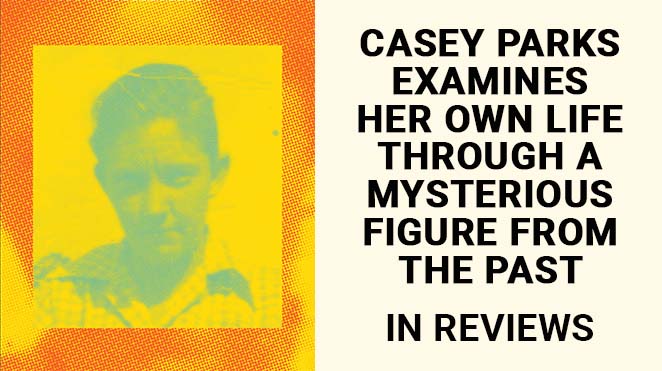1957年,当我8岁的时候,我对我的主日学校老师杰菲·卢·比克罗夫特小姐骂了个恶语。我没有当着她的面骂她,但那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词,显然是当时我心里最难听的一个词,这就是从那以后最重要的事。
 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件突然发生的事。我想我当时微微向前倾,对一个我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耳语了几句。杰夫小姐是孟菲斯故事讲述者联盟的成员,以能将圣经故事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闻名。她突然停了下来,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既像殉道者又很有说服力的柔和声音说:“奇普说完之后,我们再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件突然发生的事。我想我当时微微向前倾,对一个我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耳语了几句。杰夫小姐是孟菲斯故事讲述者联盟的成员,以能将圣经故事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闻名。她突然停了下来,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既像殉道者又很有说服力的柔和声音说:“奇普说完之后,我们再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算不上是公开的撕裂,但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我是个好孩子。我一直努力做正确的事。每个人都认为我在幼儿园的耶稣诞生表演中是一个特别警惕和崇拜的牧羊人。四年来,我一直把小学的品行成绩带回家。我曾是一名童子军。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1950年代的家庭一样奥齐和哈里特,把它留给海狸,父亲知道最好顺从的世界——我的家庭是礼仪的典范。我的父母在教堂里很活跃,但他们既不阴沉也不道貌岸然。他们穿着得体,和其他家长一起打桥牌。我们有一辆别克Roadmaster。在书生气和内向的一面,我学会了如何用语言来拯救社会:虽然我一直是老师们的宠儿,但我也喜欢帮助同学们做作业,我能让人们发笑。大人们似乎都信任我。
但是在那个主日学校的教室里,一句话,我的世界突然崩塌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自己的地方,我熟悉的地方——一间宽敞的、阳光明媚的二楼房间,里面有三四排精心摆放的小木椅,杰夫小姐的桌子放在一边,桌上放着她花园里的一朵花。过了一会儿,一幅可怕的黑幕像蝗灾一样掠过我的视野。我设法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感觉受到了侮辱。
杰菲小姐继续用她惯常的戏剧动作,睁大眼睛,调节音量和语调生动地叙述着。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破裂,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开放的伤口。没过多久,我们唱起了《爬,爬上阳光山》,然后鱼贯而出,开始教堂礼拜前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我永远也不知道杰夫小姐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拦住了我,想私下说几句可能改善我状况的话——我呆在一群人中间,低着头,以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一小时后教堂关门时,消息已经传开了。我记得我站在人行道上,几乎大小便失禁,试图让自己隐身,等着父母过来把我和妹妹推到车上。
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就是事情发生的时间。
我和班上的几个男孩站在楼下,喝着旁入口附近平台上的可乐机里的可乐。没有人提到任何事情;似乎没人在意。似乎没人在意,直到唐尼·克虏伯毫不留情地像往常一样,嘲笑地哼了一声说:“她真的捉弄你了。”他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其他人。说完之后,他带着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矛盾情绪笑了起来,表明我们都在嘲笑她,但又确定我也被牵连其中——清楚地表明我没面子。
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但我把杰夫小姐称为我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词,是任何一个聪明、有教养的白人男孩对他的主日学校老师、善良的白人女士所能说出的最轻蔑的称呼黑鬼!”
一小时后教堂关门时,消息已经传开了。我记得我站在人行道上,几乎大小便失禁,试图让自己隐身,等着父母过来把我和妹妹推到车上。但噩梦开始了,杰菲小姐穿过人群朝我走来,眼睛明亮而热情。她紧紧抓住我的上臂,凑到离我脸几英寸的地方,低声说:“谢谢你叫我黑鬼。”
我不知道父母究竟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知道我摔倒的。惩罚了。对如此严重的罪行来说,仅仅在屁股上打一下是不够的,而且我还没有到被禁足的年龄。我还记得当时持续不断的冲击波,包括那句极其严肃的“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做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但当我让父母失望时,她的脸上就变成了一张痛苦的面具。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她紧抿的嘴唇可能被蚀刻得更加牢固。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明白1957年主日学校那节课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父母和他们的教会朋友看来,我说的话是错的,不是因为它卑鄙,而是因为它就是卑鄙常见的.从我嘴里蹦出来的这个词的问题既不是它背后的敌意,也不是它可怕的含义,而是它在文明社会中没有被使用,没有被像我们这样的人使用。
在这其间的岁月里,脏话来了又去。我相信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对别人发出嘘声或被扔向别人,但即使那样,我也感到某种同谋。
从我父母和杰夫小姐那里得到的教训很清楚:语言必须像城市公共汽车或廉价商店的午餐柜台上的座位安排一样严格。谁也听不出这句话中的恐怖;没有人意识到现在是教与学的成熟时机。他们听到的不过是一种社会无礼,一个男孩的无礼。残酷的事实可能正在酝酿之中,但它们还没有通过前门被接受。回想起来,不仅因为我希望这是真的,我感觉我的父母——好人、善良的人——很想多说点什么,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
在20世纪60年代,我所在的教堂恰好是城里少数几个欢迎黑人参加礼拜的教堂之一。但在1957年的那个星期天,我只听到了关于小石城和“融合”的零碎旁白。那一天,所有那些焦虑的暗流和不确定性与我自己对身份的微妙把握融合在一起。我所了解的世界,在我所能信任的范围内,正在失去控制。混乱的威胁。我感到完全无力。
没过多久,这件事就被遗忘了,或者被埋葬了。我高中毕业,在下一个动荡的时代开始上大学。我开始积极投身民权事业。我游行,我投票,我加入。我第一次开始把非裔美国人算作我的朋友。
但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明亮的十月星期天,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它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十月星期天,我听一位黑人朋友的祖母说,我“用她的名字”称呼了杰夫小姐。
随着媒体形式的扩大,今天的谩骂激增,变得更加尖刻。在这其间的岁月里,其他的不好的词来了又去。我相信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对别人发出嘘声或被扔向别人,但即使那样,我也感到某种同谋。我们看到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被公开谩骂——不是因为他的政策,而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肤色几乎不加掩饰的发自内心的厌恶。这令人不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坚强、聪明的人,还因为这种尖刻的话现在更难收回,更不用说赎罪或改变了。它们可以在公民身体和个人灵魂中溃烂几十年。
十月的那个清爽蔚蓝的星期天早晨,也许是我童年结束的开始。这无疑是在我的清白棺材上钉了一颗钉子。对于一个热爱文字的孩子来说,多年以来,这都是对我对语言的细心、准确和救赎力量的信任的背叛。
我错过了“共产党员”这个词的广泛使用几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其他旨在伤害的绰号:“基佬!同性恋!乡下人!恐怖!”虽然每个特定的词都很重要,也有特定的含义,但很明显,那些发出谩骂声的人甚至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背后的仇恨源于对自己没有代理的恐惧,他们被世界上的唐尼·克鲁普斯(Donnie Crupps)激励着发声。
但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或多或少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终生的周日早晨的悲伤。

哈德利·胡里的诗出现在科罗拉多审查,图像,阿巴拉契亚遗产,打造,青山审查,海岸,以及其他期刊。他是孟菲斯人,住在路易斯维尔,担任电影编辑失去了海岸审查在加州的新港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