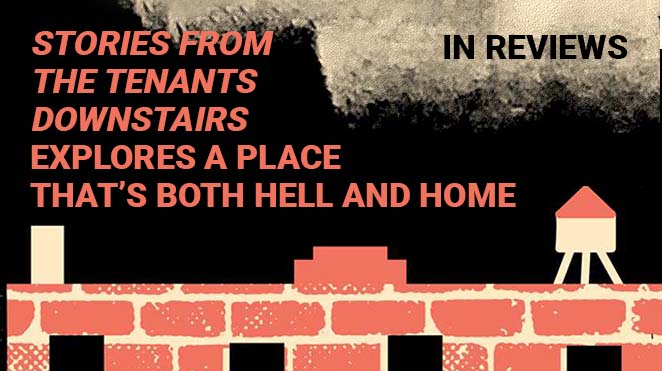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诗人和散文家,Jenny Qi为她的写作带来了复杂的视角。她的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努力谋生。齐在16岁时进入范德比尔特大学,虽然她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她也不得不应对母亲的绝症,不知怎么地,她一边上学,一边回家拉斯维加斯帮忙照顾,她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大西洋.

尽管齐淇在大学期间作为一个活跃的作家,学习马克·贾曼并担任诗歌编辑范德比尔特的审查在美国,她的主要关注点是科学。后来,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获得了生物医学博士学位。正是在读研期间,她开始动情写作,将自己的悲伤和回忆倾注到诗歌中。这些诗歌,连同最近探索一系列问题的作品,汇集在她获奖的处女作集中,焦点.
齐的文章曾出现在《纽约时报》而且文学的中心.除了写诗和散文,她目前正在翻译她母亲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她住在旧金山,在那里做顾问,跟踪肿瘤研究的进展。她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关于你父母的诗,尤其是关于你母亲去世的诗,非常个人化,发人深省。在你的作品中,你会不会因为透露太多而感到苦恼,会不会因为讲述父母的故事比他们想要的更多而感到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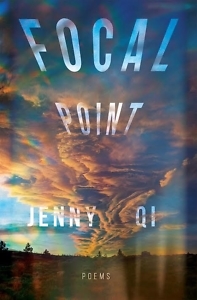 詹妮气:杰弗里·金曼写了一篇很好的早期评论焦点在强迫读者在书中,他强调要区分讲话者和作者,我非常欣赏这一点,现在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一点。毕竟,诗歌并不完全是非虚构的,虽然诗歌中经常有自传元素,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百分百真实的。
詹妮气:杰弗里·金曼写了一篇很好的早期评论焦点在强迫读者在书中,他强调要区分讲话者和作者,我非常欣赏这一点,现在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一点。毕竟,诗歌并不完全是非虚构的,虽然诗歌中经常有自传元素,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百分百真实的。
但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确实担心,特别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回避谈论任何负面或个人的文化。但这正是我写作的原因,我写了很多这样的诗不是为了发表它们,而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年轻时的我写的,我在一些艰难的经历中感到深深的孤独,我必须相信这有某种价值。我提醒自己的另一件事是,尽管有文化的这一方面,我妈妈也写了非常个人化的作品,所以我希望她能理解。
米兰:在《我们的复数》(The复数of us)和《两种疗法》(Two cure)这样的诗歌中,你用文字游戏来探讨更深层次的主题。语言经常是你写诗的火花吗?
气:是的,我想是的,比什么都重要。我喜欢思考语言,思考不同学科对单词的不同定义,不同语言对单词的翻译,同音异义词和同源词,以及增加或删除一个字母如何完全改变一个单词。通常,一首诗来自于对一个单词或短语的反复思考,有时如果我沉迷于一个单词,我会查字典,然后开始写一首诗,探索这个单词的各种官方定义。
第一首诗最初的标题是“焦点”,以一段铭文开始,包含了对焦点的各种定义。我在学校也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西班牙语,虽然我现在已经很生疏了,但我在诗歌中对西班牙语的某些部分思考了很多,并在这本书中有所探讨。也许我最喜欢西班牙语的一点是,“to be”有两种基于时间性的表达方式(爵士vs。会对于连续和瞬态)。
米兰:焦点包括一些中文原版译文,尤其是11世纪诗人苏轼的一首诗,你现在正在翻译你母亲的作品。你对翻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你觉得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气:说实话,翻译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非常费力。还有很多词是不能完全翻译出来的。特别是在诗歌中,要把节奏和意思都弄好,或者至少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因为中文是一种如此简洁的语言,有很多同音异义词,而我往往会在节奏方面犯错误。但因为我喜欢思考语言的怪癖,这些挑战也让我觉得翻译很有趣,尤其是在小范围内,比如诗歌。然而,我对翻译工作感到最大的吸引力是需要保护我的家族和文化历史。
米兰:受到“脉动”夜总会枪击事件启发的《共性》(Commonalities)和涉及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关于脸》(About Face)等诗歌,比你的其他一些作品更明显地具有话题性。是什么把你吸引到这些问题上来的?你觉得有责任承担这些责任吗?
气: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写诗,它通常是对世界上的事件和不公正的反应,写诗或写故事是一种处理我对这些事件的情绪的方式。我最早的一首诗,写于我12岁左右的时候,来自于我在国家地理关于世界各地的性交易和奴隶制度。我一直痴迷于理解我们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类,或其他生物的,如此糟糕,如此短视,以及我们如何超越这些,我相信故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我们共有的人性。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非常关心LGBTQIA的权利、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性别不平等和环境不稳定等问题。我认为,一旦我多少处理了自己的悲伤,我就很自然地回到了这些话题上。
米兰:你作为科学家的训练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你认为它调整了你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视角吗?
气:如果你在几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不。但现在我意识到,当然是这样。这在我使用的隐喻和词汇中很明显,在我一些诗歌的主题中也很明显,甚至在我分析事物的系统方式中也很明显。我思考了很多关于系统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是如何成为系统的一部分的,我们在这个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这个系统中我们能或不能控制多少,我们自己又是如何成为细胞系统的。我的科学背景可能帮助我缩小视野,识别联系和模式,看到森林而不是树木,如果你愿意的话,尽管这也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不太受强烈情绪的严厉控制。如果我停下来,在人类历史或地质时代的背景下,或在更大的宇宙背景下,思考特定的人类问题,有时它可以帮助缓和我可能倾向于感到的存在恐惧。
[阅读节选自焦点在这里.]

玛丽亚·布朗宁是第五代田纳西人,在埃林和纳什维尔长大。她的作品已刊登在格尔尼卡,洛杉矶书评,《纽约时报》.她是……的编辑米兰.
标记: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