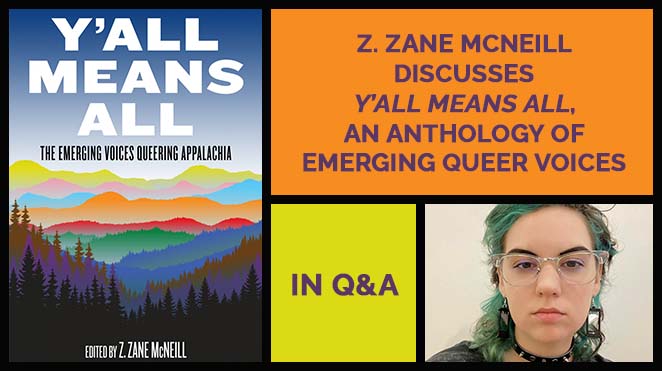根据我以前的笔记国家地理鸟类指南,1980年11月8日,我在伊利诺伊州巴林顿山的克拉布特里自然中心看到了一只号手天鹅。一个生活的鸟.

我母亲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医院住了将近两个月。
去年9月,医生给她手背的静脉注射了一针,开始注射可能挽救她生命的点滴时,我就在她身边。她含着泪看着我说:“我从没想让你看到这个。”
我见到号手的那天,她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我和哥哥一定是把父亲拖到克拉布特里去了,几年前,我在父母的陪伴下,第一次在那里钓到美国卤水。
我们所熟悉的疣鼻天鹅可能会在比尔特莫尔庄园的湖面上翩翩起舞,它的脖子呈优美的曲线,而号手则是一名战士——昂首挺胸。它的账单是黑暗和功利的。
20世纪30年代,号手天鹅濒临灭绝,只剩下69只。现在它们已不再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但就像鸣叫的鹤一样,看到它们,很难不感到恐惧和钦佩。
就在同一天,一大群沙丘鹤也受到栖息地丧失的威胁,在我们头顶上方约6英尺高的一片秋天的黄色草地上飞行,对着苔原尖叫,警告冬天即将来临。
10天后,母亲去世了。
那时,我在一家公司做排字和校对《湖村日报》那是康涅狄格州西北角的一家周报,尽管我在高中时拒绝学打字。我母亲吓坏了,坚持认为我需要一种“可销售的技能”。与此同时,她还告诉我,我应该成为一名作家或演员——她为自己设想的职业。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想象。她写了两本小说,但从未提交,她和我父亲曾在孟菲斯的一个小剧场团体里演出。
通常她希望我成为一名教师,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更好的是学者,就像我的历史教授哥哥一样。
我母亲无情地强迫他在密西西比大学读医学预科,直到他反抗,成为历史专业——这远不及我在肯特州立大学毕业后在西北大学附近街头游行时的反抗。但是反叛有多种形式。
如果我只学会打字,而不是念叨着“见鬼,不,我们不去”,我可能就能通过上世纪70年代搬到纽约时参加的一系列打字测试。如果我当时听从了她的建议,我在出版界拥有杰出的职业生涯,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
但在我母亲身体迅速、最后一次走下坡路的时候,我正在康涅狄格州的东迦南租一间小房子,靠打字为生。我有一匹漂亮的帕罗米诺混血阿拉伯母马,名叫凯西,还有一只大牧羊犬,名叫山姆·休斯顿。
当时我正坐车去芝加哥的拉什长老会医院。
随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拜访,一周又一周,我发现母亲和一个勤务兵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她的胳膊挽着他的胳膊。她会拍拍他的手,甜甜地跟他说话,就像她自己的母亲一样,对每个人都甜得令人作呕。这完全不像她。
她的肿瘤医生——一个女人——会带着一群医科学生走进来,告诉他们她的病情,检查她的体温,然后扫地出门。但我母亲认为一个可爱的年轻住院医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想要杀了她。
她总是以一种奇异而神奇的方式看待生活。她相信鬼魂和预兆。她痴迷于各种预兆,总是希望能骗过命运,活下去,但更多的时候,她看到了有说服力的迹象,表明她不会。

一天,我发现她坐在房间外的椅子上,看着大厅里的落地窗。一架飞机飞过,飞向卢普附近的中途机场。
“我看到飞机撞进窗户,然后又飞了出去,”她说。“我想他们就这样消失了。”
她的医生告诉我们癌症已经扩散到她的大脑。
几天后,她坠毁了,但他们设法救活了她。父亲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我。
在最后一次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飞机在午夜后抵达,我因为列出了世界上以M开头、人口达到数百万的城市而赢得了一瓶葡萄酒。我唯一错过的是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
9月的那一天,当她得知尽管做了第二次乳房切除手术,癌症还是扩散了的消息时——她曾以为自己已经没事了,但已经过去两年了——她惊慌失措地从芝加哥市中心坐火车回家。她开车去了她看到的第一个教堂,圣雷蒙德德Peñafort天主教教堂,奇迹发生了。
在教堂里,她找到了教区牧师露神父,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独自一人,好像一直在等她似的。他们成了朋友。他抚慰了她的灵魂,给了她力量。但他救不了她。
露神父去医院看她了。到那时,她已经有大约10亿根管子了,但当她看到他时,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她稍稍坐了起来,向他伸出手,张开双臂。他弯下身子,把她——她所有的管子,她的全部——抱在怀里。
我不得不离开房间,到大厅里去哭泣。
不久之后,她又撞车了。他们又使她苏醒过来。
在第二次复苏之后,她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她管得太紧,说不出话来。
“我想死,”她写道。
父亲坚持认为,她只是把“我”和“想要”中间的“不要”漏掉了。
但我现在长大了,见过太多的死亡,知道她说的是她想说的。
在那张纸条之后,我母亲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只有间歇性的意识。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死,但我们默默地希望她能有个了结。我父亲和我在一个家庭小房间里的硬床上度过了一夜又一夜。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不再否认,没有希望了。
最后,在床上睡了那么多晚上,我坚持要回家好好睡一觉。
黎明前我们接到了电话。
最后一次,我和父亲去市中心。他不忍心走进她躺着的房间,所以我进去了。

我一直看着她,直到我能忍受为止。她胳膊上,鼻子上,嘴巴上都没有插管。她不再痛苦了,但她也看不到平静。她看起来像死了一样,神魂颠倒。她享年62岁。
露神父在我们飞往达拉斯参加葬礼之前举行了一场仪式,葬礼在橡树崖的月桂地公墓举行,这是太多家庭葬礼中的第一次。
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知道她是个信徒。”
我点点头,但我一直在想。我的母亲是典型的怀疑论者,她作为一个充满想象力和高度紧张的女孩,忍受着地狱之火和硫磺浸信会的说教。小时候,她把每句话都当真。作为一个母亲,她发誓永远不会让她的孩子遭受那种折磨。
不管她死时是否信教,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在她死前我看到的那只活鸟是号手天鹅。我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因为我有自己神奇思考的倾向。
因此,我相信我的母亲像一只天鹅一样,乘着凛冽的风从北极出发了——狂野、自由、美丽——向南飞向充满生命的温暖水域。

版权所有©2022由Lyda Phillips。版权所有。莉达菲利普斯他是一位在孟菲斯长大的资深记者,曾在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学位。作为两本青少年小说的作者,她在返回纳什维尔之前曾为合众国际社工作。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