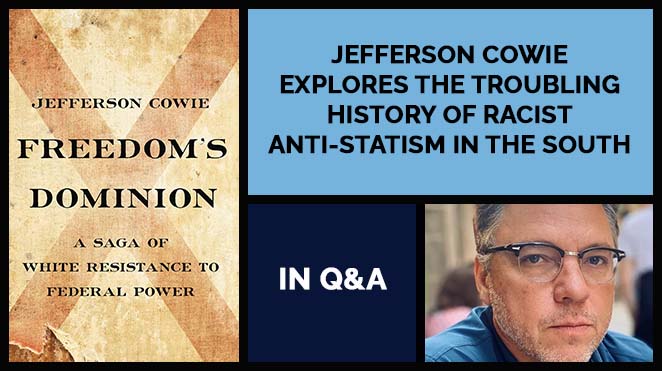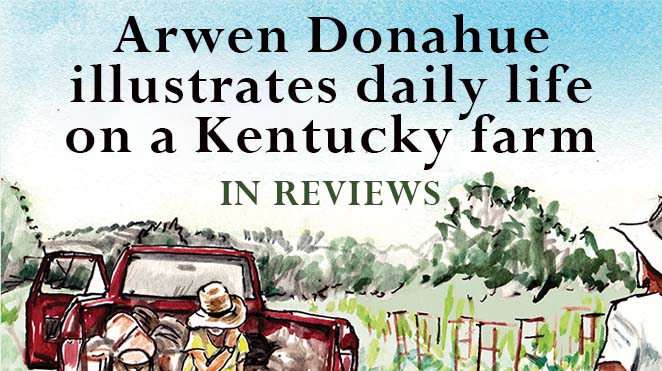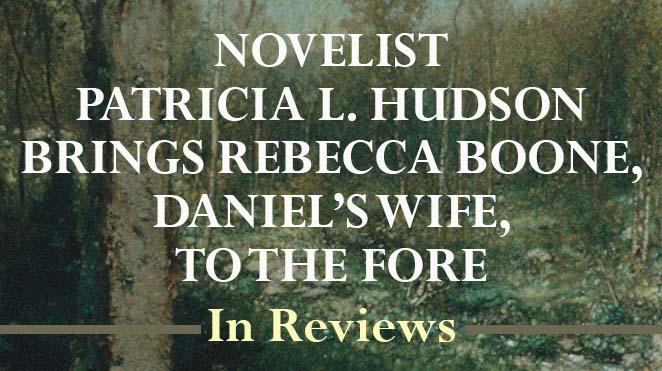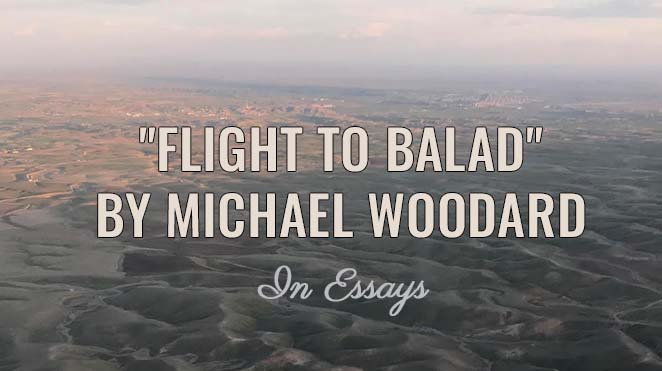杰斐逊·考伊,范德堡大学詹姆斯·斯塔尔曼历史学教授,是当今学术界最有天赋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伟大的例外:新政与美国政治的局限,对20世纪美国政治的全面重新解读;屡获殊荣的《活着:20世纪70年代和工人阶级的最后日子》关于美国政治文化中阶级衰落的生动叙述;以及跨国的历史资本流动:RCA七十年来对廉价劳动力的追求它描绘了一家公司在四个城市,两个国家的搬迁,以及巨大的社会动荡。
考伊的文章、评论和观点文章已经出现在《纽约时报》、《美国展望》、《政治家》、《新共和》、《高等教育内幕》、《异议》以及其他受欢迎的渠道。他的最新作品向南移动,通过阿拉巴马州东南部巴伯县引人注目的故事,探索了美国种族主义的自由思想——最常见的是白人对联邦权力的反抗。
考伊最近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你坚持认为,当白人一心想剥夺他人的自由时,我们会认真对待“自由”或“自由”之类的词语,这令人震惊。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仅仅是华丽的辞藻或“意识形态的粉饰”。在你看来,为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些表达理解为一种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杰斐逊考伊:自由是美国信条中最基本的方面。然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援引“自由”,不是为了支持充满希望的理想,而是为了证明统治或压迫是正当的。当我们听到它被用来为不愉快的结果辩护时,我们可能会想,“这只是在呼吁美国的核心理想,以证明说话者真正想要的东西。”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美好的自由中也有阴暗,令人不安的一面。
西方的自由观念来自古代的奴隶社会。获得自由并不仅仅是去不做奴隶,也要有自由奴役。自由关乎权力和能力。如果我们把支配他人的自由这一阴暗的观点,与我们喜欢的自由的一系列东西——各种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放在一起,我们最终会得到一个总体上积极的想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和有问题的元素。
然后,如果这种更复杂的自由理念在一个迅速发展的奴隶和定居者殖民社会中被释放出来,比如美国南部,我们最终会得到一个有效的自由理念,其中包括窃取土地的自由和奴役他人的自由。它还包括反对阻碍这些自由的联邦政府。如果你考虑一下今天的自由是如何被唤起的,它经常与权力的集中、偏执、不宽容、土地饥饿、暴力和好战形式的枪支权利共舞。想想我们的自由理念有多少是建立在占领整个大陆的基础上的。
哲学家们喜欢为自由创造简洁的定义,但在实践中,它最终是一种更为妥协和复杂的东西,对历史学家来说,它相当有趣、丰富和生动。自由的支配这是对18世纪诗人和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长篇回答。“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我们在黑人司机中听到了最大声的自由呐喊?”答案在于自由与权力的交织,以及人们强烈要求不受这种自由的约束。
米兰:你为联邦(国家政府)权力的使用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无论这些权力是有缺陷的、有限的还是妥协的。从19世纪开始,联邦权力一直的以这种方式保护公民自由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让你得出这个结论,它是如何与黑人激进主义的传统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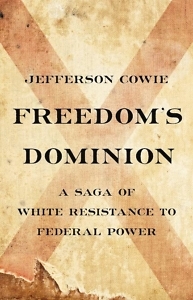 考伊: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黑人选民认为联邦权力以重建或民权立法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了自由,而当地白人认为联邦权力是联邦暴政的长臂。
考伊: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黑人选民认为联邦权力以重建或民权立法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了自由,而当地白人认为联邦权力是联邦暴政的长臂。
如果要给失控的白人自由思想踩刹车,那就应该是联邦政府来踩刹车。事实上,这个项目开始于试图找出当地对联邦当局的敌意背后的原因。当联邦政府试图让白人停止窃取土著土地时,即使是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或在重建时期保护黑人的公民权,或在现代民权时代派遣联邦当局进入当地县,这些都被视为对上帝赋予白人的自由的侵犯。
整个政治生涯都是通过大声疾呼白人自由在联邦权力手中消失而成就的。来自巴伯县的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他的地方、州和全国职业生涯中谴责“联邦暴政”,批评民权法案是“自由背后的刺客之刀”。联邦政府的一点点干预,即使失败了,也会带来大量破坏性的白人自由。
我们有很多理由对联邦政府对公民权利和投票权的执行表示深深的怀疑。但是,通常情况下,黑人积极分子的想法是利用地方斗争把联邦当局拉到他们这一边。在黑人自由斗争中,几乎每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事件都是试图将整个公民权理念联邦化。虽然我了解联邦政府介入的阴暗面,从主要的刑事过失到监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但在我的故事中,联邦政府是笨拙的英雄。
尽管联邦政府存在种种失败,但公民身份往往取决于联邦权力的意志。然而,联邦权力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自由即将丧失的恐惧。这就是在重建时期经常被表达为对“黑人统治”的恐惧。从投票权到公民权,黑人的政治自由取决于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建立联邦公民权的理念。相比之下,白人的自由取决于将公民身份保持在地方和州一级,在那里公民身份可以受到控制。
米兰:我们在书中看到一些例子,种族主义的反中央集权主义者有时很乐意利用联邦政策来追求对他们有利的地方目标。他们只是伪君子,还是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他们的头脑中工作?
考伊:联邦权力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毫无疑问地站在白人一边。时期。句号。但有时候,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是我故事的中心。这是白人对他们的自由受到侵犯感到非常不安的时候。
在书中,我把我正在探索的地方白人自由称为“种族化的反国家主义”,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当地白人会像其他人一样,利用他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政治权力。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帮助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就像主导的历史趋势那样,一切都没问题。然而,阿拉巴马州一直担心的是,如果联邦政府能搅乱任何一件事,那么它也会搅乱种族关系。所以总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例如,整个南方的当地白人对罗斯福和新政非常满意。至少在新政开始出现之前,这是有效的,因为它可能是为了其他人而不是他们,或者当它看起来可能会挑战根深蒂固的地方和国家权力关系时。然后就发生了争吵。
白人自由的捍卫者声称,如果你不能成为主人,那么你就没有自由;如果政府不在你这一边,那么它就不应该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政府侵犯了白人自由所带来的心理上和现实上的力量,许多人宁愿不看政府——即使它对他们有所帮助。
米兰:你最近的几本书是对时间跨度的广泛综合。大例外证明了辉格派或自由主义版本的美国历史——那些假定朝着某个目标稳步前进的版本——错过了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这本书证明了一个广泛的延续性,它深深植根于19世纪,从印第安人迁徙到后民权时代和现在。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伴作品。想法吗?
考伊:好问题。在我的上一本书中,我指出,新政和战后时代(大约1936-1978年)是长期政治分裂历史的“例外”,这种政治分裂不时出现在前后时代。南方和种族在那段历史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民主党可以动员南方种族隔离主义的白人和黑人,同时仍然与被称为“坚实的南方”的政治集团保持政治联盟。在这一时期,联邦权力被勉强接受。虽然有人担心新政的联邦权力可能会破坏种族关系,但它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白人的恩惠,而不是对他们自由的威胁。
然而,当民主党开始认真对待民权问题时,这个联盟就崩溃了。民权和投票权法案开始了南方白人从民主党到共和党的缓慢转变。巴伯县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全国政坛的崛起表明,南方白人从过去的民主党转向了未来的共和党。正如我在上一本书中所说的那样,在美国政治中,把种族作为一个主要的分裂点在当时看来是令人震惊的,但这更像是回到了现状试图在美国掩盖种族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重建时期的白人所说的从联邦权力中“救赎”。选举权和公民权岌岌可危。但这并不新鲜,它正在回归常态,再次将白人的自由从联邦权力中拯救出来。
我们仍在进行一场长期的智力斗争,以使我们对一切事物的思想去殖民化——包括自由。你所提到的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弧线,植根于一个充满问题的深刻的、松散的过去。这就是1619工程正想说。这就是我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可怕的是,只有当种族不被允许成为一个因素时,我们才能认真对待经济正义。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小心翼翼地控制种族问题,这样他就可以通过劳工立法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安全,这在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发生过。
米兰:你能多谈谈你选择阿拉巴马州的巴伯县来写这个故事吗?在你的致谢中,你提到"巴伯郡找到了我"这读起来既抒情又神秘,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命运。我很想多听听。
考伊:故事开始于纽约州北部一个零下20度的日子。天气太冷了,我开始幻想着把家具烧掉取暖。当时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我的孩子们瑟瑟发抖地问我:“我们春假要去哪里?”“哪儿也去不了,”我回答。错误的答案。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都挤进了我们的小车,驶向墨西哥湾沿岸。我们一离开主要的高速公路,就经过阿拉巴马州东南角的一个叫尤法拉的小镇,加满油,向海滩做最后冲刺。在庄严的林荫大道上,有一些战前风格的老房子。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田园诗般的场景。
我这位历史学家的蜘蛛般的感官立刻开始兴奋起来。我知道façade背后有一个迷人的故事。“这是什么地方?”开车经过小镇时,我问妻子。她开始在谷歌上搜索,然后说:“我不知道,但他们直到1991年才举行了第一次融合高中舞会。”
自从我写了一本关于新政的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白人对联邦当局的反抗,我开始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可能是什么。因为我很清楚,你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挑选多少数据来讲述一个故事,所以我决定,一个小农村县与联邦权力冲突的挑战,将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它带来了研究上的挑战,智力上的限制,以及,我希望,叙事上的阴谋。
因为我之前的一些工作是关于乔治·华莱士的(在我70年代的书中,Stayin”),大多数人会认为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但当我回到图书馆时,我立刻去查阅克里克印第安人的资料,我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我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华莱士是那里的人因为我仔细研究了年表。当我找到他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命运。
幸运的是,我后来搬到了范德比尔特,我可以很好地使用位于蒙哥马利的阿拉巴马州档案馆——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我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有意挑巴伯县的茬,我已经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了。我希望读者能把它看作是美国成千上万个有类似故事的地方的代表。乔治·华莱士当然是这样理解他的家乡的。对他来说,这些与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的选民有关的故事,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美国故事,一个会在全国选民中产生共鸣的故事。

彼得·库里拉(Peter Kuryla)是纳什维尔贝尔蒙特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他在那里教授各种有关美国文化和思想的课程。他也是美国思想史协会(S-USIH)的定期博客作者。
标记: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