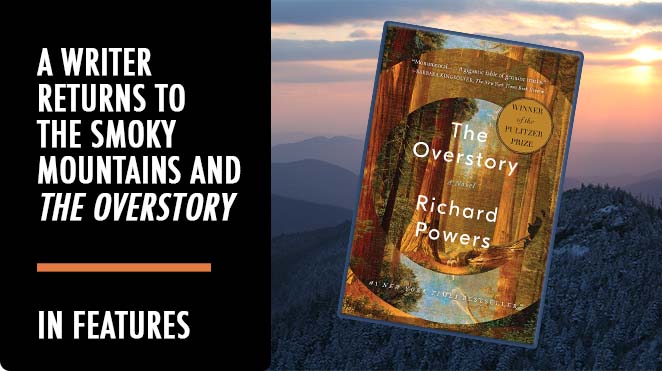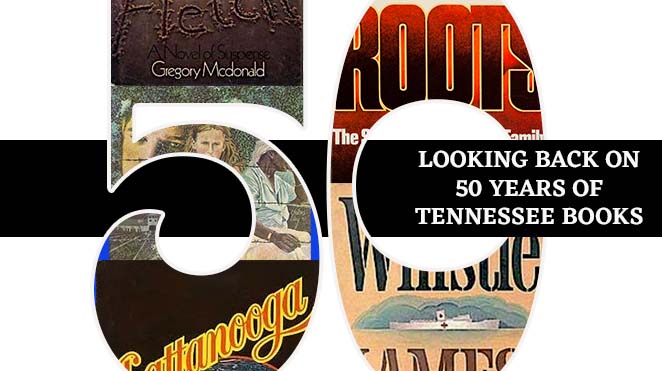我来这里山上我经常干的事——逃离我的生活和对自己的本质。或远离我对一些真实的生活和知识的一种错觉。或远离我的生活震耳欲聋的反馈和向更深的监听站。但是我真的跑向或监听,当我来这里?
 我知道我来这里,理查德·大国的斯莫基山脉,重读小说的上层。自从我和我的丈夫在当天早些时候,绕组熟悉的盘山路和狭窄的扣人心弦的道路导致一个微小的出租小屋,我无数次问作家的有关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小说——一条线,说的许多复杂的世界树,又在我的思想一个循环:
我知道我来这里,理查德·大国的斯莫基山脉,重读小说的上层。自从我和我的丈夫在当天早些时候,绕组熟悉的盘山路和狭窄的扣人心弦的道路导致一个微小的出租小屋,我无数次问作家的有关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小说——一条线,说的许多复杂的世界树,又在我的思想一个循环:
“如果你的思想只稍微更环保的事情,我们就会淹没你的意思。”
我假装不知道写作的巨大的努力的上层拿出的权力,但是我知道年底这段时间他背井离乡生活在西海岸和烟雾缭绕的搬迁,迫使这些原始森林恢复存在的。他告诉《纽约时报》他变得如此排水的经验,他怀疑他会写另一本小说。
但到了2021年困惑一本书,打开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设置在烟雾缭绕。人们很容易读这部小说作为驱逐拦蓄悲伤的气候大量毁灭力量巧妙地从事的上层。人们很容易把它作为作家的证据还不能离开特定种类的森林。
小说是一个生态系统。有些沙漠,建在干旱的条件下存活。别人推进河生活繁多,多产的和快速的。的上层就像烟雾缭绕,郁郁葱葱的主机歧管居民,一些可知漫不经心的游客和其他人难以捉摸,难以理解。世界是从容不迫的,但一定强度的目的。这个包络相关字符的生态系统,人类和非人类,似乎没有开始或结束。在其丰度,强度,其奇异性——这些礼物的浸的上层真实的产品。
小说的第一部分,“根”,介绍了九个主要人物在一套短故事,每一个令人难忘的和引人入胜的,每个设置其角色的命运与树木。短暂的开场白开始于一个简单但重要的形象:
”一个女人坐在地上,靠着一棵松树。其树皮对她带来巨大压力,努力生活。其针气味的空气和嗡嗡的木头。她的耳朵调到最低频率。树说,单词在单词。”
这部小说邀请我们去调自己尽我们所能,我们不习惯听到声音——非人类的声音填充我们的世界。“合唱的生活木“显示了这个女人她的人类感知的局限性。他们告诉她,“我们所有你想象的方式…总是截肢。你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你错过了一半,等等。总是有尽可能多的地下的上面。”
我光着脚站在小屋的门廊,熟悉的树木的树冠世界包围。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独自站在富人安静的黑暗,开始一个熟悉的过程,让都市风尚的自我,我国内的自我,简单。只需要这山上空气,喂我的老朋友,这些熟悉的树木。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他们给我回到我自己的时刻。
但低于我,从黑暗的,我听到的模式清晰、响亮的林下叶层的步骤。我知道这些步骤不是人类。我知道他们不是由小爪子。我知道他们正在发生略低于我,我并不孤单。空气加压生长,我知道我观察到。
这是我说我想要什么,我告诉自己。不仅仅是人类世界的缺失,但非人的存在。我下面的步骤重复模式,紧随其后的是一段厚安静。我听到没有更多的步骤,但没有准备好。我从玄关栏杆,回到我的明亮的人类世界。
* * *
在另一个抒情小说中通道之后,权力的地方他的九人的主角之一,躺在森林地面并查找到高树冠的白色梳理塔在他的世界。这些树交流”在媒体自己的发明,“改变这个人,因为他对他们打开自己。”他们说通过针头,树干和树根。他们在自己的身体的历史记录每次危机他们经历。”
当他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他们给一个警告:“长答案需要长时间。而长时间正是消失。”Soon trees from farther afield join in, offering their own message: “The world is turning into a new thing.”

南部边界附近的大烟山国家公园,沿着奥克那露提河位于一个特定的石头,银行完全高度和水平度作为写作上。我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里:阅读,潦草,重新调整自己与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考虑未来。我独自来这里很多年了,然后小心翼翼地描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格雷格,我的男朋友。小心翼翼地,我带他在这里。他向我求婚。
直接从我的石头坐在树在奥克那露提我相信我知道。十年前,我叫她达芙妮树。是的,她的裙子暴露缠绕根让她陷入对河流的边缘,但他们在mid-turn似乎抓住了她,一样的弧度和形状鼻子,像臀部。是她逃离阿波罗?当然,那是我的投影。最后我希望是被抓。我跑到山,任何机会我可以沉浸在我的孤独的生活。格雷格不知道此刻他向我求婚,我唯一的证人是达芙妮。
到那时,就像的上层树木宣称的合唱,我变成一个新事物。我邀请他到我的河岸。我欢迎她的见证。我只能希望她欢迎我的。
* * *
小时深入安静的工作,我达到我所知道的是时间的核心。与格雷格上涨在公园里的一天,我回到门廊,阅读和写作在角桌在发光的绿色树冠。我似乎越过门槛我渴望十字架,软化回到我的动物本性。我呼吸更深。我想我也绿化。
我听到熟悉的步模式下我。声音很响亮,我知道,当我往下看,我将看到这种生物的林下叶层。
熊,现在直接脚下,是更大,比任何我遇到熊的烟,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目击事件都发生在模糊距离。矮胖的婴儿,那些似乎太高兴地嬉戏,构成任何旅游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欣赏他们。
这只熊是巨大的黑色,但布朗的结块污垢粘其皮毛,arch-backed heavy-pawed,花的时间在长满苔藓的地上几英尺。我不怕,但我能感觉到我的电池充电,充满的兴奋,元素。
缓慢,我收集物品,机舱内退回,以下从windows熊进展到小,陡峭的清算隔壁我的小屋和另一个之间。现在在阳光充足,熊停顿,嗅空气和做决定我的位置和邻近的小屋,一个略大的名叫里斯,只有几码远。我看熊木材穿过剪草和到里斯门廊。四年前,格里格和我结婚彼此门廊,一小群包围的家人和朋友。
熊发射到它的后腿,支撑本身到走廊栏杆上,向我展示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小和高度。打雷回落到玄关地板,只有再次暴跳,攻击表面上垃圾容器四周建起防护措施(我的邻居必须离开无担保)。暴力,呼应叮当的金属,咕哝着,从本熊的搏斗的奖,然后泄漏袋垃圾在玄关,定居下来,在前门的欢迎宴会。
一起,四年前,我动摇我亲爱的阿姨,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全新的继女史蒂薇·尼克斯描绘她最深的,最疯狂的“里安农”法术,在同样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暴席卷机舱,弯曲周围的树木在阵风吹来,突然瞥见氤氲的阳光,下雨黄金。
记忆的洪水我看熊声称它的位置。在那一刻,我可怜的邻居抵达他们的卡车。想象他们的冲击。这些退休人员,从他们的度假乐趣,找到这个巨大的阻止他们的前门。从我的窗户,我看徒劳的僵局。它,更好的一部分,一个小时。邻居们他们的喇叭。熊甚至不退缩。没有着急。然后,我突然不适,邻居们放弃。 They drive away. And this is the moment when, for me, the experience begins to turn.

我已经开始尝试的话我会告诉的故事。当我观看和等待,故事开始向外分支从现在的亲密的核心经验。它开始扩张,合同,变身。它将观众的情绪和习惯学习,适应它的目的,适应我的过程。已经给我回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再次,因为所有stories-in-process做。已经我野化,喂养一些必要的进口,饥饿和无情的,总是在我的天性。
他们告诉你,当你遇到黑熊制造噪音。他们让你熊希望避免人类和会蹦蹦跳跳当我们告诉他们奇怪的咆哮。但这只熊不订阅我们的故事。它会坐下来在你的欢迎,等你离开。它知道你会告诉这个故事,它知道你将错过它的一半,和更多。
它知道这不是一个关于你的故事。
* * *
在的上层小说的最后几页,一个九主角认为特定的词。与其他积极分子,他帮助把倒下的树在森林地面,安排他们在字母拼写出这个单词如此之多,他们会通过卫星获取图像。
在这一刻,他的知觉打开向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了解他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个词已经绿化。苔藓飙升已经结束,甲虫和地衣和土壤真菌的日志。护士日志中,幼苗根的缝隙,滋养腐烂。”
我想我理解的人类居民的上层。他们经历的更深层次的知觉,甚至只是一个味道的富丽堂皇,丰富的知识生活的互联性,能追上他们。他们趋向于极端的努力如何保护一片红杉受到威胁的破坏。我也理解人物有时会发狂,其他人在他们的故事和人类阅读他们的故事。
有些故事只工作如果他们被读者。有些故事值得讲述的只是如果他们压倒那些愿意接收他们。

艾米丽·乔特小说的编辑吗Peauxdunque审查并持有的M.F.A.萨拉劳伦斯学院。她的小说和散文出现密西西比州的审查,storySouth,谢南多厄河谷,佛罗里达州的审查,接受审查,阿提克斯审查,山茱萸的季度,和其他地方。她住在纳什维尔附近,在那里她的工作在一个小说。
标记:50本书/ HT50,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