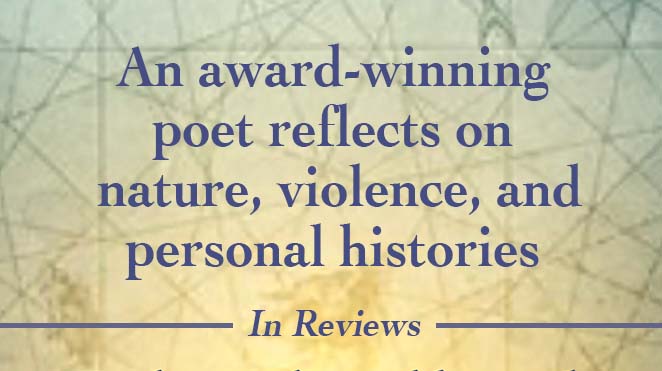我弟弟的胡子已经变灰了,他的衣服挂在他身上,就像稻草人挂在交叉的扫帚柄上一样。从远处看,在花园里冉冉升起的尘土中,他看起来就像从一张古老的家庭照片中走出来的,就像我的叔叔们,就像我的祖父,他们知道泥土的秘密。他伸手从南瓜上掐下一朵假花。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当我问他这些问题时,他只是疑惑地看着我,说:“我一直都知道。”今天,每一天,他的排都像针一样笔直,一尘不染。你可以在他的地上滚一颗弹珠。我看着他弯下腰去拔一根孤零零的杂草,然后我慢慢地走开,心想:如果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南方,就像恙螨和神糖一样,是永恒的。它将永远是,尽管它不会永远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我们童年的南方生锈了,剥落了,消失了。灌木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些把破旧的《圣经》推到光秃秃的椽子上的牧师们,现在在讲坛上宣扬政治。礼貌,即使是对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也是一种传家宝。棉被是一种用来取暖而不是用来赚钱的东西,是一种古老的东西,它们的图案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在一个老妇人的眼中慢慢消失。年轻人可以玩5000个电子游戏,却不会磨小刀;那些抓着线圈测试卡车电气系统的人失踪了。我倾听着过去,但我听不见。 The juke joints fall silent, cotton mills wind down to a final, solitary thread, and a last buck dancer shuffles off into the mountain mist. Then I see my brother Mark in his garden, and know that not everything must fade away.
南方,就像恙螨和神糖一样,是永恒的。它将永远是,尽管它不会永远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我们童年的南方生锈了,剥落了,消失了。灌木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些把破旧的《圣经》推到光秃秃的椽子上的牧师们,现在在讲坛上宣扬政治。礼貌,即使是对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也是一种传家宝。棉被是一种用来取暖而不是用来赚钱的东西,是一种古老的东西,它们的图案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在一个老妇人的眼中慢慢消失。年轻人可以玩5000个电子游戏,却不会磨小刀;那些抓着线圈测试卡车电气系统的人失踪了。我倾听着过去,但我听不见。 The juke joints fall silent, cotton mills wind down to a final, solitary thread, and a last buck dancer shuffles off into the mountain mist. Then I see my brother Mark in his garden, and know that not everything must fade away.
我还能看到我的外祖母艾娃(Ava)拿着用黑色电工胶带绑在一起的锄头去抓一头铜头鱼;它从来没有机会。我的祖父,鲍比,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磨棉花,还有6个小时是用他的双手在红土上劳作。我叔叔约翰戴坏了十五顶草帽,把三台拖拉机累死了。现在轮到马克来诅咒干旱、晚霜和地底下的岩石了。
五年前,他把一英亩长满篱笆和杂草的土地砍了个精光,把灰烬和大量的肥料混合在一起,在岩石遍布的山地牧场上创造了一片绿洲。现在,一季又一季,他带着一只年老的白色德国牧羊犬走下山坡——他给她取名为“漂亮女孩”——与那些会带走他一切的东西作斗争:一夜之间像噩梦一样出现的枯萎病;还有饥饿的昆虫,有些他甚至叫不出名字。那只老狗躲在泥土里阴凉的地方观望着,当远处雷声响起时,它站在我哥哥的拖拉机前不动,告诉他是时候在闪电到来之前进去了。好狗会那样做。
因为,你看,这不仅仅是科学在起作用。他了解科学,土壤的性质,如何种植——相隔多远,多深——以及种子的杂交和历史。但也有魔法——一些人称之为民间传说——是必须考虑的,就像青蛙的歌唱,月亮的阶段。大部分,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出于某种原因,他给自己的拖拉机取了家族的名字。那辆叫瑞奇的车起步很慢,跑步装备很差,座位上也没有填充物。
这里的人们说,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花园,种满了辣椒、洋葱、土豆和南瓜。他种的西红柿在妈妈的窗台上。装罐过程需要整个夏天和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她的房子里充满了醋和莳萝的味道。我都忘了一罐辣椒有多漂亮了。
但我想这里每个人都有马克。往红砖牧场主、框架房屋或活动房屋后面看,你会看到一片变成了泥土的地方。在这幅画里,一个南方女人或男人俯视着前方,仿佛他们能预知未来。当一切都被拆除,或重新建起,这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方式。

版权所有(c) Rick Bragg 2015。版权所有。布拉格是三本畅销书的作者:艾娃的人,到处都是,只有呐喊,青蛙城的王子.作为特稿作家《纽约时报》1996年,他获得普利策奖。他经常往返于新奥尔良和他的家乡阿拉巴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