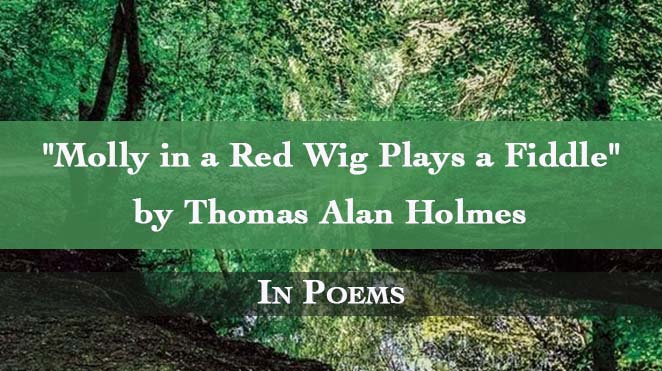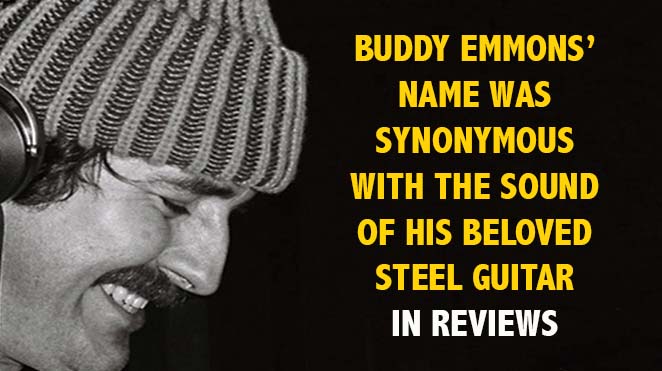[在他的新小说中,夜的颜色麦迪逊·斯马特·贝尔将读者带入梅的思想,她将童年的乱伦虐待转化为对暴力和死亡的神秘的、色情的痴迷。9/11恐怖袭击的电视画面让她激动不已,唤起了她对曼森式邪教的回忆,以及她在那里的情人和盟友劳蕾尔(Laurel)的回忆。以下有编号的章节是从即将出版的小说中选取的章节夜的颜色麦迪逊·斯马特·贝尔著。
1
直到双子塔倒塌的那一天,我一直相信所有的神都死了。多年来,几十年来,我的头脑都是静止的。只是有时候,在沙漠深处,会听到“奥”的鬼声。但是,我头上的铃铛仍然沉默着,漫无目的地在虚空中摇摆。
我可以再看一遍,想看多少遍就看多少遍,因为电视会不断地播放,就像没有人能赢的Tetras游戏一样。不限制我能消耗多少次,能吞噬多少次这些图像。一次又一次的迅速膨胀,成熟到爆裂点,然后倒下。在那巨大的毁灭之球还没有把它所有的物质都洒到地上之前,它那弯曲的、摇摇欲坠的、向外绽开的花朵。那些在它周围旋转的蚊蚋一样的小点,原来是从火焰中跳出来的凡人。在他们的尖叫声的笼罩下,他们往下沉了。
不管多少人看到一个人在看,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另一个人的心或想法。我不知道我的血液会这样上升。再一次,尽管岁月流逝,我的身体日渐枯萎。
有时电视上会播放一架飞机咬进建筑物的一侧,它的牙齿在建筑物的下方,也就是鲨鱼的嘴所在的位置,然后火焰从伤口中窜出,就像动脉里涌起的红色波浪。然后是活生生的人在街上嚎啕大哭,从脸上的骨头上扒肉,或者有些人冻住了,敬畏地跪倒在地。
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劳蕾尔,劳蕾尔跪在人行道上,头向后仰,双手伸出,手指弯曲,像是武器,或是赞美。血从她的嘴角流出来,就像从前一样,只是原因不同了。
3.
拖车停车场用铁链围栏紧紧地关着,但我在我的小甲板后面用插销剪断了一些围栏,所以我可以在高兴的时候直接走进沙漠。当我穿过栅栏的时候,我用手掌按住被剪断的锯齿状的铁丝末端,铁丝的力度不足以划破皮肤,然后我把这些碎片重新拼起来,这样栅栏上的裂口就不会太明显了,以防有人看到,但没有人会看到。
当猫头鹰无声无息地攻击我的时候,有一只啮齿动物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刺耳的尖叫,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我身后的一辆拖车里,一台电视机在喃喃自语,而在另一辆拖车里,一个老妇人在哭泣,用刺耳、丑陋、哽咽的声音啜泣。我走着,直到这些声音消失,背对着博尔德市闪亮的灯光。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的橡胶鞋底踩在沙漠苍白的尘土上发出的嘎吱声,而且那声音并不大,因为我走得很轻。有时我拿起步枪,却什么也没打死。今晚我把步枪留在了家里,两手空空。
我穿过沙滩上一辆全地形车留下的痕迹,再往南是一条响尾蛇留下的S S S。没有蛇本身的踪迹。沙漠看上去像月亮一样平坦空旷。月亮,真正的月亮,还没有升起。瑟琳娜还没有上车。
星星又冷又远,我站在它们下面,膝盖微微弯曲,背对着沙漠里的风,风从我的腿上和衬衫袖子里冲过,把我的黑头发向前拖到我的脸上。来自拉斯维加斯的环境光线从北方射入天空,使星星变暗。愤怒。愤怒。它变大了,然后消失了。
风停了,一只大猫头鹰俯在我的左肩上,在一片完全的寂静中,我的脊背在颤抖,穿过我的脚底,进入沙地。当猫头鹰无声无息地攻击我的时候,有一只啮齿动物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刺耳的尖叫,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好了。会做的事。但我仍然站在那里,又站了几分钟。我把手指缩进手掌,感觉指甲的边缘贴在皮肤上。明天之前我得把指甲剪掉。我尽量简短。
我周围的寂静并不十分完美;我仍然能听到某处高速公路上汽车的嗡嗡声,也许在远处的某个山脊上,有一座风电场的白色涡轮机。风又回来了,断断续续地,吹过一个洞,一副嘴唇,一个洞,发出一阵喘息的声音。有时,我似乎听到奥——的声音在星际间歌唱
....ταύρος-ταύρος——χορδν”κα土石方“ηικατάθλιψητηςνύχτας。Μετααστέριαπουπεριβάλλοντα,ικαιμετοφανότηςευρείας……
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毫无意义。否则我不会承认这种感觉
…οτουοποίουηλέκτρινοςσφαίρακάνειτοαπεικονισμένομεσημέριτηςνύχτας:
渴望,永恒的悲伤,使我烦恼。他无意义的声音
Εραστής των αλ ο γων, θαυμ ασ ιο ζ…
不过,这当然只是风而已。至少它停止了,在我的心完全变黑之前。
风改变了方向,把沙粒吹进了我的眼角。我转身离开了它,朝着空无一人、闪闪发光的小镇走去。天很快就要亮了。疲劳在我的大脑中是一个灰色的正方形,在我的两眼之间。我可能累得都要睡着了。
当我回到拖车里时,我四处寻找,直到找到我的指甲刀,在早晨的第一缕微弱的光线下,它们是廉价的金属银色。我撕开一包牛肉干当早餐,想都没想就猛地打开电视,一切都出现了。世界上有一个洞。透过电视屏幕的裂缝,一切都涌向我。
11
我还保存着O-的所有旧唱片,虽然可能大部分都被刮花了。他在夹克上的照片被旧碎屑弄皱了。在一张双层唱片的折页里,我发现了两颗有30年历史的大麻种子。
当然,在他们发明CD的那一刻,它们就以CD的形式出现了。你可以,我可以,把它们下载到你的I - pod上。
我没有试着去听唱片,部分原因是我没有唱片转盘了。我把其中一个盘子拿出来,看看它油腻的黑色表面。一股粉状的烟灰从圆盘前面的套筒里冒了出来。在前三条铁轨上的沟槽上,横着一道苍白弯曲的裂口。
至于俄耳甫斯的音乐,对每个人的伤口都是一种抚慰。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的骨折开始愈合。每个人都转向它,就像草转向太阳一样。
当我把唱片放回夹克里时,我的目光停留在它已经浏览了一千次的东西上。录制过程中的照片被印在封面上,以一种人为的随意方式摆放,就好像它们掉在了地板上。还有一个O——在他青春的春天,一把原声吉他平衡地放在单膝上,带着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画框右边边缘以外的什么东西。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照片右下角的一只脚。一只年轻的脚,形状很好,足弓很高,很优雅,指甲油深得几乎是黑色的,脚上戴着金色的趾环,还有一种劳瑞尔那时常用指甲花在自己身上画的乱七八糟的图案。
现在有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女人。我不知道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至于俄耳甫斯的音乐,对每个人的伤口都是一种抚慰。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的骨折开始愈合。每个人都转向它,就像草转向太阳一样。
28
大熊星座爬上墨黑的天空,在碱性的沙漠地面上投射出冷光。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远到城市的灯光在我身后的地平线上褪成了硫磺色的花朵。前方是一条长长的长野兔小径,它的颜色比周围松散的沙子稍微淡一些,摇摆着变成了一堆从台地上倾泻下来的巨石。
我蹲在一棵多节的杜松旁,把它干枯的根紧紧地夹在一块大石头的裂缝里。荆棘的影子落在我身上,用黑暗遮蔽我。
在高高的台地上,土狼在唱歌。疯狂的、高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哭声。声音在沙漠里传播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可能实际上已经走了好几英里远,而且可能只有两个人,尽管听起来像是十几个人的合唱。
我在寻找兔子;还有没有。时间在流逝,头顶上的星星在不停地转动,伴随着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音乐,就像你用吐湿了唾沫的手指在水晶杯沿上摩擦。
也许郊狼能在我的阴影里看到我。也许他嗅到了血液的味道,从我的心脏排出了长长的血液循环。
土狼早就停止了他们的音乐会。但现在有一只兔子小心翼翼地沿着杰克兔的足迹,从满是刺柏结的巨石中走出来。它躲躲藏藏,经常停下来驼背,把枪口转到肩膀上。接着,他的耳朵向前转了转,竖起来,又向前走了一步,脚步轻快,对小路的表面更加注意了,尽管我看不到什么可以跟踪的东西,没有兔子,没有蜥蜴,没有老鼠,也没有松鼠。
也许郊狼能在我的阴影里看到我。也许他嗅到了血液的味道,从我的心脏排出了长长的血液循环。
我站了起来,摆脱了阴影,让自己变大。郊狼畏缩不前,蜷缩在折叠的膝盖上,耳朵平贴在头上的皮毛上。在微弱的星光下,他的眼睛泛着淡黄色。
今晚我没有带步枪。郊狼和我保持着僵住的平衡。最后,我慢慢地后退了几步;土狼呆在原地不动。
我转过身走了,不快地走着,感觉到我的脊背上有一个苍白的斑点,尽管我很清楚,一只孤独的郊狼是不会攻击一个成年的人的,除非它得了狂犬病,而这只郊狼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这种可能性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在我身后,可能还会有爪子踩在沙滩上的干巴巴的低语。当我回头看时,郊狼仍然一动不动。
一次。下次我再看的时候,郊狼离巨石的距离可能会有一点变化。他还。
下次我再看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一英里多,离拖车公园足够近了,可以从模糊的阴影中分辨出个别的光点。现在,那只郊狼在我后面疾驰而来,但跟在我后面相当远的地方。
我慢慢地走着,朝着人造的灯光走去,心里想着第一批野狗一定是怎样出于某种原因进入营地,把自己变成人类的奴隶的。当我到达铁链栅栏的裂口时,郊狼已经不见了。
(0)
(0)
(0)
空虚的圆伤口....
我不小心穿过栅栏时擦伤了前臂;我爬上后甲板的木台阶,心不在焉地把它舔干净。我的喉咙里有一股浓浓的盐味。我不饿、不渴、不困。离晚上还有几个小时呢。
我在胳膊上喷了杀菌剂;它的刺似乎几乎没有刺到我。不知怎么的,手机就在我手里。我第二次拨通了纽约的电话号码。
“你好……”
(0)
“喂?”
啊,我当然能想象她那时的样子;我不需要看录像。她双膝跪地,头向后仰,沉重的乳房从布缝里伸出来,弯曲的手指抓着闪闪发光的尘土飞扬的空气。
“梅,”劳蕾尔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美吗?”
我想我从来没有给过她一分钱。这就是我想说的。但是我的嘴唇紧闭着,就像被铜封住了一样,我的眼睛被金属的重量压得很沉重。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苏醒过来,终于在焦灼的日光下醒来,无力的手里又拿着手机,机器人的声音在提醒我如果你想打个电话把它挂起来。
36
我带着步枪进入沙漠,蹲在一块巨石的阴影下,在兔子的足迹旁等待。没有兔子。没有水。我干瘪的嘴里叼着一块石头。
我能听到老鼠移动的声音,但我看不见它们,这很奇怪,因为夜晚的颜色是如此的苍白。那里有一颗月亮,沙漠的地面因暗淡的光线而弯曲,就像月球表面的反射一样。黑色的丝兰刺从白色岩石的裂缝中探出。地平线上,一丛金雀花和扭曲的牧豆树枝条像幽灵一样伸向天空。
祭血的烟的香味,从祭坛的角之间升起。月亮的角。
不一会儿,一只郊狼来了,它在追捕老鼠——像猫一样敏捷而警觉,用眼睛盯着看不见的猎物,然后猛扑过去。我举起来复枪,在瞄准镜里发现了他。郊狼把头转向我。耳朵,泰然自若。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岩石的阴影上,他肯定知道我在那里。
我们平衡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盯着他直到天亮,然后放他走了。
39
保利的步枪装在一个像吉他一样的长方形盒子里,里面有长毛绒内衬的隔层,用来装步枪本身、瞄准镜、星形发射器和消音器,消音器是个大而笨拙的东西,有酒瓶那么大。在外面的沙漠里,没有人能听见,但有一天晚上,我还是带着消音器,还是那样。
虽然重量不及酒瓶的四分之一,但确实改变了武器的平衡。我一直练习,直到适应了不同,找到目标,但不开枪。石尖或掉落的树枝事情已经死了。从来没有住。
伸出无形的,沉默的,致命的触摸....
然后,运动。视野中闪烁着绿色的磷光。
然后,运动。视野中闪烁着绿色的磷光。有了消音器,子弹发出的声音几乎就像打喷嚏,或者有人在干沙子上吐痰的声音。我使我小心地把步枪顶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倒在狼身上,刀拔了出来。土狼还在断断续续地踢着,用爪子磨着细细的砾石。死人的颚在撕咬。
把它翻了个底朝天。剥皮。就像多年前我们一起出去猎鹿时,特雷尔教我的那样。我现在拥有的这把刀不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当我到达困难的部分时,它已经变得迟钝了。我在石头上把它磨快了,接着剥皮。最后,头皮完整地剥下来了。我停下来,跪在地上,用手掌撑着,像狗一样喘着气。
我手肘上都是血。在微弱的星光下,映衬着沙漠苍白的地面,它看起来是黑色的。我呼吸的声音就像干燥木头上的锉刀。
我慢慢地站起来,扶着它的肩膀,抬起它柔软的皮肤,看着神面具空洞的眼洞。在缺席。不可避免的凝视。如果五官似乎在颤抖,那一定是因为我的手在微微颤抖。那微笑现在可爱地蜷缩在角落里,从它那沾满血迹的牙齿上脱落下来,它躺在我旁边的地上。在我的脚下,这具尸体现在静止了,它受了委屈,无法挽回,它的黏稠液体浸在沙子里。
面对着地平线上嗡嗡作响的光污染,我把皮肤举过头顶。一股难闻的麝香和血腥味包围着我。软绵绵的面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这次我不想让皮肤碰到我,像斗篷一样落在我的肩膀上。我笨拙地把它举了起来,越过我,远离我,保持平衡,调整方向。回头看,透过野兽的眼睛,看到凡间垂死的光芒。
点击阅读麦迪逊·斯马特·贝尔的采访在这里.
版权所有(c): Madison Smartt Bell 2011。保留所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