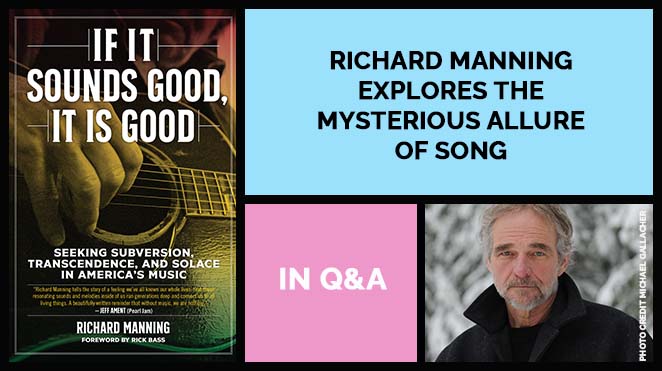我们去拜访一位姑父,我就叫他K吧,因为他的生活安排而变得复杂起来。
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为他的妻子买了隔壁的房子,我称她为Z阿姨。这比离婚更不丢人,也更便宜。不管怎样,这种安排很好,因为K叔叔每隔一周左右就会把洗好的衣服放在外面的后门廊上,Z阿姨几天后就会把衣服送回来,按照他喜欢的方式洗涤和熨烫。她还为他做饭,或者其中一些,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后门廊上,过一会儿再回来洗碗。K叔叔要做一个好养家的人,就像男人应该做的那样,Z阿姨要做一个好妻子。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不必见面。

我第一次了解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在我父亲的凯迪拉克的后座上,当时我们穿过纳什维尔某个住宅区的街道去看K叔叔和z阿姨。这是我第一次去我父亲的家乡田纳西州,也是我母亲的第一次旅行,因为父亲在娶她的时候根本没有提过他还有家人。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家庭——除了他的哥哥K叔叔,他还有一群其他的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在迪克森县长大。我是他晚年的女儿,在他快60岁时出生,所以我的叔叔婶婶都七八十岁了。
我们一拐进他们家的那条街,父亲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不想把车停在K大爷家门前,因为怕得罪Z大爷。他也不想把车停在Z大爷家门前,因为怕得罪K大爷。它们看起来很普通——两座并排的小房子,和我们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房子差不多大。我母亲的超然天赋堪比人类学家,我不记得她说过什么。
我父亲可能没有先打电话来,所以很可能K叔叔和Z阿姨都不知道我们要来。凯迪拉克(Cadillac)是上世纪50年代末推出的一款笨重的绿色车型,在满是福特(ford)和雪佛兰(Chevys)的社区里很难藏起来。他慢慢地减速,从停在街道两边的汽车中间穿过,然后开到街区的尽头,把凯迪拉克调转车头,停在了两幢房子对面的中立区域。他切断了马达。我妈妈开始下车,但他只是坐在那里,决定先去哪里。他说我们最好从z阿姨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骑士精神,所以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因为K叔叔的窗帘拉得很紧,所以他可能没有看到我们,而Z阿姨的窗帘是开着的,她可能看到了。
Z阿姨看起来和我在那个夏天遇到的其他田纳西阿姨没有太大区别。她们都是整洁、丰满的女士,穿着花裙子和四四方方的鞋子,灰色的波浪用薄薄的发网盘起来。但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当她看到我父亲时,她最初感到惊讶,然后她欢迎我们进入她的客厅,这是一个明亮的地方,玻璃盒子里放着小摆设,椅背上放着防弹衣。它非常干净。我挨着母亲坐在一张软垫沙发上,沿着硬木地板的线条一直走到墙边。我在什么地方听过“干净得可以在地板上吃东西”这句话。我记得我认为那是真的。不像我们的房子,它没有一个灰尘兔子。
我不记得大人们都谈了些什么——大概是父亲上次来访后都在做些什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一切,她四十多岁,是一名秘书。Z阿姨对我低声说了几句,其他阿姨和一些年龄足以做我阿姨的表姐也是这样说的。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每隔几年就带着一个新妻子出现,这并不稀奇,但有一个新女儿却很罕见。我比他自己的孙子还小,虽然我还不确定自己是否知道。

我们在那里坐了几分钟后,Z阿姨问我是否愿意在厨房里帮她。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她已经煮好了一壶咖啡,说我可以帮她端一盘饼干。对此我不是很确定。田纳西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我们来到那里的几天里,我一直和父母走得很近。但妈妈点了点头,于是我跟着Z阿姨穿过一间较暗的中间房间,朝后面走去。厨房和前厅一样明亮,一样干净。我惊叹于那些闪闪发光的铬合金、一尘不染的白色瓷砖和瓷器,以及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锅碗瓢盆。
厨房里有一块红色的斑点。我现在不记得是什么了。可能是大窗户边上的桌布或窗帘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盘子或一个苹果。但我清楚地记得红色,这个细节我已经带了几十年。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知怎么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想待在那个房间里,待在干净明亮的过去,看看我能对田纳西这个地方有什么了解,我不仅生活在那里,而且生活在那里,还有这位姑妈,我父亲的一个古老的亲戚,一个在我之前生活的人,我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她。当然,我并没有用这么多的语言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有孩子的本能——在语言之前就有问题。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然后Z阿姨把那盘饼干递给我,让我小心拿着,我跟着她回到了父母等着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大人们把瓷杯放在膝盖上,Z大妈凑过去,几乎是低声对父亲说:“他怎么样了?你去过那里吗?”当然,她指的是K叔叔。她想让她很少见到的姐夫告诉她关于隔壁丈夫的事。父亲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她的意思,然后他说不,我们还没去过呢。她说,哦,哦,当然没有,她的话像许多小鸟一样扑腾起来。接着是一阵沉默。我的母亲,一个善良的人,可能会用一些评论填满它——咖啡很好,田纳西肯定比俄克拉荷马州多山。过了一会儿,父亲把杯子放在桌上,说我们该走了。
K叔叔的房子很黑,有一股封闭的气味。他坐在前屋一张拉到中央的大椅子上,旁边是一张小桌子,杂志堆在四周。多年来,我需要他显得老练老练,我记得他穿着一件吸烟夹克,但那可能是他抽烟时穿的浴袍。他给我一杯可乐,我拒绝了。它看起来很脏,因为他的房子很脏。那一刻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对一个老人幼稚的残忍,以及这让我父亲多么尴尬。
很久以后,我听说了我父亲和K叔叔的姐姐的丈夫,一个邮递员,在K叔叔的女朋友住的那条路上送邮件的故事。他们就这么叫她,"女性朋友"一天下午,K叔叔听到他来了,试图躲在一件家具下,但姐夫从开着的窗户看到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还没有空调。姐夫叫我出来,说他认识这两只大脚。但K叔说他爱这位女朋友,不会放弃她,Z姨说她不会离婚。所以他们才会住在两栋房子里。
在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去了田纳西州,但我不记得回过那些房子。也许是我父亲一个人去的。我不知道。他从没提过那天我们在那里,我也再也没见过Z阿姨。

版权所有(c) 2020年由Jane Marcellus。保留所有权利。简·马塞勒斯的论文发表在包括葛底斯堡审查,锡拉丘兹评论,海马体.她收到了新俄亥俄州审查2019年编辑奖。她是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教授。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