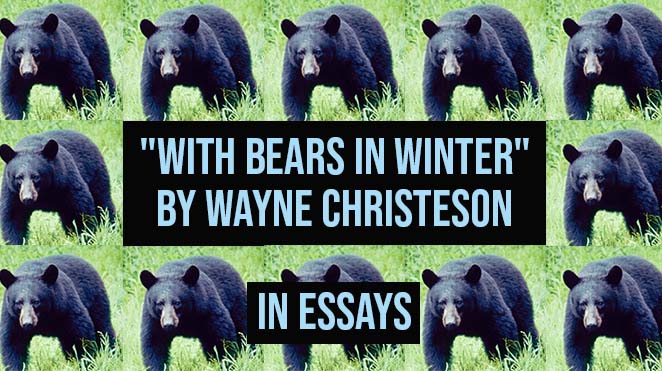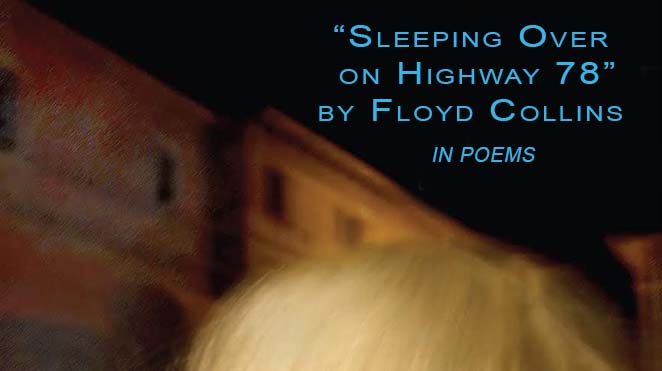在铁轨和将铁轨与雅加达其他地方隔开的墙之间四英尺的地方,人们生活着。向北和向南的轨道,两边都是倾斜的。在两组轨道之间,孩子们在踢足球。垃圾之火在目标所在的地方燃烧。
我站在一间斜屋的开口处,望着里面曾经是一个人的东西。膝盖,胸腔,静止。
他死了,我想,几乎要笑了。羞耻紧随其后。那么难以置信。也许这种近乎大笑的状态与我无法处理我所看到的东西有关。我想知道这是否是现代世界的一种状况,正确的情感很少出现。
抽搐。那人从一侧翻到另一侧,眼睛盯着我:一个正在做研究的作家,一个身材高大、吃得很饱的美国人,作为参观的一部分,正在见证可能是他最后的几个小时。
罗尼,经营贫民窟旅游的印尼人之一他的妻子叫他过来。她是一个满身尘土、多节的老妇人,蹲在丈夫旁边,两个人的脚趾碰在了一起。他妻子和罗尼说的是印尼语,所以我只听到了语气。保持冷静。认真的。他们似乎在讨论最好的行动方案。罗尼用旅游赚来的钱为住在这里的人支付医药费,但那个女人不想麻烦他。他必须说服她。
 现在我们要去看医生,但旅行总是被耽搁。首先,这里有所有的孩子,一群孩子暂停了他们的足球比赛,跳上跳下,抓住我的手,按在他们的额头上,欢迎我。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在表演把纸杯放在额头上保持平衡的表演。一个偷了足球的瘦胳膊女孩正在找地方把它藏起来。罗尼正在给我统计数据。印尼政府说雅加达只有900万人,但实际上接近25万人。他说:“这么多的人都数不清。”“盈利”。
现在我们要去看医生,但旅行总是被耽搁。首先,这里有所有的孩子,一群孩子暂停了他们的足球比赛,跳上跳下,抓住我的手,按在他们的额头上,欢迎我。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在表演把纸杯放在额头上保持平衡的表演。一个偷了足球的瘦胳膊女孩正在找地方把它藏起来。罗尼正在给我统计数据。印尼政府说雅加达只有900万人,但实际上接近25万人。他说:“这么多的人都数不清。”“盈利”。
我说:“好吧,那医生怎么办?”
“我们要去看医生。不要担心医生。”
我尽量不这么做。我决定换个话题。“你不是一周做三到四次这样的旅行吗?”
“是的。”
“但是孩子们太兴奋了。他们总是这样吗?”
“他们总是这样,”他说。然后邀请我去一个被火车撞了的女人的家里。房子,我一直想叫它们,因为它们建得很完整。这一间有一个被切割成一定尺寸的木柜和一部分书架。
这个女人本身很瘦小,由于年事已高和生活艰苦而变得消瘦。她的半边头和一只眼睛被绷带盖住了。但另一个人也很善良。我用有限的印尼语打招呼。她给了我一个如此温暖的微笑,好像她已经等了我一整天了。然后火车来了。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离她的前门只有六英寸。女人仍然在笑,但这背后有什么。这背后一定有什么。
“好了,”火车一过,罗尼就说,“该走了”——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大家都在赶医生,而是因为他想带我看鸽子赛跑。在来雅加达之前,我读过他们的故事。雄海豚会快速行进4公里去寻找它们一生的伴侣。群体中的男孩会抓住其他雌鸽子,试图让雄鸽子离开。
鸽子比赛将成为我来雅加达研究的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主题共鸣是我跟罗尼说的。我花了半个小时来解释。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看到这一点。
“你的书写的是雅加达的穷人?他最后问道。
“没有。”
“是关于什么的?”
“美国人。两名美国人在印尼。”
“有很多关于美国人的书。”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是的,有。”
不过,和许多印尼人一样,他非常乐于助人。决心带我好好参观一番,即使这意味着要花更长的时间为一个垂死的人找医生。
 比赛在两组跑道之间进行,距离男孩们踢足球的地方以北只有几百码。但今天没有比赛。当我们和这些人交谈时,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我读到过的赛鸽比赛的风格。
比赛在两组跑道之间进行,距离男孩们踢足球的地方以北只有几百码。但今天没有比赛。当我们和这些人交谈时,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我读到过的赛鸽比赛的风格。
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当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深深地点头,就好像我刚刚说了一些很有哲理的话。一个人在和罗尼握手,拍着自己的肚子,我听不懂这个笑话。孩子们还在上蹿下跳。妻子在一旁看着,等待着医生的到来,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耐心的,我无法理解。然后突然就发生了,这些住在铁轨旁边的人比我在美国的所有朋友都幸福,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幸福。
我对这种想法不是很满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似乎让像罗尼这样的人的工作失去了合法性,一个致力于帮助别人的人。此外,你有时也会听到希望维持现状的富人表达类似的情绪。
罗尼让一个少年带着他的妻子去看医生,我们继续我们的旅行。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一个地方,那里的难民用浮木建造了一个村庄,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村庄,就像某种奇迹,一个小型的威尼斯。
那次旅行结束时,我既感动又不安。关于人性和毅力的一些非常神秘的东西已经打动了我,我想告诉所有我能告诉的人。
我在酒吧认识一个印尼商人,他说这是扯淡。他称之为“良心之旅”。他的理由是,如果你拥有一块土地,人们来到那里,决定在上面生活,会发生什么?你一直在计划开发那块地,所以现在你看起来像个恶棍因为你必须把他们赶出去?如果没有人想坐火车,因为它经过这些地方,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火车撞到了人,他们会责怪火车公司?如果这些人在雅加达过不下去,如果他们需要施舍,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为什么要来?
我从没这么想过。我不想表现得好像我知道谁是对的。我对历史、商业或政治都不太了解,甚至对印尼也不太了解。我只是研究小说,我想,这意味着,最多,我知道一些关于人物的事情。我能肯定的是:那个跟我说话的人,那个被人骂的商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孤独、最不快乐的人之一。
版权(c) 2011由亚当·普林斯。版权所有。亚当·普林斯(Adam Prince)是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英语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重点是创意写作。他的故事已刊登在《密苏里评论》,《南方评论》,叙述杂志等等。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丑男人的美好愿望将于5月由布莱克劳伦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