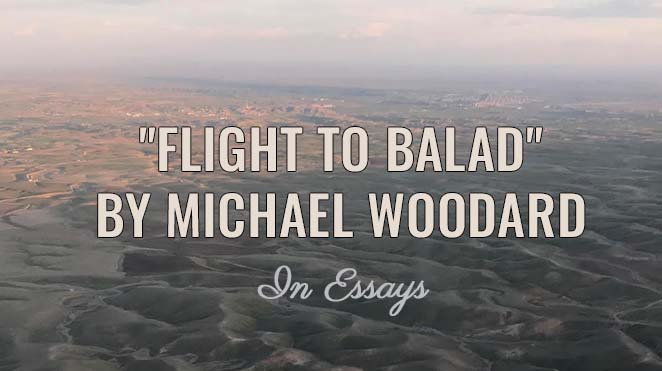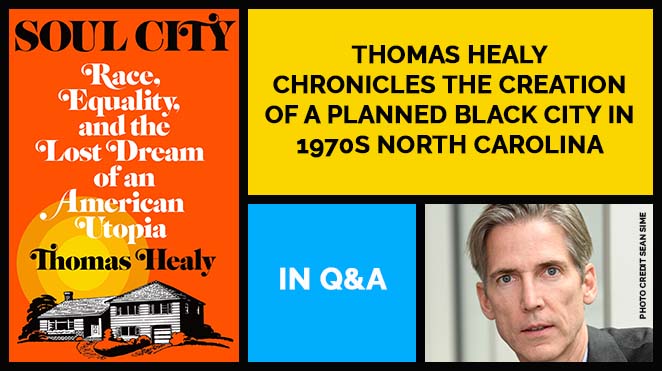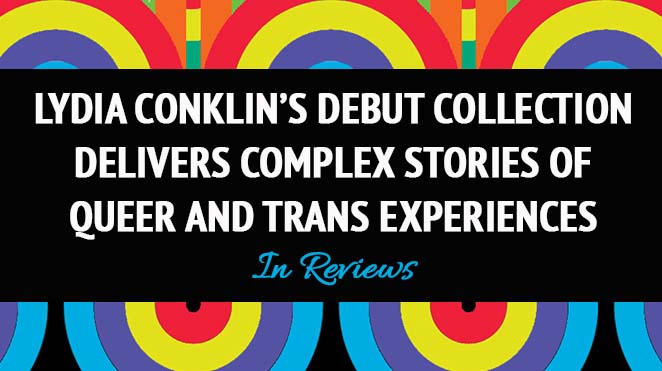我出生在田纳西州的老诺克斯维尔总医院。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在医院出生的人。当我的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和我争吵时,他们会说:“你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不认为我相信他们,但我确实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的家庭。我知道他们很刻薄,但我也想,如果他们是对的呢?如果我是被意外发现的呢?如果我属于别人呢?
 我们从诺克斯维尔搬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北部的伍德隆。那是在种族隔离时期。我父母的工作在诺克斯维尔是不可能的。我们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厨房,客厅,还有一间户外厕所。我记得外面的厕所,出于我不明白的原因,我很喜欢这种记忆。事实上,当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时,我让丹在前面做了一个外屋来收我的邮件。这是一件感伤的事情。
我们从诺克斯维尔搬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北部的伍德隆。那是在种族隔离时期。我父母的工作在诺克斯维尔是不可能的。我们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厨房,客厅,还有一间户外厕所。我记得外面的厕所,出于我不明白的原因,我很喜欢这种记忆。事实上,当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时,我让丹在前面做了一个外屋来收我的邮件。这是一件感伤的事情。
我们很穷。这是理解。当我父母攒够钱在林肯高地(Lincoln Heights)买了一套房子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林肯高地是辛辛那提城外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林肯高地没有垃圾收集系统,所以我们只能焚烧垃圾。我很喜欢。隔壁的空地是空的,我记得兔子住在那里。可能还有其他事情。我会追逐兔子,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只是想和他们一起玩,但他们不理解。我猜他们只知道我每晚都烧垃圾。 I would stand and watch the fire. I don’t think I worried so much about burning the house down as I was simply fascinated by fire. Some evenings I watched the moon. Mostly I remember just dreaming.
妈妈在圣西蒙学校教三年级。我父亲格斯在林肯高地中学教数学。有一天,出于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的原因,我决定去见格斯,他每天都爬上山来我们家。我有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当我开始下山时,我似乎记得或认为我听到格斯说:“看那个疯狂的孩子从山上下来了。”那时自行车已经骑在我身上了。72岁的我,至今仍有当年的伤痕。
但我活了下来。
我在试着理解我父亲。我有点觉得他很刻薄;一部分人认为他喝得太多了;有一部分人就是不明白。但每周六晚上11点左右,如果你问我在做什么,我会听到我爸爸打我妈妈。有天晚上我听到的最悲伤的声音是"格斯,求你别打我"这是祈祷。
 我有一个姐姐,但她总是很友好。她有可以一起过周末的女朋友。星期天她会很晚才回家,谈论她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不友好。我呆在家里。直到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的教母Baby West去世了,留给我50美元。我走到洛克兰的银行,看看我能用它做些什么。他们说,我能接受。我买了汉堡和去诺克斯维尔的票。 Our neighbor, Mr. Gray, who must surely have known what went on in our home, gave me a ride to the train station.
我有一个姐姐,但她总是很友好。她有可以一起过周末的女朋友。星期天她会很晚才回家,谈论她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不友好。我呆在家里。直到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的教母Baby West去世了,留给我50美元。我走到洛克兰的银行,看看我能用它做些什么。他们说,我能接受。我买了汉堡和去诺克斯维尔的票。 Our neighbor, Mr. Gray, who must surely have known what went on in our home, gave me a ride to the train station.
祖母一定知道我想逃避什么,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我问我能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和爷爷毫不犹豫地说:是的.
我现在读到关于黑人男孩在家里需要父亲的报道,我想知道。白人男孩家里有父亲,最后都进了三k党。白人男孩最后会骂我们。向我们吐口水,甚至更糟。现在白人男孩是警察,射杀手无寸铁的14岁少年。或者他们是竞选总统的亿万富翁。煽动仇恨。我不确定父亲除了生理功能之外还有什么必要。如果我们要把堕胎的妇女定为犯罪,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让她们怀孕的男人也定为犯罪吗?
但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亚历克斯·海莉说我们有根。他追根溯源到非洲。关于我的根,我真正理解的是,黑人女性有意无意地与她们被带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形式交配。不论肤色,种族或宗教。这种生命形式现在想要否认自己的责任。但黑人女人喜欢她孵化出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相信未来。
亚历克斯·哈利干得不错。他使我们想起希望。我想说的是,任何事物都有根源。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像拔草一样将它们拔除,还是培育它们,让它们开花结果?我认识亚历克斯·海莉。他在危难时刻给了我们前进的理由。他提醒我们,我们都有根。我们人类,我们的人道主义,工作是纠缠和丰富。

诗人尼基乔凡尼1943年6月7日出生于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虽然她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长大,但她和姐姐每年夏天都会回到诺克斯维尔看望祖父母。妮基以优异的历史成绩毕业于她祖父的母校菲斯克大学。自1987年以来,她一直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任教,在那里她是大学的杰出教授。

这篇文章是普利策奖百周年篝火计划这是普利策奖委员会和州人文理事会联合会的合资企业,旨在庆祝普利策奖2016年成立100周年。我们感谢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约翰·s·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普利策奖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对篝火计划的慷慨支持。
标记:非小说类,Pulitzer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