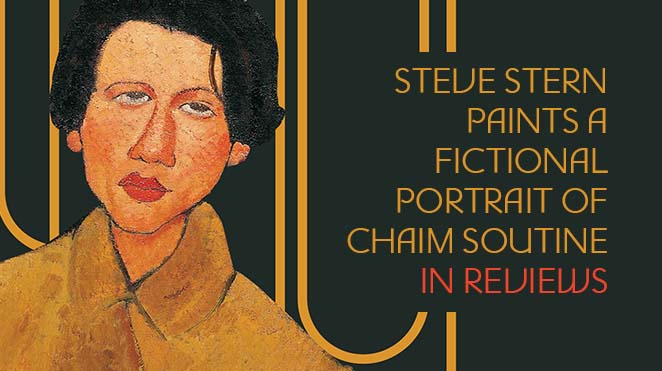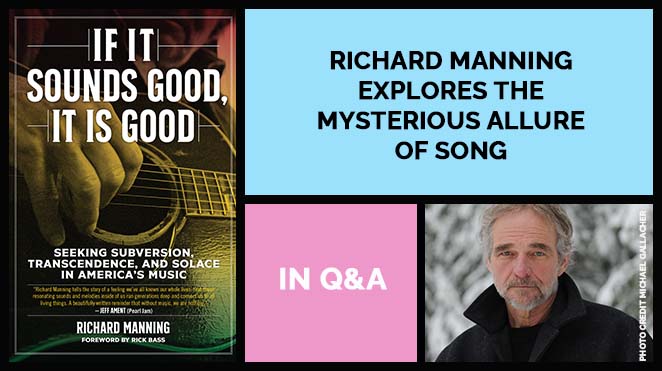我当时18岁,即将成为第一个离开底特律的瓦戈人,原因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原因。这要感谢我的学生贷款、佩尔助学金,以及一个学术留校计划的礼物,这个计划给了像我这样的孩子一个学期的时间来证明我们的学术价值,或者回到我们来自的地方。
 我有一辆车,一份在木材场的工作,在我的嵌入式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藏着一本保险公司的日历,还有一品脱装着我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的凯斯勒啤酒。在日历上,毕业后的每一格上,我都会随着日子的流逝,用红色的吱吱作响的X标记出来。x在八月里挤来挤去,就像吃豆人吞下编号盒子一样,被鬼魂追赶,就像电子游戏一样。每过一天,x就会靠近27号方格离开。
我有一辆车,一份在木材场的工作,在我的嵌入式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藏着一本保险公司的日历,还有一品脱装着我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的凯斯勒啤酒。在日历上,毕业后的每一格上,我都会随着日子的流逝,用红色的吱吱作响的X标记出来。x在八月里挤来挤去,就像吃豆人吞下编号盒子一样,被鬼魂追赶,就像电子游戏一样。每过一天,x就会靠近27号方格离开。
在我的世界里,有两种人:一种是破碎的灵魂,他们用自己的梦想换取彩电和周二晚上的保龄球联赛;另一种是幸存者,他们用阴暗的兼职和在学校停车场里通过生锈的肌肉车摇下的车窗进行的悄悄现金交易,取代了自己的梦想。这两件事我都不想干。
当我晚上在外面寻找麻烦,等待着八月的结束时,妈妈晚上在门廊上摇晃,看书底特律新闻在WJR上听厄尼·哈维尔和阿尔·卡林预报老虎队的比赛。晚上我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或气急了,她就会在屋前厨房的大窗户边等我,吃着用热牛奶泡的咸饼干,当她看到我跌跌撞撞地走到车道上时,她就匆匆跑去睡觉了。
她在11年里生了7个孩子。九年后,我醒悟过来了。我在她体内的存在导致了毒血症,在我出生前,我们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三个月,还毁了她的牙齿——甚至在子宫里,我就夺走了她愿意付出的一切。像她那样坚忍的中西部人,她买了假牙,放在厨房水槽里的一个塑料杯子里,开始毫不犹豫地抚养我。
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爸爸已经70多岁了,退休了。他的身体仍然可以看到瘦削、肌肉发达的手臂和宽阔的肩膀的阴影,这些都是他一生中辛勤劳动的结果,等待着任何一个受过8年级教育、有家庭要支撑的男人。他每天都在房子后面的一个车库里,用他捡来的木材做东西。在那里他可以离开妈妈,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处的地方。
他会讲述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和梦想的重要性。爸爸谈起梦想时,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水手坐在一艘他从没想过会用的救生艇上,眼看着自己的船沉入海底,却几乎找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给我讲的那些故事,从关于谨慎和勇气的故事,变成了我不再需要听的无休止的教训,成了我时间的负担。
在我完成日历的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爸爸哄我去车库帮他锯2x6的锯子。完事后,他把粘在一起的眼镜推到鼻尖,掸去粘在他汗流浃背的灰色工作衬衫上的锯末,问我那天晚上有什么计划。
“我在打扑克,”我说。
“在哪里?”
“丹尼的房子。”
“和谁?”
“丹尼和菲尔,还有其他人。”

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谁,但我知道。是格罗博斯基兄弟之一,爸爸真的不需要知道。丹尼的爸爸是个警察,所以说我要去他家是暗号安全.当然,孩子们可能会被欺负,被折磨,被打伤,被殴打,但在警察的地下室里不会有刀子,也不会有真正的打斗。附近的每个孩子都非常害怕底特律的警察,不管他们是不是谁的爸爸。
丹尼20岁,身材敦实,很有街头范儿,梳着一头浓密的卷发,你会以为他用四根胖手指在头发前面拽了一把埃尔默胶。他在建筑工地工作,在母亲的坚持下住在父母的地下室里。菲尔和丹尼一起高中毕业。他睡在婴儿时睡过的房间里,在某种程度上,他把婴儿床换成了大男孩床。他瘦骨嶙峋,窄尖的鼻子,稀疏的红色卷发,一张窄嘴朝下,口齿不清,说“th”还是“s”都不知道。格罗博斯基比菲尔和丹尼年纪大一点,也没有他们俩聪明。
爸爸问我以前是否和这些人打过牌。不,我说。
“孩子,你以前打过扑克吗?”
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们都知道答案。
他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开始他的工作,把我们分开的2x6整齐地堆成一堆。他把眼镜推到鼻子上,说:“孩子,记住,如果你在玩扑克,不知道谁是输家,那就是你自己。”
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之前。这听起来像是他一路学到的东西,并一直储存在他的记忆中,只是为了我,只是为了现在。我保持沉默,试图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孩子,你现在可能不明白,”他说,“但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完事后,我回到房间,在口袋里塞了四张20美元的钞票,开车去银行,把它们换成25美分、10美分、5美分和一些1美元的钞票。
在我去丹尼餐厅的路上开始下雨了。我敲了敲门。他的妹妹丽莎在厨房里,大声叫我进去。丽莎身材高大,有异国情调,夏天总是晒得黝黑。这让我很好奇她和丹尼怎么会生在同一个父母的家里。她在美容学校上学,穿着超短裤,戴着环状耳环,棕褐色的中脚趾上各戴着一个小戒指。几年前,在她16岁的生日派对上,她向我要一个生日吻。我又惊又怕,假装没听见。

她告诉我丹尼在地下室等我。我微笑着走下楼梯,知道她知道我参与了这场游戏。
木台阶在我脚下嘎吱作响,地下室里的笑声停止了。他们的地下室和我们的一样,发霉了,各种暴露的管道塞在低矮天花板的托梁之间,中间的一根铸铁杆支撑着房子的其余部分。我是最后一个到的。
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被我的笑话逗笑了,甚至格罗博斯基。丹尼在他们的小地下室酒吧用西格拉姆酒的把柄做了7&7s。等着大家都知道吧这妈的,我只对自己说。他们给我解释了每一款游戏以及如何玩:《盲人棒球》、《盲人廉价商店》、《老兵游戏》、《直男和种马扑克》等等。当我在交易中犯错误时,他们会指出来,但不会生气。
快到两点钟时,丹尼报时了最后一次报时。西格拉姆的酒瓶是空的,只剩下四张皱巴巴的美钞和宿醉在子宫内.他们三个人还坐在牌桌前抽烟,我沿着木台阶往回走,走出门,被一头驴的尾巴绊了一跤,我终于意识到我夹在了两腿之间。
长时间的雨后,夜空刚刚放晴。潮湿的空气使夜晚的声音变得清晰,也软化了城市持续的气味。我知道一旦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丹尼,菲尔和格洛博斯基了。醉醺醺地走在街灯从黑暗中划出的每一圈亮光中,停着的汽车的镀铬保险保险条在房子里闪烁着淡淡的微笑,妈妈坐在黑暗中厨房的大窗户前,吃着用热牛奶泡的咸饼干。

版权所有(c) Lou Vargo 2021。版权所有。卢·瓦戈在底特律出生长大。2003年,他从德克萨斯州来到纳什维尔。他和妻子、女儿、继女、狗和猫住在纳什维尔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