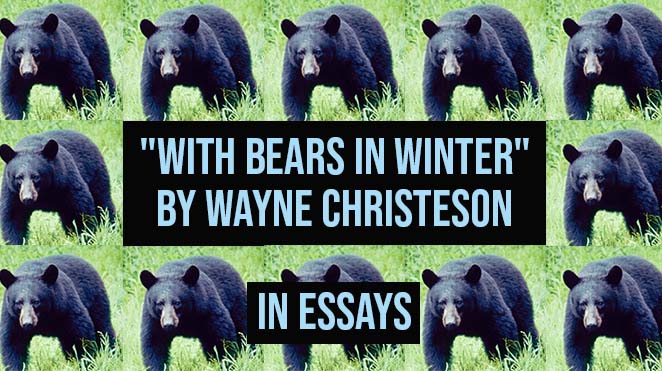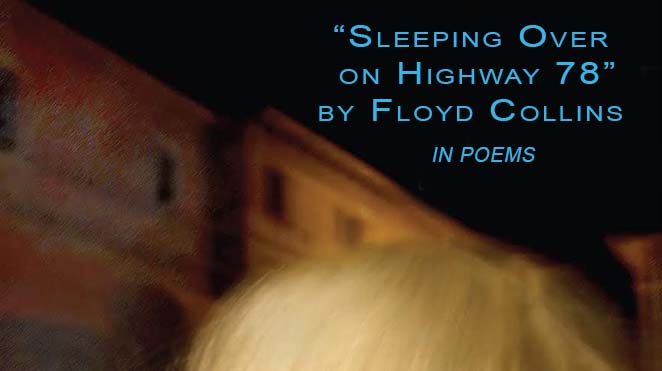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我发现自己在家乡的IGA买杂货。我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度过悲伤的开始,但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却是这样途中,它们需要吃东西。“同情砂锅”还要过一两天才会送到。母亲去世后,照顾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小心翼翼地推着手推车,希望不要看到任何我认识的人。镇上的每个人都听说了妈妈生病的消息,但我真的不想在软饮料货架上宣布她去世的消息。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在用海绵擦拭母亲消瘦的身体,听着她在死亡加速的过程中支离破碎的思绪。这让我很惊讶——所有的谈话。我原以为一个快死的人会累得无法交谈。然而,妈妈似乎不安分,每次只睡几个小时,然后打电话给我带她出去抽烟。她坐在甲板上,纤瘦的手指上摇摇晃晃地挂着香烟,讲话时时而说教,时而悲叹,时而慈爱,时而责备。
我试着倾听。我知道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什么都做不好。当我挣扎着给她输氧管时,她会翻白眼,叹口气。我知道她已经不太正常了,但那刺痛了我。在那些时候,我希望妈妈家里有比健怡可乐更烈的东西。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能和妈妈一起看电视的时间最多危险我父亲在我9岁时意外去世之后我的母亲是个奇迹——勤奋、有趣、强壮。她没有化妆,也没有佩戴珠宝,但她很漂亮,橄榄色的皮肤和温柔的棕色眼睛。她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72岁时,她还在割自己的一英亩草坪。
当妈妈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记得我以为我们刚刚进入了真正美好的阶段——我们的关系完全轻松,不受需求的影响。我喜欢回家。走进母亲的房子,闻到柠檬蛋糕的香味,即使在冬天也有74度的温度,总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人,她的爱不会因为我的错误而改变。她的拥抱是温暖的接纳,没有它,我担心我会崩溃。
 医生说她只能活三个月了。我不确定是在她身体还相对健康的时候,尽早花尽可能多的时间陪她,还是等到她需要照顾的时候再花。我决定在第一个月请几天假来陪她。她还能吃东西(虽然吃得不多),所以我会从她最喜欢的餐馆买墨西哥菜和奶油甜饼卷当甜点。那是美好的日子。我们会聊天,吃饭,她会打盹。我问了她一些以前从未问过的问题,关于她和我父亲的求爱,关于她的梦想和遗憾。
医生说她只能活三个月了。我不确定是在她身体还相对健康的时候,尽早花尽可能多的时间陪她,还是等到她需要照顾的时候再花。我决定在第一个月请几天假来陪她。她还能吃东西(虽然吃得不多),所以我会从她最喜欢的餐馆买墨西哥菜和奶油甜饼卷当甜点。那是美好的日子。我们会聊天,吃饭,她会打盹。我问了她一些以前从未问过的问题,关于她和我父亲的求爱,关于她的梦想和遗憾。
我们还谈到了她的恐惧。她是一个有信仰的女人,但她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说,最重要的是,她害怕不再是她孩子和孙辈生活的一部分。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她把她收藏的CD给了我。听贾德夫妇唱歌成了我上班路上的例行公事。
有一段时间,她似乎活得比预言的时间长。她觉得累,但不疼。然而,体重秤却显示出不同的情况,她的体重跌至90磅以下,然后跌至80磅以下。
在她死前两天,妈妈停止进食。我握着她的手时,她的眼睛呆滞。“我不想有这种感觉,”她说,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忽视自己的痛苦。当我们打开临终关怀护士给我们的急救包时,我以为容器贴错了标签。死亡不是紧急情况——不是在这里,不是对妈妈。死亡是一个终点,自从医生说“肺癌”和“不能手术”以来,她就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有时死亡就像洪流一样涌来。这是一种缓慢的滴漏——稳定,无情,并非完全不受欢迎。
她死前一晚我是在她房间的地板上度过的。作为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到的,我值夜班才算公平。但我想去那里。我不想离开我妈妈,我也不想让她离开我。我们在一起,就我们俩,在我哥哥和姐姐搬出去之后很多年了。我还是个婴儿,我吸着妈妈的气味,现在混合着腐烂的预兆。
晚上,我被锅里沸腾的泡泡声吵醒,就像我姐姐以前用混合粉的盒子给我做通心粉和奶酪一样。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意识到这就是我在临终关怀材料中读到的临终嘎嘎声。我坐在妈妈的床边,抚摸着她的脸颊。她已经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了,但这是第一次有死亡的感觉。我想起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夜晚,伴随着60年代的音乐跳舞,母亲的笑声像风铃一样回荡在我耳边。我把头靠在她脆弱的胸膛上哭了起来。
我按照他们的指示,给临终关怀中心打了电话。护士出来说妈妈最多只能再活一天。当我们把护士送出去,回到床边时,妈妈已经去世了。就好像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要私人空间。也许她只是想证明护士是错的。那就像我那倔强可爱的母亲。
她走后,房子似乎变了。虽有所减少,但并不牢固,它的墙壁随时都可能倒塌。我最后一次给母亲打扫卫生,穿好衣服,我意识到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所房子了。
当我开着熟悉的蜿蜒的双车道高速公路去商店时,我试图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个新的现实。我身上一些根本的东西已经改变了。我不再是女儿了。当我父亲去世时,我觉得他的缺席给我留下了印记,好像我家庭中的空洞定义了我。事实上,它一直如此。我是那个经历了悲剧的人。我的朋友们不能抱怨我身边的爸爸。现在我又会成为被排斥的人。36岁,没有母亲,没有父母。那个与过去的纽带已磨成细绳,因记忆而闪闪发光的人。 The one for whom the future has to be enough.
我买了橙汁,因为尼克从来不喜欢我妈妈买的商店品牌。我的大儿子一天能吃下三碗麦圈,所以我抓起了那个大盒子。我路过软奶酪和燕麦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给妈妈带了很多次。当收银员给我收据时,我微笑着看着她,直到我回到我的本田车里才哭了起来。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当我看到丈夫的车停在车道上时,我环顾了一下客厅,尤其是沙发上曾经属于母亲的地方,她的报纸、眼镜和单词搜索书就在旁边。然后我打开门,紧紧地抱着我的孩子们。我跟着他们进了屋,准备重新开始。

版权所有©2020 by Heather Iverson。版权所有。希瑟·艾弗森(Heather Iverson)是一名律师,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住在纳什维尔。她来自田纳西州东南部,获得了李大学的英语学位,并就读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大学的法学院。
标记: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