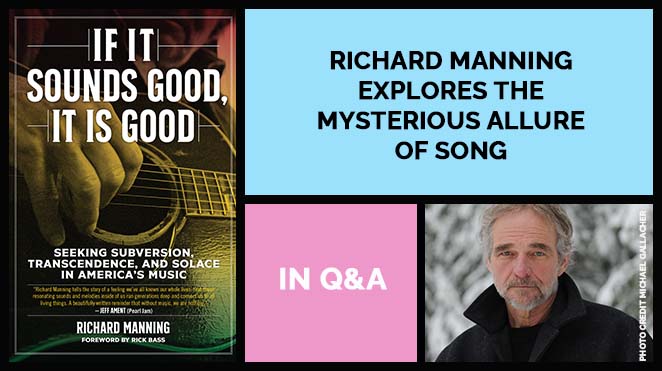当我7岁左右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建了一个堡垒,我叫她珍妮。

珍妮是那朋友我们在微波炉里做芥末小苏打蛋糕时差点把她的房子给烧了。他想把我的沙盒变成一个大坩埚,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泡泡汁和碎树叶调制药水来喂住在我院子里的巨怪了。他相信有马精灵——牙齿精灵一样的生物,只有用鞋盒和银河棒做一个陷阱才能抓住它们——他让我也相信了。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朋友,对吧?
那天晚上,我和珍妮建堡垒的时候,我们选择用硬纸板,这种材料也有它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不透气。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自然地,我们需要制造气孔。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房间的另一边向堡垒扔剪刀。
当珍妮开始扔剪刀时,我碰巧在堡垒里。我记得刀片撞击纸板的声音,它们留下的小弹坑,但我不记得有什么害怕。我信任我的朋友。我甚至信任剪刀;从来没有人给过我不这么做的理由。总而言之,我没有多想,而且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这么想——如果不是我母亲在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时候,在剪刀扔到一半的时候走进来。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受到了什么惩罚,但我的惩罚是这样的:我妈妈让我站在她巨大的戴尔电脑前,打开谷歌Images,搜索“剪刀伤”。
我记得看到图片搜索结果时很不舒服,特别是因为我当时甚至不允许看PG-13级的电影。但是,再说一次,我不记得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恐惧是一种只有在之前模糊的、假想的威胁真正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才会出现的东西。当它终于长得足够近,让我们知道它来到我们脚下时是什么感觉。

两年前,我遭遇了一场车祸。在那之前,有无数次我都在想,我旁边的车会不会突然冲到我的车道上,街对面的卡车会不会闯红灯,我右边的骑自行车的人会不会越过白线。但每一次,我都提醒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每一次,我都继续开车,但它没有。事故发生前的几秒钟,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那半英寸的东西朝我过来,也没有什么不同:我拒绝让自己想象被撞的感觉,直到我听到金属摩擦的声音。直到这时,恐惧才从窗户涌进来。
幸运的是,在11或12年前的那个晚上,我的朋友珍妮瞄得很准。剪刀从来没有打到我,所以我从来不用去想象如果被它打到会是什么感觉。我想,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没有多少WebMD的图片或者实习医生格蕾截图可以让人们关注潜在的痛苦。我想在这方面我母亲和我是不同的。她更早地感受到了恐惧:她的耳朵竖起来了,她的目光放大了。也许她不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害怕恐惧;她竭尽全力去避免。她让水淹了我们的房子,她自己就浮在水里。但通过这种方式,她从来不会猝不及防。这样,她就安全了。
最近,我一直在想那个堡垒和剪刀,还有我母亲确保我安全的方法:喂我一点她希望尝起来像恐惧的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在使用同样的技术。但它仍然不起作用。
我是阿默斯特学院即将升入大二的学生,我们学校已经决定允许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秋季学期返校——有大量的社交距离指导方针,黑镜子症状自我报告,戴口罩的要求,以及禁酒时代的禁酒规定。他们几乎尽了他们所能来创造一个安全的校园,除了不让任何学生回来——我母亲认为他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
题外话:我经常说“我妈妈”,这让我觉得不自在——我在上大学;我19岁。我不应该总是拿父母的事说事。然而,对我来说,这是不同的。
在单亲妈妈的陪伴下成长意味着打破了典型的亲子界限。大多数的决定都是一致的,所有的因素和事实都摆在桌子上,供我们两人分析和研究。我总是被赋予大量的责任来交换,嗯,大量的责任。我的母亲对我一直是透明的,我也必须对她一直是透明的。因此,与我的许多朋友相比,愚蠢的决定让我产生了更多的负罪感。或者至少是另一种内疚。感觉就像我在滥用自己的权力。

现在,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难说:“我要做我自己的决定,她也可以做她的决定;我是一个成年人。”因为她从不替我做决定。相反,是她做的与我。因此,没有必要推翻王位,逼迫她下台,以便接替她的位置,掌握我自己的人生。我一直在那里,我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被扔到我的脸上,就像从海上飞溅的浪花。
所以,当我引用我母亲的话时,并不是说她在摆架子。只是她很重要。她的意见和我的一样重要。她的恐惧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读着年轻人感染COVID-19的人数,还是给我看病人使用呼吸机的视频,都不能给我带来真正可以握在手里的恐惧,这让她非常沮丧。这种恐惧足以改变我的方向。
我希望我害怕生病;我希望我们都是。但我不是。我们不是。不够的。然而,如果我在我母亲的屋檐下,我害怕她生病,我害怕将病毒无症状地传播给其他人。所以,我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需要上厕所时就回家,以避免踩到朋友的房子里。但我不怕生病。我怎么能证明把我母亲的恐惧一端系在我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在我们的家上是合理的,就像一个主人把他们的狗拴在杂货店外面,而它不是我自己的狗一样?
我害怕回学校还有其他原因。我害怕未知、空虚和远方。无菌取代了温暖。我想在校园里建一个新家,而我已经建好的房子的遗迹到处都是,由于病毒,没有一个可以抢救。
但也许,就像我母亲一样,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害怕恐惧。因为现在,我内心深处都想要一场我能承受的风暴。想要一阵风把我吹倒,好让我记得如何重新站起来。我们不是都厌倦了平静的海水和死气沉沉的空气吗?我们不是都对检疫的惰性感到不安吗?这种惰性是由大流行这种暴力的东西带来的。
那么如果珍妮把剪刀扔到离我脸几英寸的地方我只记得没有受伤。但我不知道,回到校园后,我所记得的是否只是没有生病。如果恐惧抓住了我,到那时就太晚了。然而,许多年前,我们只是因为担心如果不扔剪刀,就会窒息而死才会扔剪刀。

版权所有(c) 2020年由Bianca Sass。保留所有权利。比安卡·萨斯(Bianca Sass)是阿默斯特学院的本科生,也是田纳西州人文学院的前实习生。她的文章发表在普发大学的杂志上凤凰她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她是纳什维尔本地人,毕业于Harpeth Hall。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