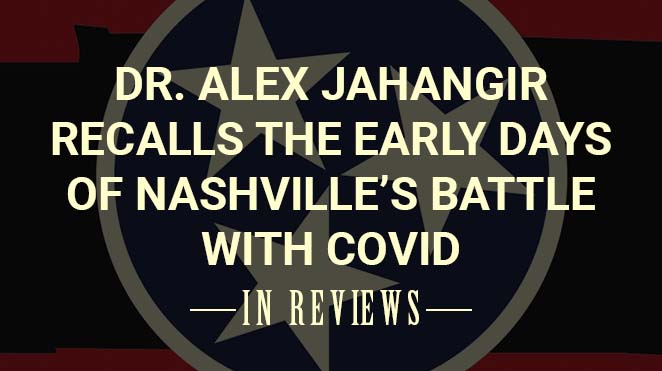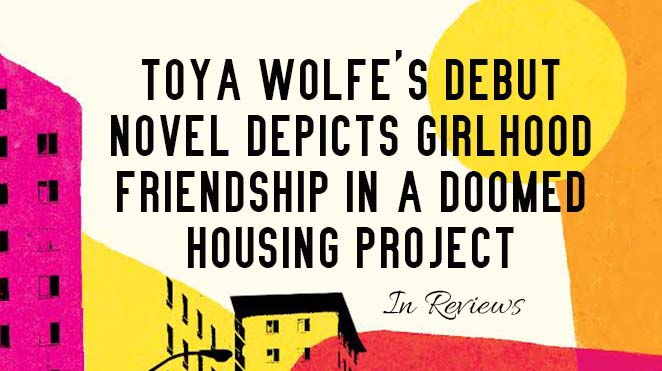烟囱里冒出滚滚的木头烟,我确信那个大胡子又用了太多的木头。我母亲在山下租了一间乡村小屋给他住,即使一个人住也很小,不过水泵旁那辆破旧的校车还可以作为储物的地方。夜晚很冷,但空气很虚弱,烟囱里冒出的烟一缕缕地滞留在那里,不愿继续前进。
我假装不在家。窗帘拉上,我把黄铜灯放在地板上,足够照亮我的路,而不让窗户玻璃发红。墨菲吞下了他的树皮,只要我把他夹在我的膝盖之间,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精神退缩,在他的胸膛里猛扑过去。
 今天下午,我母亲去了离这里很远的哈特,去收集她的古董摊位上未售出的物品,并永远关闭商店,所有破旧的灯笼,她去年夏天在萨吉诺旧货市场上买的生锈的工具,涂层粗糙弯曲的生锈的锯子,边缘光滑的螺丝刀,木制的台阶凳和写着祝福这个家而且靠太阳生活,靠月亮恋爱.画在谷仓木植物上的短语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了微小的碎片,我在睡梦中抠它们。我很想吃这房子里从来没有的食物。
今天下午,我母亲去了离这里很远的哈特,去收集她的古董摊位上未售出的物品,并永远关闭商店,所有破旧的灯笼,她去年夏天在萨吉诺旧货市场上买的生锈的工具,涂层粗糙弯曲的生锈的锯子,边缘光滑的螺丝刀,木制的台阶凳和写着祝福这个家而且靠太阳生活,靠月亮恋爱.画在谷仓木植物上的短语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了微小的碎片,我在睡梦中抠它们。我很想吃这房子里从来没有的食物。
这个大胡子男人拖着脚从他的小屋走到他的卡车上,没有手电筒。我停下来打开门廊的灯,但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在黑暗中认得路了。我和那个大胡子男人只说过一次话,他对我的谨慎态度表明,他被警告过不要和我对话,就像我被警告过不要太靠近他的船舱一样。每当我拖着鱼尾下山时,我就会把车开向校车,有时会关上自动门,看看里面有什么新鲜事。
今晚,我等着看我母亲是否会把本森爵士连同她那些卖不出去的古董一起送回家;本森爵士从夏至开始就是她的男朋友,他坚持先生好像它能擦亮皮革一样。大多数情况下,这让人困惑,让他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他是开明的当我洗泡泡浴的时候,我妈妈靠在我身边,就好像这是她一直保守的秘密一样,我想,哦。那么。我的错误.我从排水管上拔下塞子。
本森爵士想跟我交朋友,却徒劳无功,而我却玩弄了他的善意。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小玩意和小陶瓷动物——刺猬和兔子——粘在卡纸上的方块上,我发现了一个关于这些微型哺乳动物的真理:雕像越小,越不可能被打破。
 我母亲在我背后为我的轻蔑态度列出了各种借口,列举了我活了多少年,青春期,月食等细节神秘的妈妈,当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吉夫斯和伍斯特,她把姜黄粉撒在我的微波炉爆米花上,就像神奇的仙尘一样。
我母亲在我背后为我的轻蔑态度列出了各种借口,列举了我活了多少年,青春期,月食等细节神秘的妈妈,当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吉夫斯和伍斯特,她把姜黄粉撒在我的微波炉爆米花上,就像神奇的仙尘一样。
现在你一定在想,我和那个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话的。当某件事被禁止时,四风就会像狼群一样合谋。但它并不引人注目,否则我会直接描述它。他重重地敲了敲我们家的前门,那是一个真正的推销员,他拿出一个蓝色的塑料汽油容器,晃来晃去是空的。他斜着站着,手掌压在门框上,支撑着他那庞大的身躯。墨菲跳上屏幕,像猫一样舔着电线。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他说着,把空罐子敲在屏风下面的木板上。在他身后,他卡车的前灯照亮了我们家之间的草地。仿佛除了那两颗光锥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狂喜的昆虫在琥珀中反叛,两边是峡谷。
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说。
在谈话中,有一个空间,我没有用言语或手势来填补它。
但你都没看他说。
我的怀疑是重大的。
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用这种方式说话,以稳定的焦点和简短而尖锐的陈述。我学会了靠在屏幕上,这样我裸露的肩膀就会碰到丝网。我看着她以这种方式开始和结束一段感情,有时就在这扇门前,有一次穿着最漂亮的白裙子。
墨菲呜咽着,新栽的树在九月的风中抽动着。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它们可能会断成两半,然后我想起它们有多小。今天晚上,这个大胡子男人第二次离开他的小屋,穿过砾石走向他的卡车。他脚步缓慢;碎石在他身下蔓延翻滚。我希望他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然后我希望我妈妈今晚回家时没有本森爵士,这样我们早上就可以把香肠弄得一团糟,然后用咸油煎鸡蛋。
墨菲从他的羽扇豆根部嚎叫起来,大胡子转向我们厨房的窗户,卡车驾驶室的光线温暖着他的后背,在他的脸上投下阴影。
我们在分隔车道和乡村道路的山脊上见面。它前后弯曲,从鸟瞰角度看,是一个拉长的S形。恐怕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我说。我想躺在马路上.
我还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他说。我也想躺下.
我们脚下铺着冰冷的柏油路,我想象着母亲的锯子从天上掉下来,墨菲在屋里叫嚷着,他的吠声惊慌失措,胡子男人躺在我旁边,僵硬而静止,一个普通的人。我的母亲随时都可能乘本森爵士的马车回家,我祈祷他们不要在夜晚的黑暗中看到我们,不要用斑白的轮胎在我们的小腿上碾过,让我们共同的破碎,如果上帝愿意,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愈合。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自从我母亲突然离开一个星期以来。
版权所有(c) Rosie Forrest 2014。版权所有。罗茜·福里斯特拥有新罕布什尔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她的故事曾出现在SmokeLong季度,威士忌岛,&审查,《咬人:闪电小说选集》.的2013位特聘在Interlochen艺术学院,她现在担任范德比尔特青年才俊计划的学术和住宿协调员。与其他获奖者一起纳什维尔读取故事大赛,评委是门廊作家团体,罗西·福雷斯特将在诗人的书2014年3月30日下午2点在纳什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