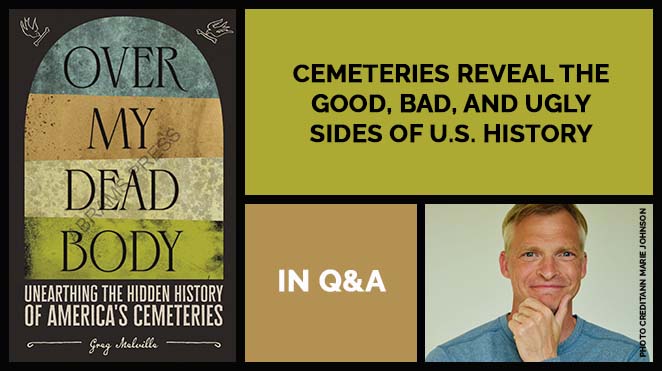这座建筑是用石头建造的。在它的一端,有一个卖酒的商店。在它的后面,有一个采矿营地,那里有成排的房子,是一家煤炭公司为工人及其家人建造的。这家酒铺的玻璃上用字母写着“蒙吉亚多斯”(Mongiardos)。一个五英尺高的男人站在柜台后面。他头顶的头发呈波浪状。男人笑了。他脖子上挂着个摄像头。酒铺金属架子的正面边缘用红黑字写着每瓶酒的价格。货架的正面边缘排列着人们在酒店或酒店前面拍摄的照片。 There are hundreds of photographs, pictures of coal miners with dust on their faces; pictures of politicians, smiling, with their arm around the man with the wavy hair; pictures of shirtless men with tattoos on their chests; pictures of women in prom dresses; pictures of young men in tuxedoes with their hair parted in the middle. The pictures are printed on paper. They seem, for the most part, to have been shot on film. These rows of pictures on paper tell the story of a drinking people. They are the feathers of a great, drunken bird.
* * *
 流经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河流一般看起来都是绿色的。一家化工厂沿着河岸绵延近一英里。这家工厂有十几个大烟囱,几组烟囱分布在几英亩的土地上。沿着建筑物的墙壁和它们之间有无尽的弯曲和转弯的管道工程。有几张灰色和绿色的塑料片,有几层楼高,嵌有铁丝网,用作窗户。这些建筑是砖砌的。他们的烟囱飘着烟。皮带嘶嘶作响,齿轮转动,里面的机器嗡嗡作响。有一种高中科学实验室失控的味道充满了工厂,并扩散到工厂周围的城市和农村。这种气味很酸,很刺鼻。 One’s eyes water at the smell, until one grows used to it.
流经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河流一般看起来都是绿色的。一家化工厂沿着河岸绵延近一英里。这家工厂有十几个大烟囱,几组烟囱分布在几英亩的土地上。沿着建筑物的墙壁和它们之间有无尽的弯曲和转弯的管道工程。有几张灰色和绿色的塑料片,有几层楼高,嵌有铁丝网,用作窗户。这些建筑是砖砌的。他们的烟囱飘着烟。皮带嘶嘶作响,齿轮转动,里面的机器嗡嗡作响。有一种高中科学实验室失控的味道充满了工厂,并扩散到工厂周围的城市和农村。这种气味很酸,很刺鼻。 One’s eyes water at the smell, until one grows used to it.
河边的那家工厂生产的化学制品,就是那个卷头发卖酒的人的相机里的胶片。成千上万的矿工和他们的家人使这个卷发男人和其他人靠卖酒赚钱成为可能。成千上万的化工工人使他们的照片得以拍摄。在所有照片都被用胶片记录下来的近百年里,每一次去多莱坞的旅行,每一次婚礼,每一次舞会,每一张照片,每一场高中橄榄球比赛,每一次生日派对都被用照片记录下来,很可能都是由田纳西州金斯波特河边的那家工厂生产的一种化学物质产生的。
这家化工厂的建筑物都有编号。这座编号为190的建筑曾经生产聚乙烯和聚丙烯颗粒。塑料颗粒。这些颗粒中的许多被卖给了制作胶片的公司。但是190号大楼的机器操作员也生产塑料小球供其他公司使用。这些颗粒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工厂,在那里它们被加热,并被塑成许多东西,包括方向盘和割草机部件,链锯防护装置和卫生棉条涂抹器。
塑料在楼上的190号楼分批混合,用的是所谓的班伯里搅拌机。混合后,一批批的塑料被放入挤压机,挤压机将塑料拉伸成一串串颜色鲜艳的合成扁面条。挤压机将塑料意大利面放入长托盘中冷却,然后将其切成颗粒,放入一个能装1000磅的盒子或更大的金属料斗中。包装盒用金属带密封起来,装上一辆拖拉机拖车,送到工厂的配送处,也就是产品发货的地方。料斗被带到包装区,放在装袋机上,以50磅为单位将小球分装到一个双层厚的纸袋中。一名操作人员设置袋子通过封口机,将袋子粘上。操作员把这些袋子堆在一个托盘上,然后把托盘装到一辆开往配送的拖车上。
在1983年和1984年的夏天,人类操作了190年的机器。人类装载产品。人类驾驶叉车。在1983年和1984年的夏天,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开着铲车,封好袋子,捆好箱子,把产品装到拖拉机拖车上。在我去190号之前,我做过的唯一有报酬的工作就是割草。在父亲的胁迫下,我割了我家院子里的草;在母亲的胁迫下,我又割了我家旁边街道上其他院子里的草。为了赚更多的钱,减轻压力,我去了工厂工作,这样挤出机操作员、班伯里操作员和船运操作员就可以放暑假了。
其中一个挤压机操作员叫贝尔。另一个叫月亮。他们俩都很结实。他们把工作服的前面敞着。贝尔戴着透明框架的安全眼镜,周围有穿孔塑料。穆恩秃顶,留着胡子拉碴的胡子。熊的胡子是红色的。我们被告知要在一间用玻璃围起来的房间里进行短暂而频繁的休息,这个房间被称为“休息小屋”,紧挨着浓缩铀棒的办公室。棒子就是我们所说的顶。我们会坐在棚屋里聊天,抽烟,休息。 One summer, Bear and Moon helped me collect Planters peanut bar wrappers. If I saved fifty of them, I would be able to send off for a free Boomtown Rats album. Bear would fish wrappers out of the trash for me. I was very glad to be able to share my excitement about the Boomtown Rats with Bear and Moon.
 有一次他们下了第二班,贝尔和月亮去跳青蛙舞了。他们把牛蛙肩膀那么宽的三叉戟固定在8英尺长的高尔夫球场旗杆上。那天晚上,他们走在小溪和池塘边,腰带上别着矿工的灯,把灯照在水边。当光线照射到一只牛蛙时,它的呱呱声停止了。“他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人会说,然后旗杆叉就会扎进青蛙的背部。贝尔和莫恩用铁丝衣架围了一个圈,把钩子弯在两端,把他们抓住的青蛙串在铁丝上,把铁丝穿过青蛙的下颚。当他们带着一群青蛙回到车上时,他们把每只青蛙都拿起来,用一把大刀砍断了它的腰,只留下了腿,把剩下的扔进了杂草里。他们建议人们在煎之前把青蛙腿浸泡在盐水中,以免青蛙腿跳出锅去找他们丢失的青蛙。
有一次他们下了第二班,贝尔和月亮去跳青蛙舞了。他们把牛蛙肩膀那么宽的三叉戟固定在8英尺长的高尔夫球场旗杆上。那天晚上,他们走在小溪和池塘边,腰带上别着矿工的灯,把灯照在水边。当光线照射到一只牛蛙时,它的呱呱声停止了。“他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人会说,然后旗杆叉就会扎进青蛙的背部。贝尔和莫恩用铁丝衣架围了一个圈,把钩子弯在两端,把他们抓住的青蛙串在铁丝上,把铁丝穿过青蛙的下颚。当他们带着一群青蛙回到车上时,他们把每只青蛙都拿起来,用一把大刀砍断了它的腰,只留下了腿,把剩下的扔进了杂草里。他们建议人们在煎之前把青蛙腿浸泡在盐水中,以免青蛙腿跳出锅去找他们丢失的青蛙。
挤压机操作员贝尔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李县,与肯塔基州的哈兰县接壤。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在哈兰上社区大学的课。我是她的导师,要求她口述一段历史。她录制了一段与父亲的对话,父亲向年轻女子描述了他的父亲,也就是年轻女子的祖父,一位煤矿经营者,是如何签署了一份价值7亿美元的合同,为金斯波特的化工厂提供煤炭。30年7亿美元,这是录音里的人说的。哈兰县的许多人都靠采煤为生,帮助那位年轻女子的祖父履行合同。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那段时间拍摄的。有些人可能喝了酒。我不能肯定。我只知道这一点:在拿到七亿美元的那段时间里,哈兰县基本没有酒喝,那个卷发男人告诉我,他在那段时间里向哈兰县的私酒贩子卖酒,其中包括一个叫马格·贝利(Mag Bailey)的人。据说,他供哈兰县的几个律师上了法学院,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很少,甚至很少。
人们知道在煤矿工作很容易死亡,特别是在地下煤矿。屋顶下降。肋骨。那里有炸药和携带大量电力的粗电缆。有致命的挥发性气体。矿工们需要保持警惕。矿工们需要互相照顾。矿工们需要知道他们可以互相信任,不会失去他们的脑袋。所以他们互相测试。他们会在彼此的洗发水瓶里放机油。 There are stories of them strapping young miners together, lip to lip, with electrical tape when they cannot get along, and leave them lying in mine passages until they kiss and make up. There are stories of nailing one another’s dinner buckets to the beltline. A miner who cannot tolerate this is not likely to keep his head when death comes knocking. That is the kind of thing most of us would like to know ahead of time, particularly if we knew we would be braving death on a daily basis.
在塑料厂工作时死在工作上不像在煤矿那么容易。但危险依然存在。有一次,一个男人的手被塑料挤出机扯掉了,他的同事不得不回去从断指上取下他的结婚戒指。一个粗心的操作人员可能会在一分钟内毁掉价值数万美元的原料,比如把一批原料扔进挤出机,或者休息时间过长,让料斗溢出到工厂地板上。所以在塑料厂也有欺辱。例如,一名叉车司机必须到外面去取托盘,所有的材料都在托盘上运输,至少每班一次。当铲车工出去取货盘时,他的同事在装着数千磅重的箱子的塑料袋里装满水,然后从楼顶往他头上泼水,这并不是没有听说过的事。覆盖在铲车顶部的钢笼可以保护操作人员不被摔断脖子,但却不能保护袋子破碎和铲车操作员被100加仑的水“淹死”。
有些欺侮是为了卑鄙而卑鄙。有些是为了打发无聊。但是,欺辱也给我们上了一课,那就是这是一份严肃而危险的工作,有一定的忍受粗暴对待的能力是能够坚持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成为一个可靠同事的一部分。
无论是我工作过的塑料厂,还是我听说过的大多数煤矿,工作场所都以男性为主。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看出,在欺辱中,有一种男子气概,喜欢“足够强硬”来承受工作的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己的空间,以对抗那些可能不符合相对狭窄的工作能力定义的人。正如我所经历的那样,矿山和塑料工厂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典产物,也是由工业资本主义支持和支持的父权制的典型产物。
* * *
我母亲19岁就结婚了。我出生时她24岁。当我长大到可以照顾弟弟的时候,我妈妈回到了大学。她去了东田纳西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成为了一名注册护士。我母亲担心自己的智力和能否从大学毕业。她是护理班的第一名。她父亲是金斯波特化工厂的副总裁。她的母亲从不外出工作。
我父亲24岁就结婚了。他毕业于田纳西大学,并获得了篮球奖学金。我父亲的母亲在他四岁时去世了。他是由他父亲的姐姐、父亲和继母抚养长大的。我父亲在两个州就读了四所不同的高中。他的父亲是W.T.格兰特公司的一个店主。我父亲成了化工厂的主管。他管理着几个仓库用于制作香烟过滤嘴的原材料的分销。他和金斯波特的许多人一样,死于癌症。
我母亲高中毕业后,她的父母送她去俄亥俄州北部上大学,选择这所学校的部分原因是它离我父亲很远。当他们终于在一起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我的父母从她的父母那里收到了一套银器作为礼物。我母亲总是告诉我她母亲告诉她,如果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他们会把银质的戒指刻上。它做到了。银器仍未雕刻。
我母亲2016年去世了。有一次,她一边打电话,一边把一包奥利奥的crème吃光了,还把饼干喂给狗吃。她曾经请医生用铁丝把她的下巴封起来,帮助她减肥。她教新生儿游泳。当我的表兄妹陷入困境、无处可去时,她收留了他们,即使她不同意他们所做的事情。她在自己出生的医院做了一份病人维权律师的工作,以毫不畏惧的勤奋把对医院病人接受的医疗服务的抱怨带到有能力对此做点什么的人那里。她退休后,医院取消了她的职务。
当我母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和她的双胞胎兄弟经常被送到田纳西州的欧文,在他们的祖父母和姑姑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有一次我妈妈得了腮腺炎。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她的阿姨黑兹尔问她怎么做才能让她感觉好点,我妈妈说:“倒立。”黑兹尔阿姨照做了。还有一次,我母亲8岁时,她去欧文她祖父母家后院的煤堆那里,发现祖父趴在煤堆上死了。周围没有其他成年人,所以她告诉了一个邻居,邻居让她到街对面等着,直到情况得到处理。当我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她不相信自己被送走了。她说:“他们以为我会看到比我已经看到的更糟糕的东西吗?”
我的母亲庇护违法者,为没有发言权的人说话,对抗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她认为正确的事,也许最勇敢的是,她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理解。有一次,在她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开车送她去我哥哥在弗吉尼亚州怀斯的家,一辆小货车开过,车床上插着一面南方联盟的旗帜。母亲看着卡车驶过,旗帜在微风中飘扬。她说:“你明知道会伤害别人的感情,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的母亲是我所认识的最无所畏惧,也是最紧张的人。尽管她在一生中采取了各种立场,但她始终坚信我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如果我们不每半小时给她打一次电话,我们就死定了。如果北美任何地方的路上结了冰,我们就得呆在家里(除非我们是来拜访她的)。在她看来,蛙舞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带来麻烦。喝酒、在外面呆到很晚、冒险离开金斯波特太远,也是如此。她旅行时很少不带自己的食物,假期中她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回家。忧虑是她生存的动力。
我母亲喜欢开玩笑。她喜欢听故事。她喜欢打牌。她喜欢我们围着她的桌子大笑。她焦虑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她面前的人不可能玩得很开心,除非她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要么她自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要么在我们面前摆上抹满黄油的食物,要么怂恿我们其中一个娱乐一下。
她去世后,葬礼在她受洗和结婚的教堂举行。那里有四百人。我和哥哥把我们能想到的关于她的趣事都讲了一遍。人们又笑又哭,失去了理智。她会喜欢的。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堆我们从未听过的故事。一位女士告诉我,当她第一次搬到金斯波特时,她第一次参加了金斯波特的派对,当她走进去时,看到一个女人在桌子上跳舞。女主人说:“别担心。这是芭芭拉·吉佩。她不喝酒。”
* * *
我在化工厂的经历让我想住在比金斯波特更深的山里,因此,1989年,我在肯塔基州莱彻县的媒体艺术中心阿帕尔shop找到了一份工作,这让我母亲很懊恼。1997年,我在肯塔基州哈兰县的东南肯塔基社区技术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协调了一个社区进程,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15万美元的拨款,用艺术来应对哈兰的处方止痛药危机。我们的小组,包括我所在大学的学生,就处方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OxyContin)、其他被误用和滥用的药物以及其他一切问题采访了社区成员。我们接受了这些采访,并与剧作家乔·卡森合作,写了一部叫做更高的地方.
我们采访的其中一位女性是在煤矿营里长大的。她妈妈走了。她的爸爸搬去了另一个煤矿营地,留下这个女人和她的兄弟们,他们都是孩子,自己谋生。为了赚房租,他们开了一个纸牌游戏,玩家大多是煤矿工人。有人问这个女人,她是如何不让这些打牌的成年人占她的便宜的。她回答说,他们总是在壁炉里生火,在火里放一根拨火棍,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朝她走来,她就会用那根炽热的拨火棍直接刺进他们的胸膛。
另一位年轻的女性受访者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这个女人嗑药上瘾了,被逮捕了,还得去见法官。她去法庭的那天,有一屋子的被告和她在一起。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钱。法官问女人:“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应该在这里。你来自一个好家庭。”女人说:“那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我只想说,‘他们应该在这里吗?他们的生活被毁了可以,我的就不行吗?“毒品不在乎你是谁。 They treat everybody the same.”
这两个女人的故事最终出现在我们的第一部戏中。在第一部《高地》中,我们试图探索的一件事是,或许我们应对毒品危机的方式,应该像我们在社区中应对洪水一样——共同应对,而不是试图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在剧本里,我们让打牌的女人和善良的家庭女人共同奋斗。但在他们达成共识之前,我们必须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当时,我们流传着一些关于包装狂的故事,我们认为这很好,因为各种阶级和背景的人都是包装狂。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的共同点。
为了将这两个角色联系起来,我们用了一个我和我母亲的经历。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去她的保险箱。在她所有的珠宝和现金文件里,有一把伞和一袋奶酪涂鸦。她说,她把它们留在了那里,因为有一天她匆忙进来,午餐吃着奶酪涂鸦,不好意思带着它们走出去。我担心当我妈妈来看戏的时候,她的感情会因为剧中的故事而受到伤害。后来我问她对这出戏的看法。她说"罗比,太棒了"我问她对保险箱的故事怎么看。她说:“看吧,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
到我们看第六部戏的时候,尽管所有的戏都有好听的音乐和有趣的故事,但人们还是想要一些更轻松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短剧,就像我妈妈的葬礼一样,每个人都讲关于死者的有趣的故事。那出戏,叫做生命就像一团水汽,采用了我们在第五部戏中介绍的角色,Sweet Betty。她的葬礼揭示了她曾多次濒临死亡——当一只啄木鸟开始啄她精致伪装的手时,她从鹿群里掉了下来,因为她的手握着拉紧的弓;她在滑索上谎报自己的体重,然后滑倒了滑索,差点压死一个青年唱诗班;她的眼睛里进了蓖麻豆的果肉,让自己剧烈地抽动;她在水太高水流太快的情况下坚持接受洗礼,靠偷浣熊的食物幸存下来,浣熊在卡车轮胎旁边的一根圆木上洗饭,贝蒂就住在圆木里。我们编织了这些故事,其中的一些版本可能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身上,当我们坐在我工作的社区大学的一间屋子里,像古代一样讲故事,一个故事通向另一个故事,眼泪伴随着捧腹大笑,娱乐的竞争是友好的和相互支持的——最好的空间,上帝的王国由荧光灯照亮,以Dairy Hut的玉米块为燃料。
我希望我妈妈能看到生命就像一团水汽.这是她的风格。她确实活了很久,看到我在我们的戏剧受到好评的鼓舞下,去了辛德曼定居学校的阿巴拉契亚作家讲习班,然后又去了其他的写作讲习班。她活着看到我出版了一本小说。她看到我读书,被人关心,被人写。这一切使她非常高兴。她对我去蒙贾尔多斯的事不太高兴或者,真的,跟酒混在一起。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很高兴当时在那里,因为蒙贾尔多斯走了,像电影画面一样走了,像我的190号楼一样走了,像大多数煤矿工作一样走了。
蒙贾尔多斯离辛德曼不远,有一年夏天,我们带着作家工坊的新朋友去看了看。所以我们才发现它关门了。大楼还在,但窗户是脏的,架子是空的。那些画面是如此美丽,所有那些生活在最快乐的时刻,最黑暗的绝望时刻,以及所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时刻,它们都消失了。
我不知道那些照片去哪了,那只大醉鸟的羽毛。也许那只鸟飞走了,羽毛完好无损,摇摇晃晃地飞上山脊,飞上高山的天空,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有一个人给我们讲所有人的故事的地方。也许吧。也许我会少喝点酒,这样我就能更好地记住我所听到和看到的所有事情,并能更好地讲述它,能更好地耐心和关心地听别人讲的故事。也许吧。那会让我妈妈高兴的。
* * *
好吧,总结一下,回到我的话题,我是多么的阿巴拉契亚人,我会这么说:我认为我比一些人更像阿巴拉契亚人,比其他人更不像。我会说我已经足够阿巴拉契亚了。我会说,我是由我的父母抚养长大的,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理解。我从小就被教育要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来创造意义。我学到的是,意义是复杂的、多变的、难以表述的,一个人在思维中加入的故事越多,就越难表达出意义。这是件好事,当一个人看到新事物时,要记住这一点——一个人在听到有关它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之前,是无法理解它的任何意义的。我从小就知道故事的一个好处就是一个人可能会理解一个故事的一个含义而另一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这种赋予世界以我们自己的意义的能力就是自由,是快乐,创造意义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我从小就被教育,我们都有义务努力,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倾听别人的故事——轻松的故事和困难的故事,快乐的和悲伤的故事,喜剧的和悲剧的故事。,我们都不得不工作,以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利听到,告诉所有的故事,每一个使我们自己的意义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是欺骗我们的邻居,我们欺骗自己的快乐生活,,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应该被迫花很长时间的车坐汽车,没有电台的永恒的人长大的地方他们不学习如何讲故事。
 版权所有(c) 2018年由罗伯特Gipe.版权所有。罗伯特·吉佩,插图小说的作者蹦床而且Weedeater她在金斯波特长大。自199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肯塔基州坎伯兰市东南肯塔基社区与技术学院阿巴拉契亚项目主任。本文发表于阿巴拉契亚清算这是对j·d·万斯(J.D. Vance)备受争议的畅销书回忆录的地区性回应,阿帕拉契山脉的挽歌.这本合集将于2019年3月1日出版。
版权所有(c) 2018年由罗伯特Gipe.版权所有。罗伯特·吉佩,插图小说的作者蹦床而且Weedeater她在金斯波特长大。自199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肯塔基州坎伯兰市东南肯塔基社区与技术学院阿巴拉契亚项目主任。本文发表于阿巴拉契亚清算这是对j·d·万斯(J.D. Vance)备受争议的畅销书回忆录的地区性回应,阿帕拉契山脉的挽歌.这本合集将于2019年3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