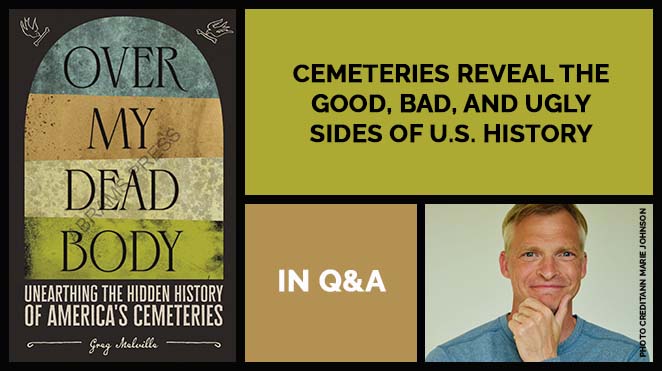我的疯狂始于一个星期五,持续了大约三个星期。拉开序幕的是矗立在文森法院广场上的一座19世纪印地安那第17团纪念碑,以纪念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动乱。很高兴能在战争中获胜,建造者不惜一切代价纪念他们英勇的英雄。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地面上有几堆焊接成金字塔状的炮弹,它们各自代表着胜利者头顶上的天空。
 这就是我要的:一堆19世纪的炮弹。我仰起头来欣赏上面的金属士兵,当我向前走,想看清楚比利·扬克时,我的右脚碰到了炮弹。我的脚没有动,但我的身体动了,我像一个士兵扑向地面躲避葡萄弹。
这就是我要的:一堆19世纪的炮弹。我仰起头来欣赏上面的金属士兵,当我向前走,想看清楚比利·扬克时,我的右脚碰到了炮弹。我的脚没有动,但我的身体动了,我像一个士兵扑向地面躲避葡萄弹。
虽然我的手腕有点疼——当然还可以忍受——但我们回到家后,我妻子说服我去诊所。拍完x光片后,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得意洋洋地说:“嘿,伙计,你把它弄坏了。”又看了一天对骨骼特别感兴趣的医生后,我发现自己左前臂上了石膏,我准备等待接下来的四周过去。我的手指还能用,现在我有了一种吸引力,可以让完全陌生的人开玩笑。
“这没什么,”给石头一样的石膏打上石膏的女人说。“我们会给你开一些温和的药。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但不会疼的,对吧?”我说。“现在还不疼。为什么现在要呢?”
“有些人受苦;一些不喜欢。你会看到会发生什么事,”她说,然后赶紧跑去用一块湿热的布裹住另一根肢体,它会变得像印第安纳士兵固定在他的纪念碑上一样坚硬。
我的石膏是白色的——他们告诉我这是最保守的颜色——开裂的骨头嵌在里面,就像花岗岩鸡下的蛋黄一样。我和它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很不安,但我告诉自己,这是意料之中的。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又增添了新的不适,不仅是前臂,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全身。在我的脑海中是最不祥的。
 “冰敷一下,”医生助理胡安妮塔(Juanita)在电话里告诉我。“吃你的药。不要想太多。继续做事吧。”
“冰敷一下,”医生助理胡安妮塔(Juanita)在电话里告诉我。“吃你的药。不要想太多。继续做事吧。”
我可以采取胡安妮塔建议的前两步,但第三步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陷入黑暗;我正以极快的速度滑下斜坡。我开始幻想如何从我受伤的手腕上撕下石膏,包括想象大锤、巨大的锡剪、几品脱的溶剂或油脂——任何能让我现在就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四周的时间。
我又打电话给胡安妮塔,她让我第二天早上去。我会的,我向她保证,但首先是另一个夜晚的前景,太阳又一次消失在伊利诺斯州的玉米地上:在一个地平线上,没有任何不同的景色能缓解一个俘虏饥饿的眼睛。
我把允许吃的药都塞进肚子里,用一袋冰裹住石膏和前臂露出的部分,然后躺到妻子旁边的床上。她尽她最大的努力说服我,提醒我明天早上石膏问题就会解决。我悲伤地凝视着她。她是好意,但她怎么会知道我的痛苦呢?
“别想那么多,”她说。“试着读点什么。”为了迁就她,我伸出我那只完好的手,拿起了放在床头柜上的第一本书。
是查尔斯·波蒂斯的南方的狗这是一本我读过很多遍的小说,我几乎放弃了它,这样我就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我想我应该允许自己快速阅读一下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的题词,他观察到,所有的生物,从最大的哺乳动物到最小的螨虫,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移动需求,陷入不安的运动中。
于是,我开始研究雷·米吉关于他妻子诺玛和前夫私奔后他所做的事情的叙述。就像我自己的情况一样,灾难突然降临雷,在他60英尺厚的书中抓住了他,打乱了他26岁重返大学的计划,开始教学,忘记他的内战历史课程,继续用诺玛作为数学练习学生,尽可能呆在离家近的地方。
雷·米吉很痛苦。他被包围在一场灾难中,就像任何数量的字面上的浇铸包围着任何数量的活四肢一样,但他并没有坐着不动。
现在,诺玛,那个有着柔和的手臂毛发和跳动的前额静脉的女人,开着雷自己精心保养的福特都灵和盖伊·杜普利一起逃走了。杜普利是个脾气暴躁的前记者,在小石城的每个酒吧都被人KO过。雷发现自己迷路了,被抛弃了,沉浸在私人的痛苦之中,拥有了杜普雷的六缸别克轿车,地板上生锈的洞,后座上摆满了糖果包装纸。
在这场灾难中,雷·米吉是否会躺在床上嚎啕大哭,梦想着被释放?他是否服用了过量的药物,并将冰袋压在身上?他把自己的困境告诉过愿意听的人吗?他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在哪里,在什么程度上受苦的吗?
不。雷拿了一张地图,通过检查盖伊·杜普利的信用卡消费记录,追踪了他和诺玛走的路线。他依靠过去的地理课程(聪明人没有知识是无礼的),得出了他必须做什么的结论。由于手头没有现金,他收集了他的政府债券,给那辆可怜的别克汽车加油,在门上挂了一个牌子,告诉所有人他要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动身去墨西哥。
雷·米吉很痛苦。他被包围在一场灾难中,就像任何数量的字面上的浇铸包围着任何数量的活四肢一样,但他并没有坐着不动。他不等待任何人的援助。他遵循了托马斯·布朗爵士在17世纪阐述的重要自然法则。他焦躁不安,不停地动着。
我受到鼓舞,从床上爬起来走了起来,冰袋托着我的石膏,头上的氢可酮嗡嗡作响。在我那空着的手里,我拿着波蒂斯的小说,在万物的躁动中徜徉,从中找到了慰藉。里奥·塞姆斯博士是波蒂斯的被革职医生,也是一辆名为“南方之狗”的残疾公共汽车的主人,他也给我指明了方向。他向雷讲述了文明世界中最伟大的作家约翰·塞尔默·迪克斯(John Selmer Dix, M.A),一位在所有情况下都主张对立极端的哲学家。
迪克斯写道,不要害怕行动,但不要仅仅为了行动而行动。花钱不为明天考虑,存钱以备不时之需。采取行动,然后反对那个行动,保持静止,继续前进。
在我被困住的状态下,在没有目的地的不安中,我发现雷·米吉的冒险正是我所需要的良药。它没有治愈;它没有做出虚假承诺。雷·米吉知道,生存就是忍受束缚,没有改变的希望。像雷一样,我发现我可以忍受等待早晨的到来。
有一次,一个老小丑给了雷·米吉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一条建议:“小心FLORR。”这就是我在监狱里不得不做的事。别再摔倒了。继续前进。遵守支配一切生物的法则,无论大小,疾病和健康。小心Florr。
在整个旅程中,雷遵循了这个建议。他把诺玛接回来,带她回到小石城的家,在他堆满书籍的公寓里,他很满意。当然,她很快又离开了他,这次是去孟菲斯,独自生活。但我知道这很合适。没有人从孟菲斯回来。

杰拉尔德·达夫曾在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任教,并在孟菲斯的罗兹学院担任学术院长。他最近的小说是在卡斯特;新版《没关系,妈妈:猫王双胞胎的未经授权的生活》将于今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