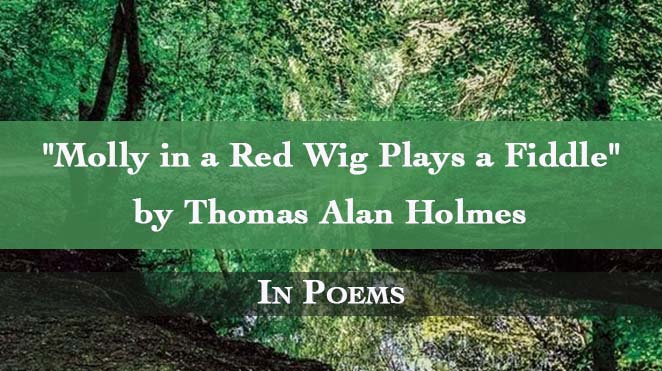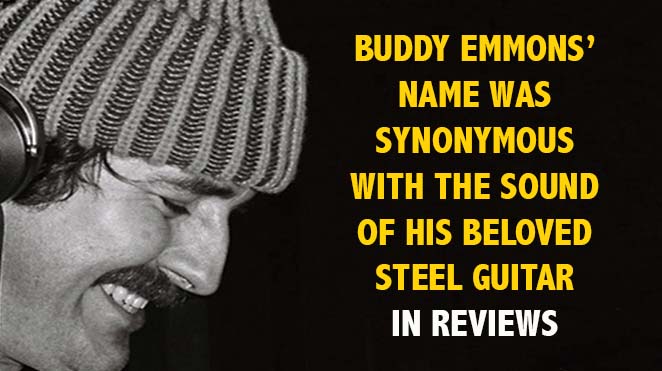在受损的宏伟在1995年出版的关于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的书中,诗人理查德·蒂林哈斯特(Richard Tillinghast)指出,学术就业的变幻莫测,频繁地从一个短期职位换到下一个,“把许多作家变成了脱离自己所在社区的无根游民”。蒂林哈斯特在孟菲斯出生和长大,他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学术游民,他的履历包括在哈佛大学、塞瓦尼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的教学工作。他还是一个专注的旅行家,曾到过遥远的印度和土耳其,在爱尔兰逗留了很长时间后,他最近回到了美国。
然而,“无根”这个形容词似乎不适用于蒂林哈德斯特,他一直承认自己在南方的成长环境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在1997年的一篇自传体文章中,他坦承了这一点“到听到‘Dixie’时喉咙哽咽,”但他在塞瓦尼读本科期间抗议种族隔离,并觉得有必要离开这个地区,去享受更自由的气候。尽管如此,他与斯瓦尼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计划于9月在那里定居。
蒂林哈斯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睡觉看在1969年,。之后的十卷包括我们的国旗还在(里面有他的长篇叙事诗《废墟中的塞瓦尼》),石匠的手,的新生活,最近,选择诗歌该书回顾了他40年的工作。蒂林哈斯特的诗歌采用了一系列的风格,尽管他早期对韵律和韵脚的精通使他的自由诗也具有明显的音乐性。爱尔兰诗人埃蒙·格伦南将蒂林哈斯特的诗歌描述为“一种文明情感的证明,它带着一些幽默和一些忧郁,驾驭着自己和世界的脉搏。”这一评价在蒂林哈斯特的主题和关注点的广度上得到了证实。1997年的诗《他的日子》(His Days),就像蒂林哈斯特的很多作品一样,抓住了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无言的痛苦和渴望:
但在某个肮脏的集镇的主要街道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喊出“爸爸!,” reaching for his father,
它像皮革的裂缝一样刺痛了他。
那时,痛苦似乎已经结束了。
水很宽,他游不过去。
蒂林哈斯特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同样有效。他2010年的诗“什么是不允许的”讽刺了以色列对加沙封锁的残酷。
你可能有南瓜和胡萝卜,
但是没有美味佳肴,
没有樱桃、石榴、西瓜、洋葱,
没有巧克力。
我们有一份清单,上面有三十多件物品是允许的,
但是我们没有义务泄露它的内容。
 除了诗歌,蒂林哈斯特还写了大量的批评作品。他评论新诗纽约时报书评二十年来,也曾为新标准和《华尔街日报》。除了他的关于洛厄尔的书——一位早期的导师——蒂林哈斯特还出版了一卷批评,诗与什么是真实;和发现爱尔兰,对爱尔兰文学和文化的反思。他还与女儿朱莉娅·克莱尔·蒂林哈斯特(Julia Clare Tillinghast)合作翻译土耳其诗人伊迪普·坎塞弗(Edip Cansever)的作品。他们的译作合集,肮脏的8月,于2009年出版。
除了诗歌,蒂林哈斯特还写了大量的批评作品。他评论新诗纽约时报书评二十年来,也曾为新标准和《华尔街日报》。除了他的关于洛厄尔的书——一位早期的导师——蒂林哈斯特还出版了一卷批评,诗与什么是真实;和发现爱尔兰,对爱尔兰文学和文化的反思。他还与女儿朱莉娅·克莱尔·蒂林哈斯特(Julia Clare Tillinghast)合作翻译土耳其诗人伊迪普·坎塞弗(Edip Cansever)的作品。他们的译作合集,肮脏的8月,于2009年出版。
蒂林哈斯特将于9月27日在孟菲斯大学进行诵读,随后于9月28日接受采访。他还将出席10月14日至16日在纳什维尔举行的南方图书节。他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和你决定在爱尔兰生活之间有什么联系,如果有的话?你居住的地方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蒂我在伯克利的一所借来的房子里给你回信。在你提出问题的时候,我还住在爱尔兰,我在那里度过了我成年时间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但现在我已经回到了美国。我居住的地方总是有力地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灵感。例如,在爱尔兰,我总是发现用韵律和格律来写作是很自然的,尽管我说不出原因。毫无疑问,这与这个地方的诗歌传统有关,尽管对我来说,我的诗歌所采用的形式总是出于本能或直觉。我把加州和自由诗联系在一起,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他们是否曾在这里生活过。印第安人认为人不只是一个个体,而是在这个地球上某个位置上的人,这种观念对我来说一直很有意义。
米兰:你最近的诗歌似乎通过具体的世界,普通物体的直接世界来表达。您认为您诗歌的侧重点与以前不同了吗?更窄了还是更精确了?
蒂:我本以为,我的诗一直是通过具体的世界说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自己是我那个时代的诗人,遵循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名言“无思想,只存在于事物中”和埃兹拉·庞德对诗人的建议:“怀着对抽象的恐惧前进。”我在Sewanee的导师Andrew Lytle一直坚决反对抽象主义,毫无疑问,这也影响了我。对我有影响的诗人从来都不是“思想”诗人,而是现实的商人,如罗伯特·弗罗斯特、约翰·克劳·兰森和罗伯特·洛厄尔。我想叶芝的诗里面是有思想的,但它总是有根据的。
米兰:您与您的女儿朱莉娅·克莱尔·蒂林哈斯特(Julia Clare Tillinghast)合作翻译了土耳其诗人伊迪普·坎塞弗(Edip Cansever)的作品。您能描述一下你们俩是如何合作的吗?谈谈翻译诗歌的主要挑战吗?
蒂:有些诗是我们每个人单独创作的。有一段时间,当我的孙子哈姆扎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睡得很多,而茱莉亚和我同时在安娜堡——哈姆扎出生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坐在同一间屋子里,来回地翻译,在字典里查单词,讨论措辞,等等。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她在弗吉尼亚,我在爱尔兰,我们就正在写的诗用电子邮件来来回回地交流。
几乎没有人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想知道,当人们不阅读诗歌所用的语言时,他们怎么能说自己在翻译诗歌。这么多“翻译者”都是字面上的小跑,或者他们认识懂这门语言的人。除非你能读到原文,否则我看不出你怎么能真正了解一首诗。土耳其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学习它所涉及的所有艰苦工作,是赋予我们成为翻译的权利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想出一个译本,一方面要以非常忠实的方式反映原文,另一方面又要作为一首英文诗独立存在。
我可能会注意到,一些诗歌,一些单词和短语,似乎无法从一种特定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此时此刻,我正在看a·e·豪斯曼的书的意大利译本,一个少年,在我对面的书架上。意大利语的书名?unragazzo dello Shropshire!我认为通晓两种语言的人对这个标题只能一笑了之。然而,这未必是意大利翻译家的错。只是意大利语中碰巧有一个听起来相当傻气的词来表达“小伙子”的意思。
 米兰:你有多美国?你有多南方?作为一个作家,国家或地区身份对你来说重要吗?
米兰:你有多美国?你有多南方?作为一个作家,国家或地区身份对你来说重要吗?
蒂:这个问题问得好,很难回答。我认为我很美国,也很南方,但同时,我不是美国人,也完全不是南方人。不过,我当然比我是美国人更南方。9/11之后,我——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人——对这首经常被邀请在教堂和犹太教堂唱的“上帝保佑美国”的歌彻底厌倦了。对我来说,请原谅,这整个想法都令人反感。上帝为什么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更多地保佑美国呢?这是对我们所有共同人性观念的侮辱。我们都需要我们能得到的一切帮助。我喜欢广阔的天空,广阔的空间,不受传统束缚的自由,这些都是美国人的特征。传统、扎根、倔强、固执、骄傲、眷恋家庭——所有这些南方人的品质——在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越来越成为我的一部分。 And yet I have been told I am very English. I suppose the self is a hybrid something.
另一方面,我喜欢伊萨的俳句,在罗伯特·哈斯的版本中:
这些海蛞蝓,
他们就是不像
日本。
有人告诉我,伊萨写这首诗是为了响应爱国诗歌的号召。巧合的是,据我所知,哈斯不懂日语——这与我上面所说的翻译相矛盾!一致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米兰:你最近的一些诗里有明显的政治评论,比如《什么是不允许的》。你是否觉得有义务在你的作品中融入社会和政治现实?这是诗人工作的一部分吗?
蒂:这是诗人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他或她认为是的话。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冲动,想写一些可以被称为政治的诗。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已经厌倦了充斥在美国电视广播中的那些毫无说服力的爱国主义论调。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塞缪尔·约翰逊的那句话:“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为什么我们这个毁灭了美洲原住民文明的国家,却要袖手旁观,任由以色列对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千多年的巴勒斯坦原住民做同样的事情,而许多声称对这片土地拥有犹太人权利的人,实际上是布鲁克林、乌克兰或其他地方的本地人,我却不明白。事实上,作为美国人,我们并没有无所事事——我们正在提供资金、坦克、导弹、喷气机来实施这一暴行,用推土机来拆毁祖先的房屋和橄榄树,这些树有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些问题在你引用的那首诗和最近的另一首诗《and and and》中都有所提及。
 米兰:在一个面试一首诗是如何发生的,你说灵感“是现实”。我靠它生活。”你一直都是这样吗?你是如何培养自己接受灵感的能力的?
米兰:在一个面试一首诗是如何发生的,你说灵感“是现实”。我靠它生活。”你一直都是这样吗?你是如何培养自己接受灵感的能力的?
蒂:我被问到的问题是,我相信灵感吗?我回答的重点是,如果一个人经历了某件事,那么就没有信或不信的问题。我希望任何从事某种艺术的人,无论是写诗、写歌、画画、写音乐等等,都知道我们生活在灵感的恩典中。灵感要么来,要么不来。话虽如此,一个人确实可以培养接受灵感的能力。对我来说,这包括手边有一个笔记本,记下每一个可能变成一首诗的小片段。诗就在那里——或者就在我们的内心——寻找着表达的机会。我还发现,培养写作的流畅性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可靠的方法。
米兰:在同一次采访中,您谈到叶芝是“活生生的存在”。你能说出其他一些对你有类似重要性的作家或艺术家的名字吗?并解释一下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影响你自己的?
蒂: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喜欢的艺术家的个人作品。Philip Larkin的《Church Going》。我喜欢这首诗完全实现的杰作,诗节就像巨大的切割石板,就像叶芝的《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一千多幅插图和一份完整的协约》、《加油站》、《在鱼屋》、《驼鹿》、《格雷戈里奥·巴尔德斯》和其他几篇散文。如此多精彩的细节,如此娴熟地总结了一生的经历。《希望是有羽毛的东西》(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的《我早早出发,带着我的狗》(I Started Early,带着我的狗),因为它们的古怪和措辞的正确。大部分的生活的研究罗伯特·洛厄尔,因为他能够捕捉一个时代的情绪,他的幽默,他的眼睛和色彩感。哈姆雷特,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因为书里的诗句无比诗意。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的《那些冬天的星期天》(Those Winter sunday)。《桦树》、《指令》、《雇工之死》、《泉水池》、《补墙》等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弗罗斯特是大师中的大师。什么保证,什么平衡,什么控制线。沃尔特·德拉马雷的《听众》(The Listeners)。一个令人难忘的诗。我喜欢鬼故事。约翰·契弗写的几个故事。一位伟大的散文诗人,有着令人心碎的悲情和时尚。这只熊和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这些书深入人心。《老森林》和我的朋友、孟菲斯人彼得·泰勒写的其他几本书。这些都是我随口写下来的,顺便说一句,我没有检查它们的准确性。战争与和平。的部分荒原。Bob Dylan的《Shelter from the Storm》和《Tangled Up in Blue》,因为他唤起了缪斯女神的灵感,用歌唱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他和我几乎是同龄的。
米兰:这些年你写了大量的批评。评论家的主要责任是什么?评论的陷阱是什么?
蒂:我不再评论任何我不喜欢的诗歌,但我也会在我感兴趣的领域评论非虚构和虚构作品。书评是年轻人的游戏。这太容易树敌了,我以前经常写新诗评的时候,当然就树敌了《纽约时报》。我确实认为书评是一项光荣的工作,我非常钦佩西里尔·康诺利、威廉·普里查德、兰德尔·贾雷尔等人。
米兰:你不仅是作家,还是音乐家。这两种追求是如何相互促进的?
蒂我每天都会弹吉他,唱几首歌,但我完全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希望我能弹得更好。我喜欢的歌曲。当诗歌不再是歌曲时,它们就失去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上面挑出来的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像歌曲。当诗歌中失去了音乐性,那么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就失去了。
Richard Tillinghast将于9月27日在孟菲斯大学进行读书会,随后在9月28日接受采访。他还将出席10月14日至16日在纳什维尔举行的南方图书节。
标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