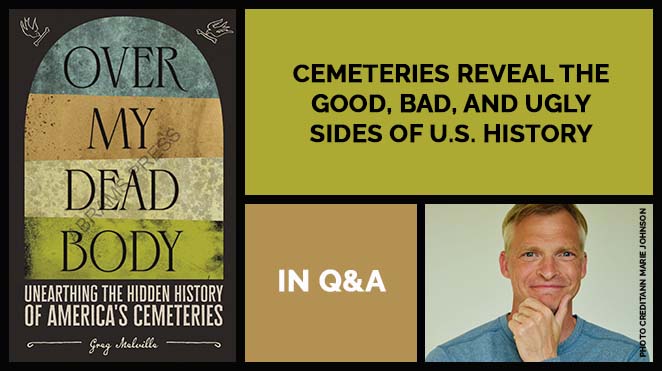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的一家餐馆里,我从桌子上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我刚吃完我的第一盘angulas幼鳗,正确的叫法是鳗鱼。它们是一种美味的巴斯克特色菜肴,一份重四分之一磅的两英寸长的小动物,看起来像透明的细面条,一端有两个黑点的眼睛。
用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大蒜和适量的辣椒面,在陶制的碗里快速煎炸guindilla胡椒,它们有淡淡的鱼和海洋的味道,在嘴里很快就融化了。在几个月的季节里,angulas出现在当地巴斯克餐厅的菜单上,每份约100美元。我是一名旅行作家,受餐厅老板/厨师的邀请,希望能得到一些好的媒体报道,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食物。已经喝了半瓶干白了txakoli好在,我需要放松一下。
浴室里干净得闪闪发光,灯光明亮,水池上方有一面宽大的镜子。我那中年的肚子先于我穿过它那反光的表面。我瘦了一辈子,现在也依然如此,除了这袋肉已经落在了我的腰带上。地心引力无情地施加着它的要求。如果我脱下衬衫,我会看到下垂的乳房盖着下垂的内脏,肌肉垂在二头肌下。肌肉开始松弛,岁月在折磨我,我的整个身体都向等待着我的大地倾斜。还是那个身体,但失去了锋芒。再等一会儿,就像那首古老的福音歌曲里唱的那样。
我母亲年近90,身体一直不太好。
我们惴惴不安地描绘着我们的长辈步入老年的过程。我们看着他们把日常生活抛在脑后,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仅仅是保持身体和灵魂在一起就需要很大的努力,去购物,做饭,站着。一个人年纪越大,坐得越容易,站起来就越难。老人不得不聚集起来,从椅子或沙发上跳起来。他们不得不立起遗嘱。重力也在拉着它们。首先,人们不能自己做饭,然后他们不能可靠地站起来,在一个不可阻挡的循环中回到同样的无助,我们开始了我们唯一一次的生命。
***

这家圣塞巴斯蒂安餐厅以西10英里处是奥里亚河的入海口,它在那里流入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每年一月,在黑暗无月的夜晚,这些体型矮小的鳗鱼(每只都比人的头发大不了多少)会进入奥里亚河和横跨欧洲的沿海淡水支流;它们的长城将在涨潮时冲入河流。他们在大西洋漂流了两年多才到达这些河流。它们从百慕大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之间的马尾藻海远道而来,在那里它们以细头动物的身份开始了它们的生活,这种微小的漂浮幼虫形状像小叶子,漂浮在大西洋中标记着百万平方英里马尾藻边界的强大水流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进入了奥里亚河,而另一些人则继续漂流,直到到达英格兰的塞文河,或者一路漂流到北爱尔兰的班恩河,或者穿越地中海到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东北部河流,或者找到通往北海的荷兰和德国支流的路。
无论幼虫选择在哪里产卵,它们都会第一次进入淡水,变成小鱼,失去叶子的形状,变瘦,变成带有眼睛的透明细丝。它们会随着涨潮离开海洋,大量进入河流。当潮水开始退潮时,它们聚集在低处,接近海底,抵抗着被拉回大海的力量。它们微小的身体进行了必要而复杂的细胞变化,从咸水中生存到淡水中,它们逆流而上,同样的力量驱使着它们走到这一步。
在某个时刻,它们会选择一些地方结束它们漫长的旅程,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里,它们会生活在这些地方几百码的范围内,长成一码长、粗如前臂的鳗鱼。它们白天在泥泞的河底挖洞生活,晚上在水中滑翔觅食。几十年后,它们将再次开始转变,向下游的开阔海域进发。当它们到达咸水中时,它们的消化系统就会停止工作,它们开始长达数月的游泳,没有食物,回到马尾藻海,在那里交配和死亡。这就是普通鳗鱼非凡的变形生活。它让我们自己的童年到老年生活在同一个身体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看起来灰暗、常规、乏味。
***
我们家在为一个表妹庆祝婚礼,我母亲在彩排晚宴上摔倒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几次把她从那种慢慢失去意识、瘫倒在地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那些昏厥已经够糟糕的了,转过身来,看到她的目光远远越过我,什么也没看到,心不在焉,看着她的身体蜷缩起来,下垂,或者在隔壁房间里,听到她撞在地板上的砰砰声。这一次,她从节日预演晚宴的餐桌上起身去洗手间(就像我做过的那样),却被一个足球绊倒了,那个足球是别人的孩子丢弃的,她那只正常的眼睛没有看到。她倒下去,撞在铺着厚厚的地毯的地板上,四肢伸开躺在那里。摔得突然而猛烈,她的手来不及放下来垫住。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骨折,只是吓了一跳。第二天,她带着黑眼圈和淤青脸颊去参加婚礼。
“懦夫不适合老年,”母亲总是这样向我保证。
***

随着angulas沿着奥里亚河缓缓而上anguleros正等待着他们,代表着全球丁香市场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的anguleros站在河岸上,孤独的身影被脚下地上的灯笼照亮,每个人都在一根长杆子上拿着一个又宽又浅的网。他们戴着黑色的雨具,包括黑色宽檐的平底橡胶帽,以保护他们免受无休止的雨水的侵害。这是又湿又冷的工作。这张网并不轻,在一月的晚上把它在河里泡来泡去并不容易,但它值很多钱。在那些夜晚,当小鱼们乘风破浪,anguleros两人站在相距10码的奥里亚河畔,雨具湿漉漉的,闪闪发光;它们像岸边的黑鹭一样稳稳地站着,等待着精灵们在它们非凡的上游之旅中经过,一心一意地寻找一个家。
这些捕获的鳗鱼将从这条漆黑的巴斯克河开始另一段漫长的旅程,这次是在飞机的货舱里,用干冰包装,飞越半个地球到达中国,在那里它们将被培育成成年鳗鱼,然后卖到日本。圈养鳗鱼从未成功培育过。日本人对鳗鱼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当地的鳗鱼种群,并将鳗鱼的价格推高到即使扣除空运到中国的费用,也能赚到钱。那些留在圣塞瓦斯蒂安为当地食客提供食物的小精灵只是这些进来的小精灵的一小部分。
***
妈妈,我正看着你呢,我对着男厕所的镜子说,这时我正从镜子前面走过,回到我的餐桌,去上下一道菜。
*saragoldsmith / Wikimedia Commons CC-by-2.0
标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