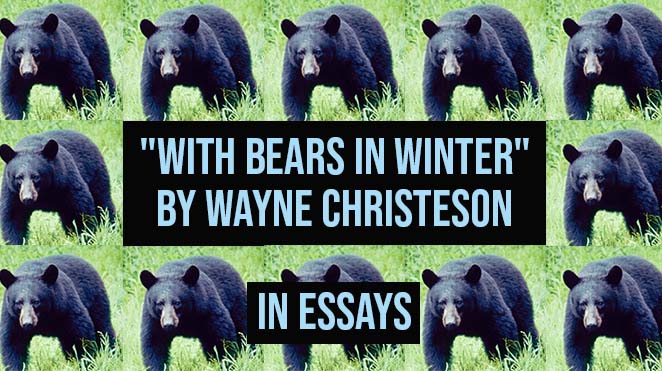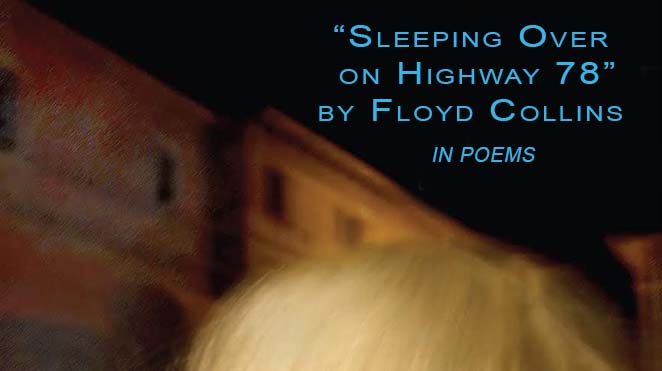纳什维尔人麦迪逊·斯马特·贝尔写了三本关于海地革命的著名小说,还写了一本杜桑·卢维杜尔的传记,但他与海地的联系远远超出了作家的知识兴趣。他在海地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解了海地人和他们独特的、深刻的精神文化。在去年1月的毁灭性地震之后,贝尔成为了海地的杰出倡导者,谴责帕特·罗伯逊在赫芬顿邮报并出现在主要新闻媒体上,解释海地不应该被冠以“西半球最贫穷国家”这个令人沮丧的标签的诸多原因。
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是海地的文化瑰宝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贝尔一直在帮助海地许多苦苦挣扎的画家为了响应地震造成的迫切需求,纳什维尔的LeQuire画廊从3月份开始出售这些画作,所得收入将捐给艺术家和海地运营的援助组织。贝尔是巴尔的摩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的英语教授,他将于4月15日在该画廊发表演讲,就海地的艺术和当前局势发表见解。他回答了来自米兰在他来访前给我发邮件。
米兰:在1995年第一次访问海地之前,你对海地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吗?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公益性服务油漆工代理?
 贝尔: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当我第一次去海地时,我对1791年到1804年这段时间了解很多,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1995年,在Cap Haïtien,我在Mont Joli酒店的酒吧里遇到了一位名叫Guidel Présumé的艺术家。我们一拍即合,他帮我做一些事情,去一些地方做我的研究(为海地的小说),如果没有他,我将很难做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他一直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但在那个时候,海地的旅游业真的开始枯竭,因为海地持续不稳定(或者至少是认为海地不稳定,根据我的经验,这经常是错误的)。
贝尔: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当我第一次去海地时,我对1791年到1804年这段时间了解很多,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1995年,在Cap Haïtien,我在Mont Joli酒店的酒吧里遇到了一位名叫Guidel Présumé的艺术家。我们一拍即合,他帮我做一些事情,去一些地方做我的研究(为海地的小说),如果没有他,我将很难做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他一直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但在那个时候,海地的旅游业真的开始枯竭,因为海地持续不稳定(或者至少是认为海地不稳定,根据我的经验,这经常是错误的)。
我开始试着在美国出售Présumé的画,帮他一点忙,渐渐地,我开始为他认识的其他艺术家做同样的事情,其中许多人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名为AJAPCA的合作社的成员。我开发了一个系统,我以他们带到海地的价格购买小幅画作,然后试图在美国转售(它们)。如果我成功了,我会在下次访问时把差价全部汇给艺术家。我善意地拿走了我所有的利润。
米兰地震后,你和那些艺术家有联系吗?
贝尔:是的。AJAPCA团队在2000年左右解散了,当时他们失去了在h角的工作室/画廊空间。所以,早在地震之前,我就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去了联系。一些人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那里有旅游业,还有一些人去了太子港。Cap Haïtien没有受到地震的(直接)影响。所以Présumé和其他留在那里的人都很好。有两位画家我还和他们保持着联系,Emalès Délis和阿尔芒·弗勒蒙德(Armand Fleurimond),地震发生时他们在首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音讯。我开始对他们不抱希望了,但最终他们都重新出现了。他们在首都的空地上和其他幸存者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Fleurimond和他的妻子和孩子最终回到了Cap [Haïtien]。在勒奎尔画廊的展览中有这两位画家的作品。
 米兰:在地震之前,参加LeQuire展览的艺术家们——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能够靠他们的工作谋生吗?
米兰:在地震之前,参加LeQuire展览的艺术家们——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能够靠他们的工作谋生吗?
贝尔:表示怀疑。我主要和Cap-Haïtien地区的艺术家打交道,虽然那里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旅游目的地,但不幸的是,旅游业还没有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动荡中恢复过来。所以,地面上没有足够的客户。太子港的画家可以做得更好,但那里也有更多的画家在为获得关注而挣扎。
米兰:许多画作都以伏都教为主题。艺术家们认为这些作品是精神上的表达,是神圣的灵感,还是他们对艺术的态度比这更超然?
贝尔:这取决于艺术家和特定的作品。例如,新教艺术家如果要画伏都教的场景,他们只会把它们画成当地的颜色。在这个作品中有很多的工艺意图;也就是说,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关于自我表达,而是关于制作一件有人会觉得有吸引力的物品。勒奎尔画廊展览的一个例外是阿尔芒·弗勒蒙德(Armand Fleurimond)的作品,它往往带有自传色彩。
我接触过的许多艺术家都有几种不同的绘画风格,就像在制作一种产品时的通用性一样,在我看来,同样的画家在绘画时,我们所说的“灵感”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可以从完成作品的质量上看出来。我认为这个过程可能类似于伏都教。一个灵魂出现了,把自我从画家的头脑中驱逐出来,用画家的手画了一幅或多幅画,在....上航行之后可能会有另一个灵魂出现。这和我们艺术中的自我表达有多大的不同?
 在某些情况下,同样是hungans或bokors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也可以作为pwen.一个pwen是一种被束缚在物体上的精神力量。他们可以为他们的主人做魔法工作等等。我学会了不买卖这种藏物。灵魂困在一个pwen基本上都是奴隶,所以这些东西会背叛它们的主人。
在某些情况下,同样是hungans或bokors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也可以作为pwen.一个pwen是一种被束缚在物体上的精神力量。他们可以为他们的主人做魔法工作等等。我学会了不买卖这种藏物。灵魂困在一个pwen基本上都是奴隶,所以这些东西会背叛它们的主人。
米兰:在华盛顿邮报》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你写道:“在海地社会的底层,在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工薪族中,潜意识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你能详细阐述一下这个观点吗,它是如何反映在海地艺术中?
贝尔:嗯,我们可以理解为Les Morts et Les Mystères,或Ginen Anba Dlo,或Sa Nou Pa we Yo,就像伏都昂人所说的,这三个短语都是指在海地死去的每个人的精神能量池。正是从那个蓄水池中,特定的个性化的灵魂或lwa出现。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心理化,说这些短语确定了类似于第一世界深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所投射的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在海地文化的情况下,集体无意识是外部的和共享的。正是这种分享让神奇的思维在海地比在其他大多数地方更有效。不管你叫它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就艺术灵感而言,在海地人当中,它更有可能来自外部和内部——一种经过然后继续前进的精神。
米兰:你在海地的遭遇对你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你曾写过你的灵附身经历和你练习伏都教的仪式。作为一个作家,它对你有什么改变?它是否让你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你的工作?
贝尔我一直觉得,就像很多作家一样,在我写的材料中,我更像是一个管道而不是创造者。安德鲁·利特尔是我的好朋友和明智的顾问,他这样说:“你把自己和自己分开,你进入了想象的世界。”这是对进入轻度恍惚状态的描述。我确信,每个从想象中制造神器的人都使用了某种恍惚体验来做到这一点,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海地文化中,这类事情是高度系统化的。自我脱离自我的转变有时被称为marassa(双胞胎)通常是完全附身的前奏。大多数第一世界的艺术家和作家并没有遵循它那么远。我们通常都太自负了,但大多数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工作的宣泄。
 米兰:您鼓励人们将捐款直接捐给海地基层组织,如Fonkoze和海地兰比基金会。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帮助方式?
米兰:您鼓励人们将捐款直接捐给海地基层组织,如Fonkoze和海地兰比基金会。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帮助方式?
贝尔这些组织是由海地人建立和经营的,他们在海地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他们也不受政治影响,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这在那里非常重要。它们在自身运营成本上花的钱相对较少(不像大型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因此捐助者可以感觉到,捐给这两个机构的钱会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两个组织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好事。但Fonkoze强调小额信贷和低成本资金转移和银行业务,而Lambi则强调可持续发展项目,主要是农业项目。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筹款工具“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也是一个不错的机构——在健康问题上是最好的。
米兰当前位置地震激发了全球帮助海地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在这场危机中提供即时援助。这显然是一件好事,但可能的危险是什么?海地文化中是否有可能受到外来利益和影响的威胁?
贝尔:虽然很多海地比中国还小,但它有一种奇怪的能力,可以吸收任何进入它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都能成为海地人。
尽管如此,全球化的力量和海地文化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自治和自给自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阿里斯蒂德开始着手使海地在农业上自给自足,这在当时是一个完全可能的项目,如果海地能够解决一些其他问题,这仍然是可能的。然而,全球化希望海地进口美国剩余的农业产品,并从组装工厂出口产品(支付西半球最低的工资)。这种利益冲突是国际社会勾结推翻阿里斯蒂德的动机。它不会消失。
此外,“我们”总是渴望把我们所谓的“民主”强加给海地这样的国家,这可能比他们得到的独裁要好。但最近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麦迪逊·斯马特·贝尔将于4月15日星期四在纳什维尔的LeQuire画廊发表演讲。活动时间为下午6-7点半,6点半开始评论。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