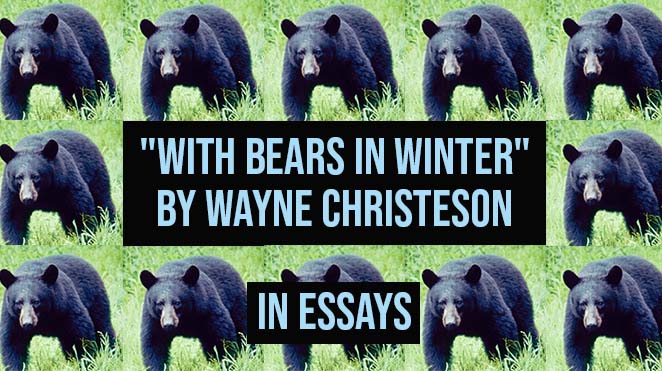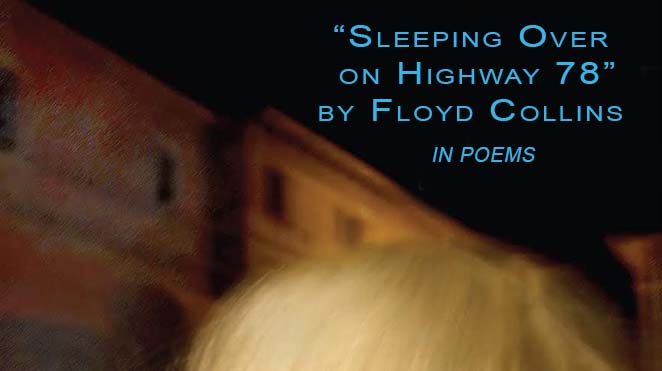在我快16岁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喜欢观鸟了。在我少年时期的自我陶醉中,我完全错过了这一人生变化的准备阶段。当我发现他们用双筒望远镜全神贯注地盯着树林时,我感到既震惊又尴尬。有一天,他们恢复了正常。第二天就没有了。
 在其他方面,我的父亲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领,戴软呢帽的标准。他是一名会计,在斯威夫特公司(Swift & Co.)的一间小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位于孟菲斯市航空和拉马尔公司普里纳饲料厂后面,靠近卡茨药店和霓虹灯猫牌。他的办公室有一排大型计算机,每一台都有一个两倍宽的文件柜那么大。因为电脑需要凉爽,他在空调房里工作。
在其他方面,我的父亲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领,戴软呢帽的标准。他是一名会计,在斯威夫特公司(Swift & Co.)的一间小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位于孟菲斯市航空和拉马尔公司普里纳饲料厂后面,靠近卡茨药店和霓虹灯猫牌。他的办公室有一排大型计算机,每一台都有一个两倍宽的文件柜那么大。因为电脑需要凉爽,他在空调房里工作。
在家里,他有一个旧的木制剪贴板,他开始在上面记录他第一次识别的每只鸟——观鸟者称之为“生命鸟”。他用自己精确的笔迹——全是大写字母,黑色墨水——把这只活鸟的名字填了进去,以便永远保存下来。伯丁满足了他记录和验证的需求,保持列表,在扎实的东西上工作,就像他按数字画的蓝松鸦肖像。这是他后来痴迷于邮票和硬币收藏、填字游戏(他可以用墨水做)以及基本上任何涉及他可以填上正确答案的空格的东西的自然前兆。
我父亲有一种温暖而稳定的嗡嗡声,从不改变。似乎在任何真正重要的层面上,都没有什么能触动或伤害他。他离得太远了。他几乎从不说话。他可能会在烟斗旁微微一笑,但他不说话,即使在家里也不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愿意和他在一起。他根本没注意到我。他不看我,不担心我,也没有可怕的想法。他就在那里,所以我就能在那里,和他在一起,以我自己的身份。
这让我们想到了我的母亲,弗吉尼亚,她是一名高中西班牙语老师,对她来说书籍就像毒品一样。她不断的批评有效地让父亲闭嘴了。她看着我,担心我,对我有可怕的想法。但当双筒望远镜出现时,观鸟把我母亲从她自己建造的笼子里带了出来,把她的鼻子从她的书里拿了出来。这减轻了她的无聊,满足了她的知识抱负,满足了她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需要。观鸟安抚了她不安的心和烦恼的头脑。
 这也迎合了她对自然的热爱。她曾经养过一只受伤的蓝松鸦,那只松鸦在羽翼尚未成熟时就从巢里掉了出来。我们给它起名叫“威士忌”,取自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中的一只松鸦。每隔几个小时,妈妈就用镊子喂它剁碎的鸡蛋和狗粮。他从鸟类的幼年期幸存下来,活了大约5年。虽然它残废得飞不起来,但它可以扑腾着飞到我母亲的肩膀和手指上。
这也迎合了她对自然的热爱。她曾经养过一只受伤的蓝松鸦,那只松鸦在羽翼尚未成熟时就从巢里掉了出来。我们给它起名叫“威士忌”,取自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中的一只松鸦。每隔几个小时,妈妈就用镊子喂它剁碎的鸡蛋和狗粮。他从鸟类的幼年期幸存下来,活了大约5年。虽然它残废得飞不起来,但它可以扑腾着飞到我母亲的肩膀和手指上。
无论何时何地,我的母亲都是一个复杂而不可靠的人。前一分钟,她还坐在我们家门前的台阶上,轻轻地把草蛉从她的手指递给我,让我感受它昆虫般的小脚的触感,或者教我如何从四点钟的花朵中取出种子。下一刻,她可能会痛苦地告诉我,她从来都不想要我,从来都不想要第二个孩子。这是旧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她经常这么说,有时还会说:“但你来了之后我就爱上你了。”有时又不是。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以为所有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都有着深深的矛盾情绪。16岁时,我开始意识到母亲在这方面是不同寻常的。
在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几乎没有注意过父母的私生活。他们就在那里,通常会阻止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比如和朋友一起过夜,或者和声名狼藉的男孩约会。但是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在我16岁那年的春天发生了交集,在那个春天,他们开始观察鸟类,而我手里拿着学习许可证,开始开车。
星期天早上,我们在市中心的圣玛丽大教堂度过。做完礼拜后,我们总是出去吃午饭,但那年春天,我们在星期天的例行活动中加入了另一项活动。我们沿着前街(Front Street)往前走,转到佛罗里达街(Florida Street),在麦克勒莫尔(McLemore)向西拐,然后驶上总统岛(President’s Island),这是密西西比河上一个灌木丛生的工业半岛,位于当时的普里麦克炼油厂(Premcor)的阴影之下。
我父亲会把车开下堤坝,停在一条砾石路上,然后我来开车。我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他坐到了后面。他们从窗户探出身子,用双筒望远镜夹在眼睛上,专注地凝视着细长的树木,树木上鸟儿像飞散的宝石一样活跃着——金色的、红色的、橙色的。我很高兴地踩下油门,我们在嘎吱作响的碎石路上以每小时五、六英里的速度缓慢前行,直到每走几英尺,我父母中的一方就会尖叫一声:“停车,停车。”
“停,停,我有东西。”
“我看到了。全是黄色,黑色的面具。”
我会等着,听着鸟类向导扑扇翅膀的声音。
“共同Yellowthroat。”
这本书会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
“是的,毫无疑问。真可爱!一个小强盗。”
我会瞥一眼那只鸟,不得不承认,是的,它们很漂亮,尤其是那个对我们大喊“女巫,女巫”的小强盗。
“好吧,继续。”
我会踩油门。
“等等!停,那是什么?”
“红尾鸲,看。”
“不,不,那里没有那种红色。它更黄。”
“那是雌的,看到了吗?”
“你确定吗?”哦,它走了。我不确定。”
“好吧,我把它列出来了。”
我父亲一直都是这样。我母亲其实不太在乎清单。我父亲想填补空白。我会翻白眼,然后踩下踏板。
“等等!等等!我还有别的东西!就在那棵开着白花的树的中间。”
“看不出来。”
“第二个大树枝,然后向左走。”
“明白了!”
 就这样。在1965年春天的总统岛迁徙中,我一周又一周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尖叫着“停!“再来一次,我就杀了他们。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再吹毛求疵,也没有注意到父亲开始说话了。
就这样。在1965年春天的总统岛迁徙中,我一周又一周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尖叫着“停!“再来一次,我就杀了他们。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再吹毛求疵,也没有注意到父亲开始说话了。
剪贴板上的清单越来越长。我父亲把它翻过来,从背面开始翻看。他忘了用同样的墨水。字体缩小了,字体也缩小了。春去夏来,河岸上石油和腐肉的气味越来越浓。蚊子太多了,无法忍受开着窗户在沼泽里缓慢移动。这些莺迁移到中西部北部和加拿大,养育它们的后代。我拿到了驾照,把父母抛在了后视镜里。
那年春天,我母亲45岁,父亲47岁。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还有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他们离自由如此之近,他们一定感觉到风在掀起他们的翅膀。
那年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去阿肯色州的哈迪参加了六个星期的夏令营。我父母飞到西班牙去住了一个月。我母亲在马德里大学上过一门课,她让父亲在晚餐时喝葡萄酒。我哥哥和我们的牧羊犬呆在家里,开车穿过三角洲,为斯威夫特的农业和化学部门向棉农出售农药。当他晚上回来时,他开的那辆旧福特车已经蒙上了厚厚的黄色灰尘。
第二年,1966年,我母亲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并进行了第一次乳房根治术。那年春天她病得太厉害了,不能去鸟。那年夏天,父亲被调到了芝加哥。我在外星世界度过了大四,躲在我们联排别墅的地下室里听鲍勃·迪伦(Bob Dylan)和西蒙与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我没有结交一个朋友,没有一次约会,尽管有一天在生物课上,当我用我那滴滴答答的孟菲斯口音问我的实验伙伴,我的显微镜镜头是否“准备撞上”载玻片时,我无意中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我母亲教八年级,她那些魔鬼般的学生完全不像那些狡猾、表面上很乖的南方孩子。她的同事们公开咒骂她,说脏话,我母亲认为这是对她的人身攻击。我父亲往返于芝加哥西北火车站和联合油罐车大厦的路上,每次都要花一个小时,忍受了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冬天,从芝加哥西北火车站到联合油罐车大楼,他穿过迷宫般的暖气大厅,鼻涕冻在胡子上。于是又一年过去了,双筒望远镜都没有被举起来。相反,我大声地给他们读了三卷书指环王.
1967年秋天,我上了大学。我哥哥开车把我从Prospect山送到埃文斯顿,把我和我那破旧的旅行箱放在西北大学的Willard Hall。
我很多年都没有再想过鸟。

莉达菲利普斯他是一位在孟菲斯长大的资深记者,曾在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学位。作为两本青少年小说的作者,她在返回纳什维尔之前曾为合众国际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