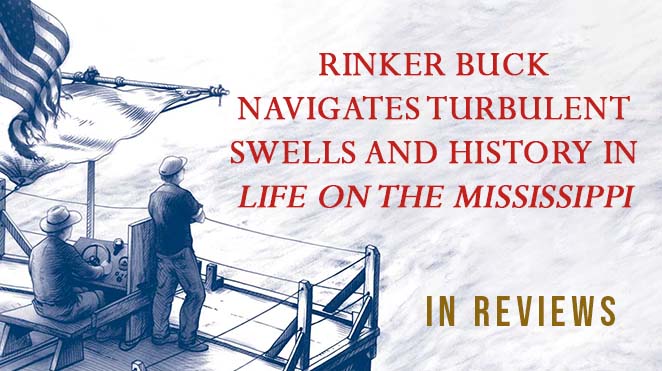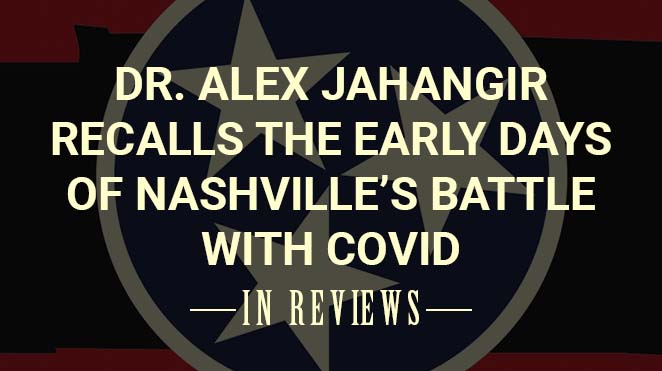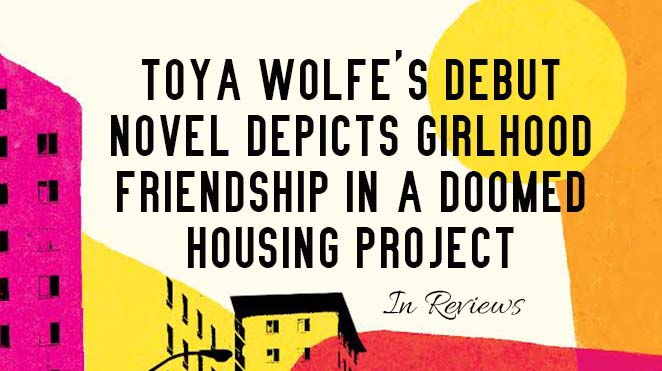我和威尔默·米尔斯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夏天,当时我们都是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的大学生诗人,被选中参加一个暑期研讨班。作为室友,我们立即开始分享我们的诗歌,然后很快就开始争论诗歌。我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20年来,我们一直在相互挑战,以扩展我们对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和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想法。我们玩得多开心啊!我们带着热情和好奇,带着傲慢和谦逊,带着困惑和确信去做。威尔的诗和弗罗斯特、狄金森、巴索、辛波斯卡、斯塔福德或其他我很亲近的作家的诗一样,都是我生活的中心。
 5月14日,威尔打电话告诉我他得了癌症的消息。我在西田纳西州参加完婚礼回家的路上,他让我找个地方停在路边。我并不担心:威尔有某种名声,有人可能会说,他对科技的态度与我们的文化不一致,他讨厌任何人在开车时打电话。(几个月前,他在查塔努加的圣约学院(Covenant College)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当时他是那里的常驻作家;要听对话,请点击在这里)。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休息站,打电话回去,只听到他说“小细胞癌”和“在我剩下的时间里。”我刚跟威尔和他的家人待了几天,就在一个半月后,这个可怕的消息改变了我们的声音。当我挂断电话时,我无法和我妻子通话。我只是坐在那里哭泣。
5月14日,威尔打电话告诉我他得了癌症的消息。我在西田纳西州参加完婚礼回家的路上,他让我找个地方停在路边。我并不担心:威尔有某种名声,有人可能会说,他对科技的态度与我们的文化不一致,他讨厌任何人在开车时打电话。(几个月前,他在查塔努加的圣约学院(Covenant College)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当时他是那里的常驻作家;要听对话,请点击在这里)。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休息站,打电话回去,只听到他说“小细胞癌”和“在我剩下的时间里。”我刚跟威尔和他的家人待了几天,就在一个半月后,这个可怕的消息改变了我们的声音。当我挂断电话时,我无法和我妻子通话。我只是坐在那里哭泣。
对于任何坚持到底的人他CaringBridge网站-威尔与肝癌的斗争,很明显,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这里展示了威尔在面对毁灭性的诊断时,对语言、爱、家庭和信仰的力量的非凡见证。威尔自己的更新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分享的信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超出了他的圈子,进入了完全陌生的人的生活,他们被这个家庭不可否认的力量所吸引。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不会徒然而归。威尔把自己的写作生涯建立在《圣经》上,每天以阅读和祈祷开始,并在上帝话语的光芒中创作自己的诗歌。这就是他的过程。CaringBridge上的评论让我觉得威尔的话也不会是空洞的,而是会深入世界,深刻影响读者的生活。
大约两个月前,威尔给我发了一篇关于时间和口语力量的短文。他考虑把这张照片贴在CaringBridge上,他问我是否认为这张照片在这个网站上“不合适”。当我阅读威尔的草稿(后来修改并发表在米兰,在这里),我感到既谦卑又惊讶:
时间不是一种冰冷的终结,而是一种充实,是一个让人驻足和深呼吸的地方,不受日历和最后期限的影响。这是我们最具人性和最神圣的地方。太多时候,我们只为时钟而活,却没有注意到,如果没有增加的时间,我们会更讽刺地看到地毯上的图案,我们生活中的彩色玻璃窗是如何作为整体而不是碎片而有意义的。
威尔和我这样的谈话已经有20年了,就像钓鱼、体育或政治话题对其他人来说一样,是我们友谊的一部分。这些话,虽然顺序正确,但似乎是威尔多年来一直想说的话的惊人升华。“请把它寄出去,”我回信说。“你的话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安慰,就像对我一样。”鉴于“关爱之桥”上的留言,我相信它们不仅帮助其他人理解了如何面对他的死亡,还帮助他们了解了如何崇拜我们被赋予的神奇生命,如何探索我们为什么被赋予这个世界,为什么被赋予彼此的生命的奥秘。
 威尔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带着一份崇拜的礼物。在无数经过Sewanee的作家中,他以好客、独创性和个性著称。威尔很有主见,安于现状,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反映了一个艺术家的情感。他是一个创造者,在这个世界上构想并建立了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他在Sewanee的房子是一个奇迹,每一个细节——从嵌在通向楼上的墙上的钢琴弦,到楼梯下嵌有书架和顶灯的壁炉——都是他在自己的时间感中构思出来的。他所建立的空间——无论是房屋的房间,诗歌的房间,还是交谈的房间——都成了我一直敬畏的想象存在的空间。
威尔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带着一份崇拜的礼物。在无数经过Sewanee的作家中,他以好客、独创性和个性著称。威尔很有主见,安于现状,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反映了一个艺术家的情感。他是一个创造者,在这个世界上构想并建立了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他在Sewanee的房子是一个奇迹,每一个细节——从嵌在通向楼上的墙上的钢琴弦,到楼梯下嵌有书架和顶灯的壁炉——都是他在自己的时间感中构思出来的。他所建立的空间——无论是房屋的房间,诗歌的房间,还是交谈的房间——都成了我一直敬畏的想象存在的空间。
威尔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消息几周后,我承认自己对他的绝症诊断也有困难:
我可以在路上开车,突然间我的情绪失控了。我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好像我已经在哭泣,或者已经睡着了。就像你说的,活在时间里有自由——真的有自由——活在时间里,活在这一切的意义之中,其中一部分是了解时间的流逝以及我们在时间里所处的位置。悲伤是深深的,但赞美是我们生来的目的,我带着我所有的一切踏上赞美之路。我把你举到上帝面前说:“谢谢你!”我不敢相信我们曾经有过交集,但我们在这里,在这段时间里,分享它,就像我们过去二十年一样。这个事实只能是上帝恩典奥秘的另一部分。
十多年前,当我妻子发现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斯托里时,威尔是我第一个告诉她的人。第二年,我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当时他和凯瑟琳正在生本杰明。当威尔和我的作品被文学杂志接受时(《新共和》,南方的审查,哈德逊审查,测量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这个好消息。电话铃响了,我立刻认出了他的声音,就像他认出了我的声音一样。我们交换了诗歌和批评,在整个成年生活中互相鼓励,都是彼此和彼此作品的忠实粉丝。
 几年前,在7月4日的一个周末,威尔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去塞瓦尼,帮他在一个他专门为此建造的户外烤箱里整夜烤面包。他想做一百个左右的面包,星期六上午在农贸市场上卖,然后在南方大学的一个活动上卖——我想是返乡吧。我们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我们磨小麦,混合和揉面团,把它揉成面包和法棍,然后把托盘拿到烤箱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威尔喜欢教我如何做这些事情,他一直在解释小麦、酵母和在如今快节奏的世界中早已被遗忘的古老工艺的详细历史。有时我以为他只是在胡编乱造,但这一切听起来太有趣了,所以我没有挑战他。
几年前,在7月4日的一个周末,威尔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去塞瓦尼,帮他在一个他专门为此建造的户外烤箱里整夜烤面包。他想做一百个左右的面包,星期六上午在农贸市场上卖,然后在南方大学的一个活动上卖——我想是返乡吧。我们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我们磨小麦,混合和揉面团,把它揉成面包和法棍,然后把托盘拿到烤箱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威尔喜欢教我如何做这些事情,他一直在解释小麦、酵母和在如今快节奏的世界中早已被遗忘的古老工艺的详细历史。有时我以为他只是在胡编乱造,但这一切听起来太有趣了,所以我没有挑战他。
我们一边烤着面包,一边享受着闲暇时光,我们坐在高耸的橡树下,在夜晚凉爽的空气中聊天。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是一种神圣的感觉,我无法解释,就像进入了一个宁静的时空。多年来,我和威尔分享了很多这样的时光:我们两个人,安静的空气,上帝在倾听。
威尔经常会拿出他的吉他,任何听过他唱歌的人都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多么亲切,他的眼睛是多么深沉和锐利。或者,就像那天晚上发生的那样,当面包从烤箱里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像孩子一样“啊”和“啊”地叫了起来,面包的厚皮冒着热气,那么香,我们站了一会儿,吸了一口。威尔切了一块面包给我们“品尝”,半夜里我们就像吃吗哪一样吃了起来。当威尔喜欢什么东西时——比如无花果的味道,或者一首引起共鸣的、丰富的诗句——他会因为明显的喜悦而全身颤抖。我喜欢想象,在月光下,我们脸上的笑容可以被经过的卫星看到,有人在某个控制室里想,田纳西州山上的那两个成年人究竟为什么这么高兴。
有一天我在威尔的家里,当时他的女儿Phoebe-Agnès正在帮助他做一项砌砖工程。当时她只有三四岁,穿着靴子,手里拿着一把泥铲。“布兹,”威尔叫她。在用手推车搅拌好灰泥后,威尔拍了一层薄薄的灰泥,牢牢地固定住了一块砖。Phoebe-Agnès用她的泥铲刮掉了多余的灰泥。至少可以这么说,每块砖都要花点时间。他们是效率低下的写照,而且很漂亮。受时钟的限制,成年人通常只想尽快完成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们很少被带进学习和分担责任。我一直很钦佩威尔,因为对于他来说,“时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存在。 What is time, if not this space we share together? What is time, if not our own creativity finding a space to flourish? Time is holy, and Wil existed in it without hurry, and I hope his daughter carries this memory, too, and a thousand just like it.
多年来,威尔不断修改一本他命名为的书到达时间.这就是他伟大的主题——时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写,
 进入圆满时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彼此大声说出我们的话语,通常是带着爱和希望。口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坚持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就像一封信一样,它把说话者的精神以正确的速度实时地带入房间,也就是呼吸的速度。它有人们一起吃饭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说,凯罗斯时间和口语是同一科伊诺尼亚的两个方面。
进入圆满时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彼此大声说出我们的话语,通常是带着爱和希望。口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坚持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就像一封信一样,它把说话者的精神以正确的速度实时地带入房间,也就是呼吸的速度。它有人们一起吃饭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说,凯罗斯时间和口语是同一科伊诺尼亚的两个方面。
多年前的一天,威尔打电话给我,只是想和我谈谈时间和圣经翻译的问题。首先,他说,像“上帝的话临到摩西”这样的诗句的翻译并没有真正提供完整的含义。更准确地说,这节经文应该是,“还有神的道发生在摩西。”他喜欢这个观点,上帝的话语在自我之外,然后冲进来发生一个人。
其次,他说,在希伯来语中,时间的概念和我们对时间的概念不一样。我们对它最接近的理解可能是“一个适当的空间”。他说,既然上帝控制着时间,既然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设计和旨意,那么时间只是上帝打算发生的事情的完成。这个想法使他大为兴奋。在我们有限的视野中,威尔自己的寿命似乎是悲惨的短暂,但他会说,上帝需要通过他完成的任何事情都是“合适的”。和任何人一样,他想活得长久,但他也相信要服从上帝对自己人生的旨意。
威尔的思绪从建筑到木工,从高果糖玉米糖浆到麦草,再到使徒保罗,全都在同一段对话中。我永远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他的机智经常让我猝不及防。知道我对烹饪节目主持人尼格拉·劳森(Nigella Lawson)有好感后,他高兴地写了一首关于她的诗,只是为了取笑我,激起我的反应。当这首诗发表了诗歌杂志我担心他会写一系列关于我其他迷恋对象的诗,当然,第一个是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
3月下旬,威尔给我做了介绍,当时我在圣约学院读书。我记得当他从笔记(但主要是发自内心)说起我和我的诗时,他脸上的喜悦。令我惊讶和尴尬的是,他说他自己的作品在两大影响柱之间来回移动:理查德·威尔伯和我。当他说到我的名字时,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发红,他不得不控制住自己,强忍住泪水。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喜欢的事情。我没有意识到他会在他的介绍中使用其中的一些想法,但当他这么做时,我成了那个不得不隐藏自己情绪的人。威尔说:“杰夫·哈丁喜欢春天,喜欢春暖花开,喜欢大地复苏。杰夫·哈丁爱着他的妻子,她是他高中时代的恋人,二人于近20年前结婚。杰夫·哈丁喜欢诗歌。杰夫·哈丁喜欢读书。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盒盒的。杰夫·哈丁很可能会拿着圣约学院付给他的所有钱,一大早就去麦凯书店把钱都花在书上。”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喜欢的事情。我没有意识到他会在他的介绍中使用其中的一些想法,但当他这么做时,我成了那个不得不隐藏自己情绪的人。威尔说:“杰夫·哈丁喜欢春天,喜欢春暖花开,喜欢大地复苏。杰夫·哈丁爱着他的妻子,她是他高中时代的恋人,二人于近20年前结婚。杰夫·哈丁喜欢诗歌。杰夫·哈丁喜欢读书。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盒盒的。杰夫·哈丁很可能会拿着圣约学院付给他的所有钱,一大早就去麦凯书店把钱都花在书上。”
我多么喜欢最后这句话!被人这样了解是我最喜欢我们友谊的原因之一。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观众哄堂大笑,我装出困惑的样子,但随后,在那些目光投向我的面孔下,我勉强点头表示同意。我们都是陌生人,一起分享这个亲密的空间。正如诗所要求的那样。就像威尔的最后几个月一样,把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彼此都是陌生人,但威尔不认识。彼此也不再是陌生人了。
“杰夫·哈丁喜欢威尔·米尔斯。”我真希望那天晚上我站起来读诗的时候想到要说这些话。当然,我要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一群人面前说出那些出乎意料的话仍然是正确的,即使只是让我们双方都感到尴尬,并在真理和友谊的喜悦中开怀大笑。
我上次去西瓦尼看望威尔是在六月底——不到一周后,他就住进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扎卡里的父母家的临终关怀病房。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天。他很累,昏昏欲睡,但我们设法复习了他的几首诗。他称之为“Facebook”十四行诗。其中一些我已经认识了,但还有一些我还没见过。我对在线修改和句法重排提出了建议,然后对每首十四行诗的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序。他喜欢我对他的逻辑安排,喜欢我以一首特别的十四行诗开头,为接下来的十四行诗定下基调。
几年前,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首名为《高空作业的自白》的诗,这首诗后来出现在他的作品集里,孤儿之光.在这首诗的最下面有一句神奇的诗句:“建造古老教堂的人都死了。”当他大声朗读那句台词时,我起了鸡皮疙瘩。我告诉他,他必须把这句话作为诗的开头。当然,他会和我争论——这是威尔的天性。他固执、暴躁、固执到了极点。他声称我不理解他在诗中想表达的意思。我告诉他,他太自以为是了,第一次看到这句诗的读者会更深刻地领会到诗的核心。这种改变需要大量的修改,大量的辛勤工作——整首诗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创作。“也许你还没准备好。”我揶揄他。 Then I told him that I’d beat the living crap out of him if he didn’t take my advice. He was taller, had a longer reach, but I warned him that I was scrappy. We both laughed. Sometime later, he rewrote the poem, starting with that magical line. It’s one of the gems in that collection, but then all of them are gems. Or “keepers,” as Wil would say.
今年早些时候,在我们得知威尔的病情之前,我给他发了一封鼓励我们写作的电子邮件。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必须帮助彼此重建破碎的自我。虽然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尚未出版的书,虽然缺乏认可似乎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但我想在我们之间树立一个我从未真正能够完全形成的想法: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读者,唯一重要的读者。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能遵循腓立比书4:8所说的一种方式:“弟兄们,最后,凡真实的,诚实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佳美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赞美,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
其他的一切——认可,我在舞台上的位置,下一本书的出版——都很好,但最终,思考“这些事情”真的是令人震惊的快乐之源。这可能就足够了。好吧,这就够了。
 威尔热情地回信说:“阿门!”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这种快乐越来越深。自私地说,我真希望他能多写四十年的诗。也许他会把他常写的《箴言》和《哀歌》移到他自己的《诗篇》中去。但我不想太自私。我想对他写的那些话感到敬畏。和他一样,很久以前,他们从未存在过。现在它们确实存在了,以一种以前不存在的、令人费解的丰满程度出现了。
威尔热情地回信说:“阿门!”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这种快乐越来越深。自私地说,我真希望他能多写四十年的诗。也许他会把他常写的《箴言》和《哀歌》移到他自己的《诗篇》中去。但我不想太自私。我想对他写的那些话感到敬畏。和他一样,很久以前,他们从未存在过。现在它们确实存在了,以一种以前不存在的、令人费解的丰满程度出现了。
在我们最后一次拜访的那个下午,威尔想让我带他去兜兜风。他本希望我们能坐在斯特林咖啡馆的门廊上聊诗,但他身体不太舒服。相反,我们开车去了可以俯瞰考恩镇的巨大十字架。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离我们坐在我车里的地方有一段路。看到她们,我们谈论着与妻子相爱的感觉是多么美妙。由于化疗并没有缩小他的肿瘤,我们也讨论了临终关怀的可能性。当他接到诊断时,他以为自己可能还能活一年,但他开始接受这个事实,认为自己活的时间要短得多。他试图让我为未来的日子做好准备,而这些日子的到来比我们两人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谈到了他美丽而非凡的孩子,本杰明和Phoebe-Agnès,以及他的妻子凯瑟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如何照顾他的。他不愿意丢下他们。 That reality worried him more than anything.
当我们把车倒出停车位时,我望着窗外,盯着那个高耸的十字架看了一会儿,十字架周围围着一个小栅栏。我说:“看来我们应该祈祷。”会同意。我们把车后退,走到一张长椅前。威尔总是迈着这么大的步子,走起路来像子弹一样快,但现在我必须意识到要放慢脚步。我们坐下来,我祈祷,祈求上帝与威尔同在,让他完全知道他的存在。当我做完的时候,我没想到威尔也会祈祷。
我不得不问你一个问题:你曾被一个垂死的人祈祷过吗?你可曾听过有人在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时,请求上帝帮助你接受他的天意?当我想到那种无私,那种谦卑时,我仍然感到震惊。威尔的话,就像我们所有人说过的话,就像我们被赋予的生命一样,永远不能不说出来。威尔对我们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将我们放在彼此的生活中,一起分享这段文字的旅程。他求神将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发扬光大,以成就他的旨意。我希望我能再听到那句祷告因为它是从威尔内心最深处最充满爱的地方发出来的。它就像一首美丽的诗,世界永远不会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上帝分享。它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空气中,存在于我们共享的亲密空间中。
Jeff Hardin版权所有(c) 2011。保留所有权利。杰夫·哈丁是田纳西州萨凡纳人,是哥伦比亚州立社区学院的英语教授。哈丁毕业于奥斯汀皮伊州立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在那里他获得了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学位。浅滩深处(GreenTower出版社)慢山的消失(布丁屋),以及一本书的合集,秋天避难所他是尼古拉斯·罗伊里奇奖的获得者。
标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