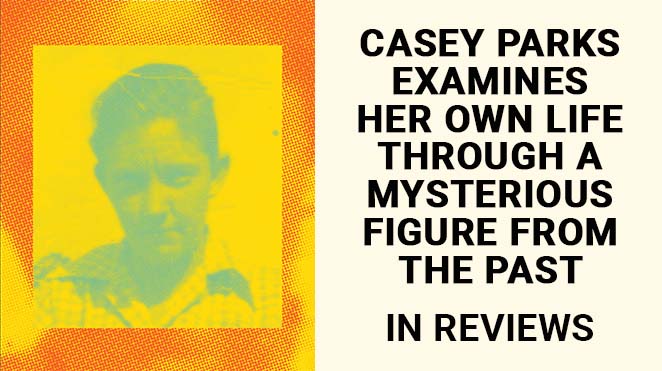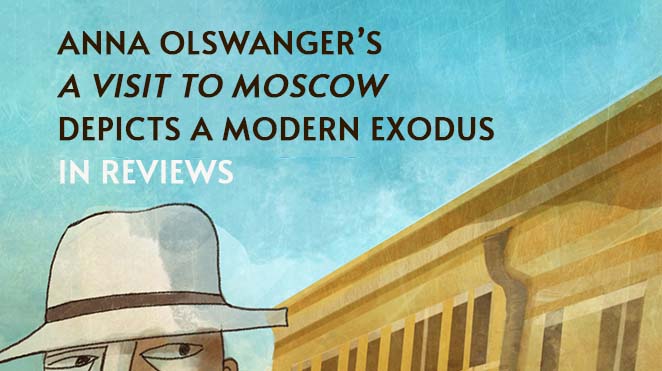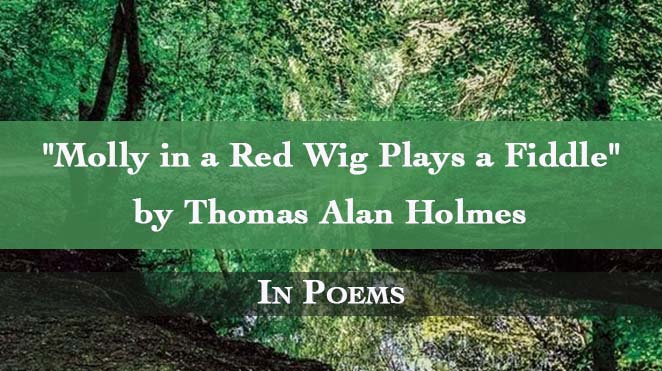埃莉诺•罗斯•泰勒是一位诗人,也是彼得•泰勒的遗孀。我对她的生活和工作的钦佩是长期存在的,而且不受我随随而就想到的任何界限的限制。
我应该指出,我不认为自己是文学评论家。更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充满激情、勤奋好学、不落俗气的认真读者,以及我所深切关注的书籍——尤其是诗歌书籍——的倡导者。但即使是在当代诗歌这个互相推敲的世界里,我也并不比泰勒夫人本人更害怕坦率。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她就要求犹他大学出版社立即停止发行过去的日子/回来的日子并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因为最初的封面上有一组墓碑:“我不能发送这对我的朋友们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寡妇。”(这本书的签名本至今仍是我最珍贵的财产之一,不过泰勒夫人——我没办法。这就是她在西瓦尼作家大会上被介绍给我的方式,我总是这样称呼她——她拿出笔时皱着眉头。)
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泰勒夫人口头上的无畏,在纸上和在人身上,而且也说明了她在其他诗人中激发的忠诚和钦佩。戴夫·史密斯当时是犹他诗歌系列的编辑,尽管他没有参与选择不得体的封面艺术过去的日子/回来的日子,这充分说明了史密斯和泰勒夫人对彼此的相互尊重,他继续印刷她的下一个系列——晚休闲(1999)俘虏的声音艾伦·布赖恩特·福伊特(Ellen Bryant voigt)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方信使系列》一书中,以一种只能用一种不祥的清晰来形容的方式精彩地介绍了《南方信使》。
 “欢迎你,尤梅尼德斯”——这是泰勒夫人第二本书的标题诗所发出的如此不怯懦的邀请吗?Eumenid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据推测是被雅典娜和洛的力量驯服的。泰勒夫人欢迎“复仇女神”,驯服的和未驯服的,进入她的生活,就像她欢迎那些在塞瓦尼作家大会早期扩大她每年聚会的访客一样。她对“复仇”并不感到害怕,就像对那些在她家里狼吞虎咽地吃裹着毯子的猪一样。她和彼得把夏天的恒温器调到八十度以上,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炎热的环境中感觉最自在,他们年轻时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她通常穿着新熨好的短袖衬衫裙,当她优雅地穿过汗流浃背、愚昧无知的人群时,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她额头上有一滴汗——不像我,我是适应了空调的那一代人——那些人对她的诗歌成就一无所知,只因为来到彼得·泰勒的家里而激动不已。
“欢迎你,尤梅尼德斯”——这是泰勒夫人第二本书的标题诗所发出的如此不怯懦的邀请吗?Eumenid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据推测是被雅典娜和洛的力量驯服的。泰勒夫人欢迎“复仇女神”,驯服的和未驯服的,进入她的生活,就像她欢迎那些在塞瓦尼作家大会早期扩大她每年聚会的访客一样。她对“复仇”并不感到害怕,就像对那些在她家里狼吞虎咽地吃裹着毯子的猪一样。她和彼得把夏天的恒温器调到八十度以上,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炎热的环境中感觉最自在,他们年轻时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她通常穿着新熨好的短袖衬衫裙,当她优雅地穿过汗流浃背、愚昧无知的人群时,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她额头上有一滴汗——不像我,我是适应了空调的那一代人——那些人对她的诗歌成就一无所知,只因为来到彼得·泰勒的家里而激动不已。
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泰勒夫人的活动仅限于招待有抱负、胃口大开的作家。在比较安静的时候,她和彼得(彼得坚持要叫他的名字,我也不知怎么做到了)大声地给对方读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信件,泰勒夫人开始写诗,这些诗最终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晚休闲.她告诉我,她还读了大量的“附属材料”——南方历史、信件和传记,尤其是与女性有关的书籍。(“阅读的兴致!阅读的兴致!”我能听到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对有抱负的诗人的训诫,这句话泰勒夫人在他的学生时代肯定听过一遍又一遍。)她的这句话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几乎二十年后,当我继续写一份手稿时,这颗种子将努力开花结果。这份手稿包含了我自己的家族史,还有密西西比州蓝调歌手罗伯特·约翰逊的故事。
泰勒夫人的直系亲属由四位作家组成,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她的妹妹简(唐纳德·贾斯蒂斯的遗孀)继续发表短篇小说,她的侄女希瑟·罗斯·米勒(Heather Ross Miller)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她写了一篇关于她姑姑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灯塔看守人:埃莉诺·罗斯·泰勒诗歌随笔(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2001年)。这本诗集由独一无二的简·瓦伦丁(Jean Valentine)编辑,对她来说,这肯定是一种最需要付出爱的劳动,其中还有贝蒂·阿德考克(另一位从未得到应得回报的优秀南方女诗人)、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埃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詹姆斯·朗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以及艾伦·布莱恩特·福伊特(Ellen Bryant Voigt)的精彩作品,她在许多方面都是泰勒夫人自己的文学继承人。
在我们定期见面和通信的那些年里,泰勒夫人在谈话和通信中都很尖刻。她形容一位著名编辑是彻头彻尾的“虐待狂”,尤其是对年轻作家。事实上,她说她怀疑他向有前途的年轻作家索要作品,仅仅是为了创作他认为特别诙谐的退稿信的乐趣。她甚至用同样清晰的眼光看待她显然爱的人。在她的经典作品中,有几首关于贾雷尔的可爱的、令人心酸的诗歌,但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是在我给她寄了一盘贾雷尔大声朗读的磁带之后,磁带把他的阅读风格描述为“腼腆、半谦逊、过度情绪化”。她担心,至少在这一次,“他发现自己的智慧不可抗拒”。
 泰勒夫人的作品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短语是“我的套装”,它来自更早的一首诗——是的,是尖刻的——《彩桥》(The Painted Bridge)。我们的信件中有一段令人捧腹的轶事——至少对我来说,对我那一头乱发的头发来说是这样的——她试图取消与小说家约翰·凯西(John Casey)的午餐约会,因为她本周早些时候去了一家“美容院”,但未能如愿。她家的热水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她回家想自己梳头发。她说,她看上去如此可怕,以致于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我听过的最站不住脚的借口,”凯西回答说。
泰勒夫人的作品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短语是“我的套装”,它来自更早的一首诗——是的,是尖刻的——《彩桥》(The Painted Bridge)。我们的信件中有一段令人捧腹的轶事——至少对我来说,对我那一头乱发的头发来说是这样的——她试图取消与小说家约翰·凯西(John Casey)的午餐约会,因为她本周早些时候去了一家“美容院”,但未能如愿。她家的热水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她回家想自己梳头发。她说,她看上去如此可怕,以致于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我听过的最站不住脚的借口,”凯西回答说。
然而,在诗意的语境中,“我的发型”显然不只是指她的理发师。她说的是她的人生定位,她的丈夫比她名气大得多,她是他的终身伴侣,是南方女性强加给她的生活定位——她所属于的定位,不一定是她自己选择的。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她指的是她限制自己的那个集合。下面有请贾雷尔的介绍荒野的女士们解释这句话:“世界是女人的牢笼,里面的女人就是她自己的牢笼。”
在某种程度上,泰勒夫人为她的作品选择的生动、独特,有时甚至是愤怒的标题可以概括她的全部作品。但是,就像被里奇称为“家里的维苏威火山”(Vesuvius at Home)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一样,泰勒夫人的愤怒被她的歌词天赋所超越。任何人都可以对被强加的限制感到愤怒——哦,亲爱的上帝,让我们摆脱那些“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词语吧,但现在,它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生活给我们的手,但泰勒夫人从来没有抱怨过要更好的手,也没有回过头去看她可能已经发过的牌。在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中,她给了我人生中最好的忠告,也许也是我的工作中最好的忠告:“不快乐要花很多时间”。
我怀疑埃莉诺·罗斯·泰勒在任何事情上都浪费了很多时间,尤其是在自怜自怜上。所有的诗人都希望留下第一流的作品,尽管在她的生活中被荒谬地忽视和不为人知,但它们将持续下去。在这一点上,泰勒夫人没有任何自怜的理由。
[本文首次发表于2009年12月17日。]
标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