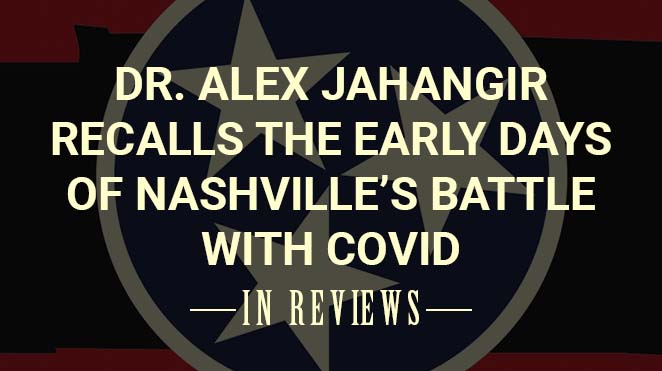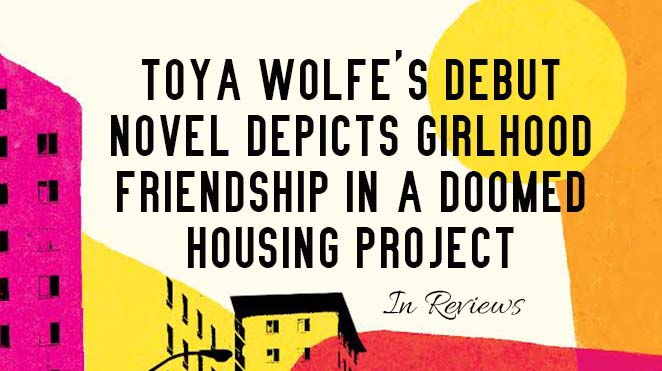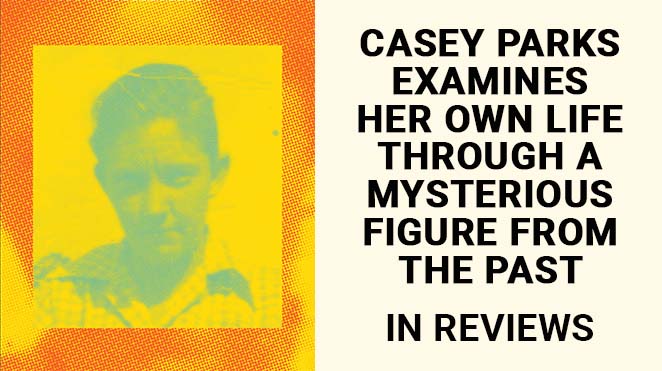17世纪晚期的巴黎冲击了感官,也扰乱了神经。尖叫声和喊叫声在狭窄街道的墙壁外回荡,巴黎人大声抱怨城市生活的侮辱:愤怒的邻居之间拳打脚踢,钱包从受害者手中跑出,便壶从楼上扔到楼下的路人身上。车夫们为了争夺这条街的指挥权而互相辱骂。成群的小贩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动物的声音穿插在刺耳的声音中:狗叫,公鸡叫,奶牛在铃铛叮当作响的时候哞哞叫着。
 巴黎的污物附着在衣服上、建筑物的侧面和鼻孔里。每周都会有几次,肉贩、制革工人和牛脂生产商将成群的牛羊送到市中心的屠宰场,这些屠宰场位于像牛脚街(rue Pied-de-Boeuf)和牛脚店街(rue de la Triperie)这样的街道附近。在周四和周五,巴黎人别无选择,只能在数英寸的凝固血液中跋涉。即使是在没有屠杀的日子里,街道上也永远是锈迹斑斑的,因为鲜血浸透了泥土。
巴黎的污物附着在衣服上、建筑物的侧面和鼻孔里。每周都会有几次,肉贩、制革工人和牛脂生产商将成群的牛羊送到市中心的屠宰场,这些屠宰场位于像牛脚街(rue Pied-de-Boeuf)和牛脚店街(rue de la Triperie)这样的街道附近。在周四和周五,巴黎人别无选择,只能在数英寸的凝固血液中跋涉。即使是在没有屠杀的日子里,街道上也永远是锈迹斑斑的,因为鲜血浸透了泥土。
巴黎没有人行道。没有一个欧洲城市拥有它们。许多房主在他们家的石头建筑上安装了一根突出的铁棒,高到脚踝,这样游客就可以在进入之前刮掉鞋子上的污垢。为了完全避免在街上行走,那些有能力租用马车的人越来越多地这样做。在17世纪中期,只有不到300辆马车在街上穿行。在短短几十年里,这个数字膨胀到一万多,造成狭窄街道上的交通堵塞,每次长达数小时,更糟糕的是,严重的安全隐患。正如一位意大利旅行者所写的那样,“有无数肮脏的马车,上面覆盖着泥土,它们可以杀死活人。”
拥挤不堪、肮脏不堪的巴黎,甚至把头脑最冷静的居民也逼到了暴力的边缘。冲突的裁决往往依靠武器的供应——从铜指节和棍棒到匕首和短剑——这些武器都近在咫尺。当街头“正义”得到伸张时,它来得很快,而且往往令受害者大为震惊。在离国王图书馆几步远的黎塞留街,一个钟表匠遇到了以前的顾客。那人没有礼貌地打招呼,而是开始尖刻地抱怨他一年前买的手表有缺陷。当钟表匠抗议时,他的顾客用一把沉重的剑刺向钟表匠的头,把他刺死了。
 手枪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使一个已经危险的城市变得更加致命。炮是16世纪硝石发现的产物,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早期欧洲的战争。到了17世纪40年代,法国人已经完善了燧发枪射击技术,使得枪支比传统的轮锁式枪支和步枪更轻、更小、生产成本更低。小偷们在斗篷下藏着袖珍手枪,胆子更大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巴黎人竞相购买手枪,这使得这个城市更加不安全。
手枪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使一个已经危险的城市变得更加致命。炮是16世纪硝石发现的产物,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早期欧洲的战争。到了17世纪40年代,法国人已经完善了燧发枪射击技术,使得枪支比传统的轮锁式枪支和步枪更轻、更小、生产成本更低。小偷们在斗篷下藏着袖珍手枪,胆子更大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巴黎人竞相购买手枪,这使得这个城市更加不安全。
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暴力,1660年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禁止所有武器,包括——尤其是——手枪,除了士兵、警察、法官和贵族。这项法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六年后颁布的另一项法令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660年的法律。它还补充说,所有的手枪都必须显眼、笨重,枪管至少要有15英寸长。任何拥有这种武器的人都被要求在夜间穿过街道时携带灯笼或火把,这样法律官员和公民都能看到此人携带武器。从夜幕降临后充斥整个城市的暴力事件来看,也很少有人遵守这一命令。
到了晚上,巴黎变得幽闭得可怕。日落时分,士兵们关闭了这座城市壁垒的巨大大门,放下了身后的路障。但这些大门几乎没有保护那些被锁在一起的人。夜间狂欢的人穿过漆黑的城市,只有微弱的烛光透过窗帘或百叶窗照亮一小段街道。房主和店主用木条封住了他们的房子和商店,晚上关好门窗,就像水手准备迎接暴风雨一样。这时,武器派上了用场。就像一位苏夸林女士在杀死一名闯入者后若无其事地对警察说的那样,她总是在床边放一把刀,就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尽管危险重重,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仍在向我们招手。一些人注意到了这座城市酒馆的警报声。大多数街道都至少有两到三家名气各异的酒馆。他们给自己起了许多色彩鲜艳的名字,比如“摇篮”、“狮子沟”或“肥葡萄”——他们吸引了附近渴望吃喝或打架的当地人。
直到17世纪晚期,巴黎才有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警察部队。相反,这座城市的治安责任只掌握在48个专员手中——每15000个巴黎人中还不到一个专员。理论上,每个专员都能维持他所居住区域的秩序,但是专员们很快就意识到打击犯罪并不能获得回报。真正值得付出的是犯罪后所需的大量官僚和法律工作。在漫长且往往昂贵的寻找正义的过程中,拜访一个专员的家(他的办公室)是第一站。专员仔细观察每一个进门的人,看他们是否有支付能力。一位名叫Nicolas de Vendosme的专员,在一个当地工人代表他的两个儿子来投诉时,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两个儿子在一个木雕工手下当学徒。激动的父亲说,木雕匠把他的两个儿子推到泥泞的街道上,并用木槌打其中一个。父亲解释说,木雕匠没有弄断儿子的腿,真是太幸运了。
Vendosme解释说,对木雕匠的一个简单投诉就会让他的父亲支付15英镑溶胶相当于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三。因此,木雕匠将收到正式通知,他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这位父亲希望在法庭上追究此事,将需要额外的费用。一开始,纸不是免费的。它的价格远远超过1美元索尔每一页,他们需要大量的纸张来处理信件和法庭文件。证人也希望他们的证词得到补偿。还有一些书记员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要求支付报酬。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专员自己的酬金之外的,酬金将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而定。总之,这位父亲将面临至少三项指控里弗,相当于工人整整三天的工资,以起诉木雕工。尽管如此,这与七个国家相比还是合理的里弗皇家纺织厂的厂长支付的费用,或者十英镑里弗一位公爵夫人支付了类似的服务。在17世纪的司法审判中,人们认为一个人付得起的钱越多,他通常就付得越多。
塞纳河左岸坐落着城堡般的Châtelet大院,里面有法庭,也有一所监狱,被判有罪的囚犯在审判后在那里受刑。Châtelet被划分为两个官僚领地。一个是文官中尉德奥布雷的统治,他是Châtelet的总负责人。他裁决个人和团体之间对城市公共利益有影响的纠纷。另一个是刑事副队长雅克·塔迪约(Jacques Tardieu),他管辖巴黎发生的大多数犯罪。和委员们一样,这些副手(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到原告的报酬。确定一个案件的管辖权——尤其是那些涉及富人的备受关注的案件——引发了激烈的内斗。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Châtelet的法律体系陷于停顿,因为地方法官们为了争取某些案件的听审权而斗争,往往要持续数月之久。
巴黎医学院(Paris Faculty of Medicine)的医生盖伊·帕廷(Guy Patin)写道:“他们在这里不分昼夜地杀人,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渣渣。”事情似乎不能再糟了,在1665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里,这座城市达到了沸腾的顶点,犯罪的中尉本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
René和François塔切特花了数周的时间监视犯罪副队长雅克·塔迪厄的家,记录左岸家庭的出入。塔迪厄的家是奢华的典型代表酒店particuliers(城市房产),只有最富有的巴黎人才能买得起。一道高大壮观的墙将塔迪厄家族与周围街道的污浊和喧嚣隔离开。两扇20英尺高的木门通向一个大院子,为外面的暴力世界提供了另一个缓冲。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塔契特兄弟越来越相信高墙后面藏着大量的财富。72岁的塔迪厄定期去巴黎圣母院做弥撒,那里离他在Orfèvres码头的家只有一小段马车路程。René和François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埋伏着,直到院落的大木门打开,释放出几辆马车和一群步行的仆人。兄弟俩以为房子是空的,就爬上墙,从一扇开着的窗户进去,开始在房子里翻箱倒柜,寻找珠宝、金钱和其他贵重物品。
他们没有意识到年老的塔迪厄那天选择呆在家里。一想到要和人们一起庆祝圣巴塞洛缪节,我就觉得筋疲力尽。相反,他和他的妻子把家里的其他成员都打发走了,他们宁愿自己呆在家里。
一声可怕的尖叫刺穿了塔迪厄宁静的早晨。这是隔壁房间里他妻子的哭声。他在衰老的身体允许的范围内尽快从床上爬起来,拖着脚沿着长长的走廊去找她。片刻之后,塔迪约听到一系列令人作呕的声音:手枪扣动扳机,一颗子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是一声闷响。当他终于到达妻子的房间时,他看到她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鲜血在她的尸体周围凝结。
塔迪厄以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符的力量,向盗贼扑去,与塔契特兄弟争夺枪。其中一个兄弟扔下武器,飞快地一脚踢过房间。塔迪厄蹲下身子去拿剑时,老二把手伸到腰带下,取出了一把匕首。脖子上挨了四下,塔迪约瘫倒在地。
当这对夫妇从教堂回来时,仆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震惊之下,他们尖叫着跑到街上。当地的卫兵来了,在搜查了房子之后,他们发现两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正蹲在屋顶上。年长的躲藏在地窖里,浑身是血,最终投降了。
这对兄弟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在距离塔迪约法庭不远的地方,有一场公众表演,罪犯被处决,巴黎人挤在广场上观看。
塔迪厄的谋杀案震惊了这座城市的贵族。如果连负责对暴力罪犯判刑的刑事中尉在巴黎都不安全,那么谁会安全呢?第二年,答案来了,塔迪约的对手,陆军中尉François德鲁克斯·德奥布雷也被谋杀了。这一次,死亡不是由枪或匕首,而是由毒药。
 摘自光之城,毒之城:谋杀,魔法和巴黎的第一任警察局长冬青塔克。版权所有©2017由Holly Tucker。获出版人诺顿公司许可。保留所有权利。冬青塔克是《血液工作:科学革命中的医学与谋杀的故事,这是一个洛杉矶时报书奖决赛。她住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
摘自光之城,毒之城:谋杀,魔法和巴黎的第一任警察局长冬青塔克。版权所有©2017由Holly Tucker。获出版人诺顿公司许可。保留所有权利。冬青塔克是《血液工作:科学革命中的医学与谋杀的故事,这是一个洛杉矶时报书奖决赛。她住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