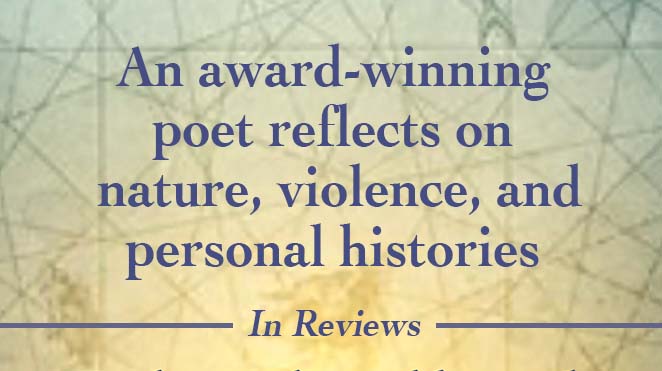在从圣华金英语教授Barry Kitterman Peay奥斯汀州立大学从事,创造了美国短篇小说的一个很好例子周期,这种联系收集舍伍德安德森在他的杰作,俄亥俄州》。在从圣华金,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寻求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的家,工作,恋爱,结婚,child-face打败困难的情况下的结果和自己的不足。与俄亥俄州》单独的故事可以被理解,但读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web的意义比个人更强和更复杂的部分。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Kitterman的故事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关系到加州的圣华金河谷。令人惊讶的是,它并不是那么遥远的精神安德森的中西部设置,通过退休人员的眼睛Cy富兰克林集合中的第一个故事,“兔子”的人:“他搬到圣华金战争结束后,离开旧金山寻找像他记得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姑姑和叔叔和老化的祖父母口音遗留下来的世界留下了自己的父母。“Cy赞赏什么镇的艾芬豪是其明确的关系自己的过去:“他在这里遇到的人当他第一次开车Studebaker进城,加油站的人feedstore,只是一代从农场和商店的中西部和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他发现安慰。在战争期间,加州的人他除了说好像整个地方被巨杉长沙滩阴影,一棵树那么大你可以开你的车。但艾芬豪Cy的加州,是熟悉的他长大的八十英亩在爱荷华州。”
 熟悉,也许,但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生存的地方。Cy能够在新奇士orange-packing工厂工作28年,但他的朋友和邻居难以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从一个非技术漂流,低薪的工作。设置大概在20世纪跨越几代,这个集合提供了一个加州的柔和的颜色,险恶地浓雾,和无处不在的空气消散和失望。Kitterman很简单,明确的叙事风格部队人物故事的重任,他熟练的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理由的读者在日常语言中经常悲伤和孤独的人,轻微和阴暗的人物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故事。
熟悉,也许,但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生存的地方。Cy能够在新奇士orange-packing工厂工作28年,但他的朋友和邻居难以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从一个非技术漂流,低薪的工作。设置大概在20世纪跨越几代,这个集合提供了一个加州的柔和的颜色,险恶地浓雾,和无处不在的空气消散和失望。Kitterman很简单,明确的叙事风格部队人物故事的重任,他熟练的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理由的读者在日常语言中经常悲伤和孤独的人,轻微和阴暗的人物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故事。
奇怪的是引人注目的“疯子”,一个漫无目的的,生气的人似乎比他应该更多的了解当地的谋杀。“木头的河流”描述了毫无意义的欺负新员工的木材厂和突如其来的暴力结束。神秘的“窗口”,前教授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形状的窗口污点大学体育馆,他去游泳。在这些故事中,过去的痛苦事件打扰人物的生活改变的过程,并很少。这是从来没有更引人注目的“婚礼”,当一个击败,平凡的牧师竟然发现勇气毁掉一个年轻夫妇的幸福或者拯救他们从一生的绝望,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哪一个。
一些声音在收集过程中出现多次,最明显的是约翰尼·福斯特,十几岁时我们见面在“男孩来自贫困家庭,”一个心碎家庭悲剧的故事。约翰尼最终离开了圣华金寻找更多机会在蒙大拿。在扣人心弦的“工会工资”,他的工作作为一个铁匠雇来修建栅栏当地邮局把他与工人发生冲突的一个小镇上:“我想那天早上。可能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不认为。我看到了雪桩远离他们的汽车和卡车。我看到一个男人把他的香烟和另一个人在街上吐痰。他们走向我们,马克斯,谁站在前面的吉米,仍然用导线和配件。马克斯的脖子太薄,李维斯也缩水了一英寸高。Sid开门的卡车。他一只胳膊休息,那个上面的名字,以及后面的座位。 And the ma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rest of them, the man I know now has never been a sheriff’s deputy but would have made a good one, comes a little nearer. ‘You can’t win,’ he says.”
 这句话代表的主题从圣华金,如果不是偶尔的一丝光线,救赎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抓住。没有很多的英雄,但是在“像我这样的人,”年轻的保利哈伯德标识与尼克如此强烈,他的姐姐珊瑚安的男朋友,很快去战争,他的眼睛总是在他身上,寻找线索提示自己的行动,甚至在当地教会复兴会议:“当(传教士)真正的软珊瑚安来弹钢琴,每个人都应该闭上他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心。我抬起头,瞥了传教士,他盯着尼克,尼克是直直地看着,而不是假装祈祷。今晚我们唱的邀请,“为什么不?“我看到卡罗尔·安看尼克和微笑,但尼克不会看她。他不是看牧师了。他只是盯着这幅画的洗礼像他知道有鱼。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得到拯救。”
这句话代表的主题从圣华金,如果不是偶尔的一丝光线,救赎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抓住。没有很多的英雄,但是在“像我这样的人,”年轻的保利哈伯德标识与尼克如此强烈,他的姐姐珊瑚安的男朋友,很快去战争,他的眼睛总是在他身上,寻找线索提示自己的行动,甚至在当地教会复兴会议:“当(传教士)真正的软珊瑚安来弹钢琴,每个人都应该闭上他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心。我抬起头,瞥了传教士,他盯着尼克,尼克是直直地看着,而不是假装祈祷。今晚我们唱的邀请,“为什么不?“我看到卡罗尔·安看尼克和微笑,但尼克不会看她。他不是看牧师了。他只是盯着这幅画的洗礼像他知道有鱼。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得到拯救。”
最有希望的注意是在最后的故事收集由约翰尼·福斯特(第三个叙述),“如果我知道你要呆这么长时间。“经过多年贫瘠和不幸,约翰终于回到艾芬豪和他父母的房子,他年老体衰的父亲是肺癌。约翰尼花时间与他的父亲,他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打我。我很像我的父亲,我不能让我们直了。他坐在在躺椅上和其他我会坐在躺椅上。但是突然当我起床泄漏或去绝望在冰箱里,我不能确定,如果是我穿过房间这次还是他。我把这些前三个步骤弯腰与悲伤,我停顿在窗前,仰望天空,我清楚我的喉咙好像我要说话,但是我不喜欢。这些动作我父亲只要我记得。”
他父亲希望约翰尼帮他修剪一个巨大长满树在后院。约翰尼爬起来,从一个旧的条幅平台他停顿的愉快的气味橙果园和山脉的观点。当他有了一个想法:“我帮助他爬它一步一步,然后稳定梯子所以他可以大步最低的分支。什么时候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的树,我有片刻的清醒,知道我们在搞什么鬼。但他给了我一个鬼脸,膝盖到树屋。我推他努力他几乎超过对方。一旦我起床他旁边,他的内容让我做实际的修剪。足以让他的。。我们看看地平线和呼吸和汗液。我尽量不去想我要让他回来在地上。” It’s what they do together up in the tree that provides the closest thing to a moment of grace in Barry Kitterman’s从圣华金。它表明,生活不可能是几年的成就和更多关于每个小的时刻真正的意义住。
巴里Kitterman将出现在2011年南部节日的书,10月14 - 16在纳什维尔举行。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