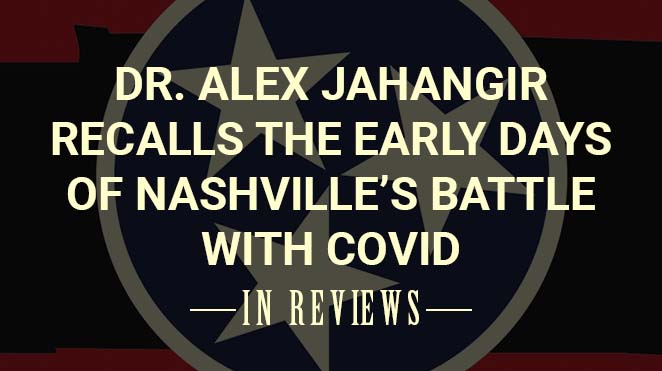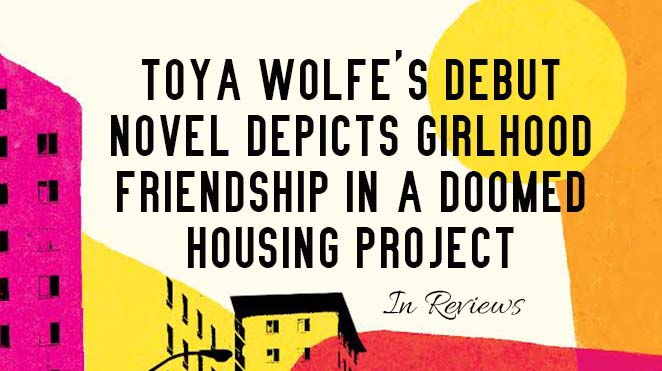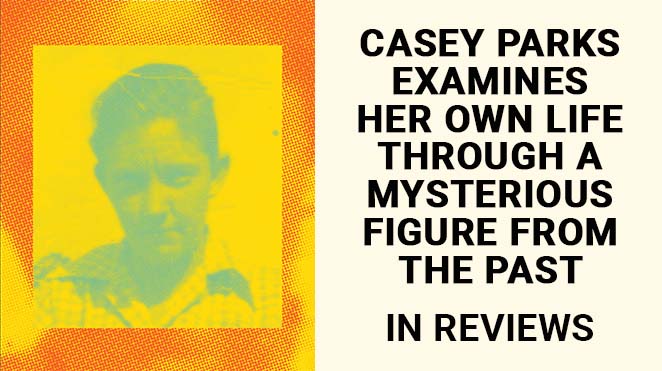阿巴拉契亚诗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詹姆斯仍他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在田纳西州接受教育——就读于林肯纪念大学和范德比尔大学——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肯塔基州东部的山区度过的。大萧条时期找工作的困难把他吸引到了肯塔基州的诺特县,但正是这个地方的野性之美留住了他。当他开始了解这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极度独立的居民时,他开始写他们的生活。在山上还记得位于约翰逊市的东田纳西州立大学阿巴拉契亚研究教授特德·奥尔森(Ted Olson)将斯蒂尔的短篇作品完整收集在一起。它们跨越了四十多年,代表了斯蒂尔的诗歌和小说之间的联系。正如奥尔森所解释的,“他的短篇小说扩展了他诗歌的长处,最终鼓励了他的想象力去探索扩展的叙事小说形式。”
根据奥尔森的说法,“斯蒂尔将他的愿景和价值观提炼为极简主义景观。事实上,对许多读者来说,他的短篇小说似乎更接近于口头传统的流露,而不是传统的、自觉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来自阿巴拉契亚灵魂的简单故事和传说,引人入胜,永不过时。”然而,斯蒂尔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区性的作家1992年的采访中他说,“我不是在写阿巴拉契亚的故事。我只是在写一些我知道或想说的东西。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而,他确实被阿巴拉契亚的人民迷住了。在詹姆斯·斯蒂尔:麻烦溪上的人他说,“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与这里人民生活基本相关的主题,我认为那就是克服任何困难、任何悲伤、任何条件的意志。我看到他们这么做了,我很钦佩。”
 在山上还记得悲伤来得又厚又快。在标题故事中,老奥斯·汉利,“上帝绿色大地上最卑鄙的人”,可能已经倒下了——字面意思是躺在河堤上,是致命枪伤的受害者——但他绝不是倒下了,因为他的攻击者在奥斯死的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遗憾地发现。在《他们的路都是黑暗的》(All Their Ways Are Dark)中,一位保护欲强烈的母亲宁可烧毁自己的房子,也不愿让丈夫那些忘恩负义、吃白食的亲戚多陪伴一天。《迷失的兄弟》讲述了一个善意的小提琴手的故事,他为自己的儿子意外中弹而感到内疚,收养了一个被斯蒂尔描述为“所有恶魔在折磨中滚成一个球”的年轻人,可预见的可怕后果。
在山上还记得悲伤来得又厚又快。在标题故事中,老奥斯·汉利,“上帝绿色大地上最卑鄙的人”,可能已经倒下了——字面意思是躺在河堤上,是致命枪伤的受害者——但他绝不是倒下了,因为他的攻击者在奥斯死的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遗憾地发现。在《他们的路都是黑暗的》(All Their Ways Are Dark)中,一位保护欲强烈的母亲宁可烧毁自己的房子,也不愿让丈夫那些忘恩负义、吃白食的亲戚多陪伴一天。《迷失的兄弟》讲述了一个善意的小提琴手的故事,他为自己的儿子意外中弹而感到内疚,收养了一个被斯蒂尔描述为“所有恶魔在折磨中滚成一个球”的年轻人,可预见的可怕后果。
斯蒂尔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在《十二梨高悬》中,孩子们贪婪地享受着父亲在煤矿找到新工作后突然出现在厨房桌子上的奖赏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桶五磅重的猪油,桶上画着一个猪油孔。红糖装在玻璃瓶里。一个正方形的小肚腩,瘦而多毛。一袋灰蒙蒙的面粉,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抱着一大堆麦秆。还有一铁盒黑胡椒和两把咖啡豆。我们惊讶地看着,说不出话来,只知道一种巨大的饥饿爬上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舌头湿润了我们的嘴唇。”
 在这些故事中,最年幼的孩子尤其脆弱。在《蛋树》中,一个婴儿的葬礼被推迟到收割完毕后才举行,这是一个大家庭聚会的场合。孩子的哥哥描述了这一幕令人心酸的场景:“邻居们安静地走过来,向妈妈打招呼,女人们手里拿着手帕,哭着。然后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房子里有人死了。所有进去的人都低声说话,他们的声音比声音更多。大钟停了下来,它的指针指向婴儿死亡的钟点和分点;走过房间的人都知道那张床,因为它铺着白色的床罩,上面放着一束秋天的玫瑰。”
在这些故事中,最年幼的孩子尤其脆弱。在《蛋树》中,一个婴儿的葬礼被推迟到收割完毕后才举行,这是一个大家庭聚会的场合。孩子的哥哥描述了这一幕令人心酸的场景:“邻居们安静地走过来,向妈妈打招呼,女人们手里拿着手帕,哭着。然后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房子里有人死了。所有进去的人都低声说话,他们的声音比声音更多。大钟停了下来,它的指针指向婴儿死亡的钟点和分点;走过房间的人都知道那张床,因为它铺着白色的床罩,上面放着一束秋天的玫瑰。”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关键是努力工作和大量的运气。《Still》描述了煤矿、伐木、农业、锯木、甚至清洁井等危险而不可靠的工作所带来的机遇和失望。在《吃干草的人》(The Hay受苦者)中,一个瘦削的小个子男人下到一口井的深处,“井底的泥一直到他的膝盖”,他继续用手从井底舀出泥和粘土到一个桶里。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只有在井底他才不会过敏。斯蒂尔写道:“当最后一层泥土被清除后,清洁工人用手拉着绳子剥去了蜜藤,他用手指当纺锤,在上面缠起了蜘蛛的网。”最后,他在底部撒上食盐,然后宣布:“那些坚果居然没有让你生病,真是个奇迹。”
“Gom”(混乱)是斯蒂尔邻居们常用词汇的一个例子,奥尔森称斯蒂尔的故事充满了“阿巴拉契亚语的杰出文学近似值”。Olson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数据库链接,其中包含了数百个阿巴拉契亚词汇的定义,比如“rusty”(恶作剧)、“witty”(机智的人)和“sang”(人参根)。
 尽管困难重重,或者正因为困难重重,斯蒂尔的角色们充分利用了快乐时光,有种植高粱的社区集会,屠宰猪,牲口棚舞蹈和婚礼。幽默通常是一个人物以牺牲另一个人物为代价而享受的,丰富多彩的隐喻和明喻在故事中自由地散布,以达到滑稽的效果。在《刮刮》中,人物爬上的地面“陡峭得几乎会刮到鼻子”,他们的头“像圆球头锤一样硬”。在《鸽子窝溪》中,迷人的ella afronia Saul“温柔得像蜗牛的角”,牙齿“白得像瓢虫种子,甚至像玉米粒上的玉米粒”。在《学校黄油》(School Butter)中,满屋子的孩子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他们“像苔藓吃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在《木板镇》(Plank Town)中,一个孩子“被宠坏了,盐救不了他”。
尽管困难重重,或者正因为困难重重,斯蒂尔的角色们充分利用了快乐时光,有种植高粱的社区集会,屠宰猪,牲口棚舞蹈和婚礼。幽默通常是一个人物以牺牲另一个人物为代价而享受的,丰富多彩的隐喻和明喻在故事中自由地散布,以达到滑稽的效果。在《刮刮》中,人物爬上的地面“陡峭得几乎会刮到鼻子”,他们的头“像圆球头锤一样硬”。在《鸽子窝溪》中,迷人的ella afronia Saul“温柔得像蜗牛的角”,牙齿“白得像瓢虫种子,甚至像玉米粒上的玉米粒”。在《学校黄油》(School Butter)中,满屋子的孩子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他们“像苔藓吃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在《木板镇》(Plank Town)中,一个孩子“被宠坏了,盐救不了他”。
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风景就像书中人物一样丰富多彩。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犁地》(The Ploughing),年轻的叙述者在一个四月的清晨到田野里寻找他的乔利叔叔。他写道:“天空像瓶子一样蓝。一大片绿色覆盖着有遮蔽的栅栏边缘,尽管山毛榉和皮革木因为阳光冲刷着它们的树枝,变得更加棕色和裸露。我开始爬,双手放在膝盖上,路很陡。我穿过荆棘丛,来到乔利叔叔犁地的地方,荆棘丛里还长着尚未开放的花朵和叶子。长凳向后伸展到一块洼地上,平坦得像小溪的土地,面对着天空和空气,什么都没有。”后来,乔利叔叔决定让他热心的侄子试一试,这段经历就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地球分开了;它从铲犁上掉了下来;那份股份闹得沸沸扬扬。 I walked the fresh furrow, and balls of dirt welled between my toes. There was a smell of old mosses, of bruised sassafras roots, of ground new-turned. . . . The share rustled like drifted leaves. It spoke up through the handles. I felt the earth flowing, steady as time.”
最好的作家能够巧妙地将文字编排在一页纸上,从而在作者的声音和读者的心灵之间直接打开一条通道。詹姆斯·斯蒂尔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对阿巴拉契亚生活看似简单的描绘,充满了强大的真理和雄辩的美。与山上还记得在美国,他的声音将一如热天里一盆凉凉的山水,在人们心中回荡。
阅读米兰的审查楝树,詹姆斯·斯蒂尔死后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点击在这里.要阅读特德·奥尔森自己最近诗集中的一首诗歌样本,启示,点击在这里.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