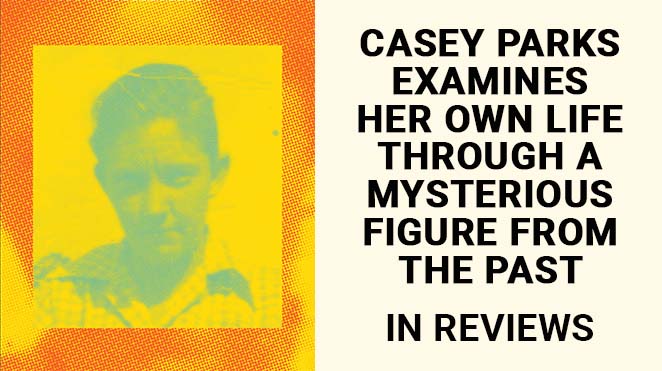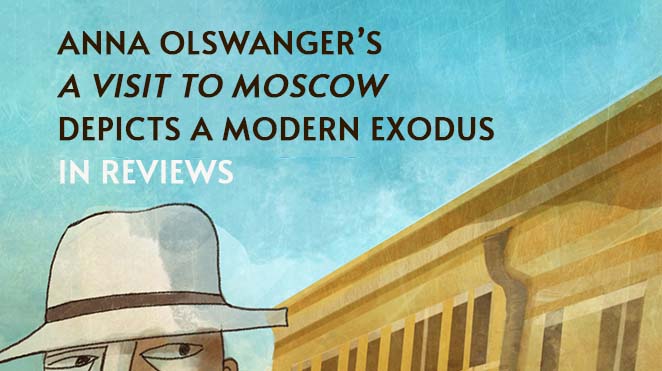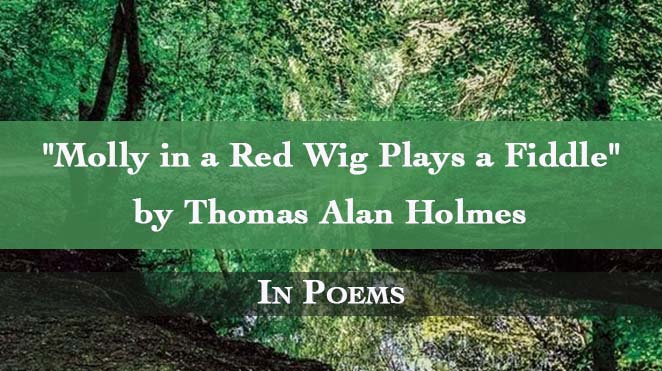克里斯托弗·赫伯特的第一部小说,沸腾的季节,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加勒比国家,非常像海地。这部美国作家的处女作似乎借鉴了20世纪最好的海地文学作品,创作了这个最初是田园牧歌,后来最终成为反乌托邦寓言的故事。在阅读这本书时,你能感受到热带空气的重量,以及背后的血液和历史的重量。
作为安提阿学院的一名本科生,赫伯特致力于安提阿的审查;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读艺术硕士时,他获得了霍普伍德小说奖(Hopwood Award)。他游历过中美洲,现在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英语系任教。
麦迪逊Smartt贝尔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小说时,我惊讶于一个奇怪的巧合,你和我写的关于海地革命的书的法国主人公的姓氏一样,赫伯特。我猜你不可能是这个虚构人物的后代,但你和圣多明克和海地有血缘关系吗?
 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这真是个有趣的巧合。尤其是考虑到我的法语完全是徒有虚名。赫伯特其实是我父亲继父的名字。所以它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追查过他们的家谱,但我怀疑这些赫伯特家的人更可能来自北方。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威胁说要恢复这家人失去的口音aigu.不过,如果我真要这么做的话,我想这本书应该是时候了。
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这真是个有趣的巧合。尤其是考虑到我的法语完全是徒有虚名。赫伯特其实是我父亲继父的名字。所以它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追查过他们的家谱,但我怀疑这些赫伯特家的人更可能来自北方。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威胁说要恢复这家人失去的口音aigu.不过,如果我真要这么做的话,我想这本书应该是时候了。
贝尔您的书的背景让我想起勒克莱尔庄园,这是一个表面上属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妹妹波琳的种植园,在杜瓦利埃政权时期,它变成了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后来为舞蹈家凯瑟琳·邓纳姆所有。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参观过这个地方,当时太子港(Port au Prince)的发展或多或少是围绕着它发展起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squattalize当地人。它有一种奇怪的神韵,部分是因为它仍然包含着古老的树木,你在你的环境中唤起。我想知道赫伯特·勒克莱尔是不是你的榜样,你和那个地方可能有什么联系。
赫伯特:绝对的。赫伯特·勒克莱尔是我的模特,也是我的灵感来源。你所说的在那里看到的正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迷人的地方。我完全是偶然接触到海地的,当时我对海地知之甚少。我并不是在寻找这个故事,但当我看到它时,我立刻意识到它汇集了许多我着迷的不同事物。
我当时正在写一本非常不同的小说。另一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美国一个地下政治活动分子的细胞。它的背景设定在当代,灵感来自对激进政治人物和美国历史上各种运动的兴趣。作为一名作家,我对意识形态的容忍度很低,但我对那些选择艰难奋斗的人有着永恒的魅力。2002年,当我还在写另一本书的时候,我碰巧读到一篇文章《纽约时报》.标题是《凯瑟琳·邓纳姆的伊甸园,来自地狱的入侵者》。伊甸园和地狱之间的浪漫二分法让人难以抗拒。
 原来,这个“伊甸园”就是你提到的那个现已不复存在的度假胜地,而它恰好也是这个国家最后一小片热带雨林的遗址。故事的背景是海地正在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以及它所面临的可怕的环境破坏。由于种种原因,这片曾经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几乎全部被砍伐殆尽,邓纳姆和庄园的管理人试图保护这片森林。这是一个令人钦佩和可以理解的目标。
原来,这个“伊甸园”就是你提到的那个现已不复存在的度假胜地,而它恰好也是这个国家最后一小片热带雨林的遗址。故事的背景是海地正在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以及它所面临的可怕的环境破坏。由于种种原因,这片曾经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几乎全部被砍伐殆尽,邓纳姆和庄园的管理人试图保护这片森林。这是一个令人钦佩和可以理解的目标。
“来自地狱的入侵者”被描述为武装团伙。正如片名所示,他们是故事中的反派。尽管我对这座岛了解不多,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善与恶、伊甸园与地狱的二分法。尽管被妖魔化了,但我马上怀疑的是,至少有一些人——如你所说——只是在蹲着。人们只是想活下去。人们需要住的地方,吃的东西,喝的水。基本的东西,但在像海地这样动荡的地方,这些东西代表着每天的斗争。
我开始写这本书,因为我想知道,当你陷入两个对立的,但也可以理解的,相互斗争时,会发生什么。一方面,保护那些美丽的、几乎已经灭绝的东西。另一方面,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人们挣扎着生存。我想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参与到这些斗争中来的,他们是谁。
所以我才对赫伯·勒克莱尔感兴趣。正如你所看到的,它最初是由一些抽象的想法驱动的兴趣,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象征而非真实。但就像许多对海地好奇的人一样,我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我把另一本小说放在一边,开始阅读我能弄到的所有东西:小说、学术巨著、通俗历史、游记。我怎么都吃不够。我开始把这个庄园看作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岛的整个历史。就像你说的,这种联系可以一直追溯到波拿巴和海地革命。然后在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统治期间,当政治暴力和镇压实现了暂时的“稳定”时,庄园发展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颓废之地。显然是米克·贾格尔的最爱。
在我早期对历史档案的一次深入研究中,我发现了一篇1974年的文章次),作者是被派来报道该度假村为纪念开业而举行的派对的人。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作者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戴着钻石、聚集在泳池边的富豪和社会名流感到困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周围的极度贫困和政治不稳定。即使在那时,贫民窟也在爆炸式增长。
在建造度假村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拒绝接受现实。最近,我偶然看到了一段采访负责建造这个地方的法国金融家(兼夜总会老板)的视频。这是很早以前的事,甚至在它还没有开业之前。采访者带着明显的沮丧指出,度假区的客人到达岛上时,将乘坐劳斯莱斯(Rolls Royce)穿过这个国家最贫穷的贫民窟。这位身着白色喇叭裤、赤膊上身、胸前挂满金链的金融家说,这没关系。他的客人是来“享受”的,而且当地人都很友好。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始于赫伯·勒克莱尔。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贝尔: 90年代末,我去了勒克莱尔住所。从通往家乐福的路往下坡走,在那个地方的墙旁边有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非常可怕,如果你以任何速度撞到它,车轴就会断裂。据说,这些人会在晚上蜂拥而出,抢劫被困在那里的汽车。当然,坑是他们自己挖的。
贝尔: 90年代末,我去了勒克莱尔住所。从通往家乐福的路往下坡走,在那个地方的墙旁边有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非常可怕,如果你以任何速度撞到它,车轴就会断裂。据说,这些人会在晚上蜂拥而出,抢劫被困在那里的汽车。当然,坑是他们自己挖的。
我在白天进入院子;从墙上的一个洞里走过去是很容易的。里面似乎有一个很好的海地人lakou的生活方式。组织和和平。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讲一口流利法语的领导出来和我谈话。他大概20岁启蒙哲学家这是海地中学体系授予你的学位。在出去的路上,和我一起的海地朋友告诉我,他是整个地方的土匪头子,如果我们晚上在那个拐弯处相遇,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俩的头都砍下来。
我认为凯瑟琳·邓纳姆不是把这里发展成酒店的人。你知道她什么时候接手的吗?在我看来,那一定是在你所描述的七十年代之后。
赫伯特凯瑟琳·德纳姆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她是非裔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受过舞蹈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训练。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学生,她第一次前往海地从事民族志工作。但她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家。她是二十世纪舞蹈界的领军人物,几十年来,她领导着自己的现代剧团——凯瑟琳·邓纳姆舞蹈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但她与海地的关系特别密切,在20世纪40年代末,她买下了居住地勒克莱尔。据我所知,她本人并没有参与度假村的开发。20世纪70年代初,她将庄园(或至少大部分)租给了法国企业家奥利维尔·科奎林(Olivier Coquelin),后者也是纽约著名时髦的河马俱乐部(Hippopotamus)的老板。他把旅馆变成了现实,虽然只是短暂的。
贝尔如你小说的气氛使我想起恋情,Colere,精神错乱的作品,部分原因在于,抽象地说,压迫和压抑的相互作用。我想知道她是否对你或其他海地作家有影响。
赫伯特是的,尽管我是在很晚的时候遇到她的。直到2009年新版出版后,我的书基本完成了。但你说的气氛相似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让我对海地着迷的部分原因是,我意识到政治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之大。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不关心政治。相当多的美国人甚至懒得去投票。了解了这一点,读到杜瓦利埃家族倒台后海地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了解到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提交选票,是令人振奋的。
维尤-肖韦是在Papa Doc统治时期写作的。他之所以在镇压方面如此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将无情的残暴与专横结合在一起。人们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而被当作政敌,也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在那种环境中,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正如莱斯利·马尼加特(Leslie Manigat)在1964年(当时他正在流亡)所写的那样,“政治对生活方方面面的侵蚀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不从政,政治本身就会来找他。”我觉得玛丽·维尤-肖韦的作品有力而感人,因为她准确地审视了这种侵犯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意义。
对我来说,因为我在《勒克莱尔住处》中卷入的冲突,我开始对创造一个梦想是逃离所有混乱的角色感兴趣。我不禁自问,如果他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干脆决定退出,会发生什么?如果他想抛开所有的政治、暴力和动荡,去创造美好的事物,试着和平生活呢?我想我的结论或多或少和维奥-肖维的结论是一样的:所有他试图逃避和忽视的事情,最终都发现他是一样的。
Marie Vieux-Chauve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还有其他的。没有人比Edwidge Danticat更能生动地描述海地。我也很喜欢莱昂内尔·特鲁洛特。我也从那些从外部接触海地的作家那里得到了很多。不仅仅是美国人。我还想到了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蒂埃和玛雅·蒙特罗。我认为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很大的价值。
贝尔我想知道是否有一种加勒比精神在美洲传播,不时地照耀着人们。显然,你写一本关于海地的书没有比我写我的书更好的理由了。但你们的英雄不断提醒我在海地的头半个小时里触动我的事情。在从机场到太子港的路上,尘土、泥浆、碎片到处都是,在我无知的眼里,这简直就是一片混乱。在马路的边上,也就是人行道的边上——在那个地区没有人行道,或者当时没有——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一件整洁的、熨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黑裤子,有完美的褶皱。灰尘在他周围飞舞,在他辛辛苦苦做的衣服上似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已经习惯了在海地看到这种现象,但我仍然不明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你的英雄是如何保持干净的?
赫伯特我明白你的意思。在我写这本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处于一种暂时的敬畏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所学到的东西和我所期望的东西之间的脱节。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受诽谤了。我们在新闻中听到海地的唯一原因——几乎也是大多数人听到海地的唯一方式——就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不想走到另一个极端,也不想把海地的一切都浪漫化,因为我们听到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但与此同时,在这个地方,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残暴的暴君,人们都不会屈从于任何问题。
这是你的书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理解赢得独立的过程。那些奴隶所面对的困难,他们所克服的困难。革命的决心从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新年刚从那里旅行回来。你提到的那种混乱感仍然存在。在地震之后,这一点可能更加明显。但我所到之处,都看到有尊严的人们决心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有他们的力量吗?我一点也不确定我会不会。
Christopher Hebert将会讨论沸腾的季节3月1日晚上7点在诺克斯维尔的劳雷尔剧院;点击在这里获取详细信息。他还将于3月5日下午7点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校区的霍奇斯图书馆礼堂朗读这本书;点击在这里获取详细信息。这两个活动都对公众开放。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2月28日。]
麦迪逊·斯马特·贝尔和克里斯托弗·赫伯特将出现在第24届年度大会上南方书节10月12日至14日在纳什维尔立法广场举行。所有活动均免费向公众开放。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