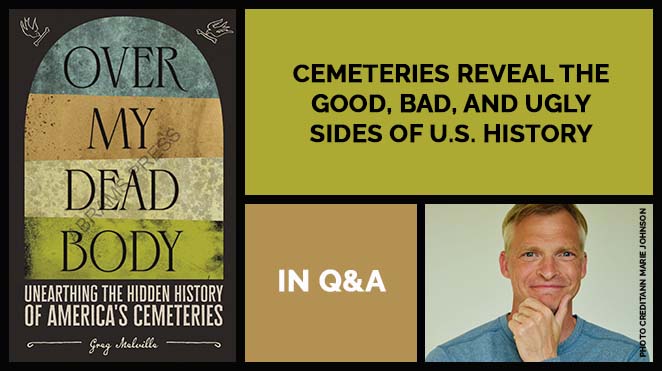“她设想了两种结果:在北方城市过着来之不易的满足生活,或者死亡。”她是科拉,一个出生为奴的年轻女子,对她来说,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自己的。科尔森·怀特黑德令人震惊的新小说,地下铁路,讲述了她的故事。这本书有望赢得今年的所有奖项——普利策奖、布克奖、国家图书奖等等——而且每一个奖项它都实至名归。

科拉的故事在南北战争前戒备森严的南方边境展开,那里的野蛮习俗让人一眼就认不出来——或者至少,它的野蛮习惯的本质让人难以辨认——而且令人产生可怕的共鸣。柯拉在一条被怀特黑德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地下铁路上奔向自由:穿越大地的隧道,机车和摇摇晃晃的箱形车厢,隐藏在厨房地板活板门下的车站,但从未远离危险。
如果地下铁路如果是电视节目,它的封面上会有一个印有字母代码的黑盒子,以警告读者其页面中包含的语言和暴力。这些注意都不足以让读者对该书开篇的残酷情节有所准备。在她甚至可以梦想北境的自由可能存在之前,科拉必须在乔治亚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里生存下来。它的主人特伦斯·兰德尔(Terrance Randall),正如臭名昭著的捕奴者里奇韦(Ridgeway)所描述的那样,在纪律方面拥有“华丽”的想象力。
为了让这个暴力的世界变得触手可及,怀特黑德运用了和兰德尔一样华丽的想象力。但最终的愿景是棱镜和广阔的,即使环境将人物的动机降低到最狭隘的关注点:逃跑,惩罚,生存,捕获。怀特黑德可以看到从这个世界的裂缝中渗出的光明,以及激励科拉和她的同谋们继续前进的短暂希望。最终,我们能够相信,即使在一个如此丑陋和残酷的世界里,爱也能扎根——它必须扎根。这在小说世界中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奴隶制的遗产对美国人的心理来说并不新鲜一样。但是怀特黑德在地下铁路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清算;这是一个比例模型,显示了有多少可以克服,还有多少需要拆除。
米兰:书中的叙述者地下铁路是无所不知的,但有时徘徊在非常接近一个特定的人物的观点。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特定的逻辑——一种我们可能不同意其结论的逻辑——直到我们已经遵循了它的前提。我们几乎成了同谋。你能谈谈你自己对叙述者声音功能的看法吗?
怀特海德:叙述者向每个人物的意识扭曲和弯曲,如果它起作用,读者确实被席卷到人物的哲学/世界观。但叙述者也解释了这个世界,做了一些讽刺的旁白,并且——比如科拉的逃亡奴隶广告——不时地给予祝福。所以,希望叙述者在做自己的工作,但也要时不时地打破它的指令。
米兰当前位置通过把铁路变成字面上的一组轨道,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随意处理来获得更大的真相,有人可能会说,你冒着干扰我们对我们国家身份的那一部分的估计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让某些人与实际事实作斗争是多么困难。对此有何回应?
怀特海德好吧,我不负责人们如何选择或选择不考虑我们的国家身份,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米兰当前位置在瓦伦丁农场对自由的男女发表演讲时,演说家伊利亚·兰德称美国是“一个错觉,一个最大的错觉”。他说,美国不应该存在,因为“它的基础是谋杀、盗窃和残忍”。然而我们却在这里。”最近,NFL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拒绝在奏国歌时起立,这是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侵害有色人种社区的抗议。你认为在未来,这种矛盾——“我们在这里”中的“还”——会变得不那么尖锐,甚至消失吗?
怀特海德不完全是,但我想我必须承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确实在逐步地进步,缓慢地进步,所以也许可以想象,在遥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进步。
米兰霍姆是捕奴者里奇韦的得力助手,相反,他是一个经常在笔记本上记东西的年轻黑人。他是一个迷人而又令人烦恼的角色。他是怎么来的?他的原型是你在研究中遇到的人吗?
怀特海德荷马还是荷马。在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中有许多奇怪的地方,这在一些故事中很明显:被解放的奴隶继续为他们的主人免费工作,而主人即使在折磨、强奸和虐待他们的时候也声称爱他们的奴隶。当然,霍默和李奇韦的故事并不奇怪....
米兰基督教的教义和人类世界的实际运作之间的争论贯穿全书。如果这里有上帝的话,那也是一个冷漠的上帝,但与此同时,“幽灵隧道”也隐藏着最轻微的暗示,如果不是超自然的,那就是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荷马,和他的同名人物一样,最终陷入了一种不确定的境地。如果有的话,你想让读者考虑在这部小说的世界中,除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残酷之外,还有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
怀特海德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人类是靠自己的,偶尔会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让事情变得奇怪,也许我已经把它放在小说里了。
米兰:科拉与音乐的关系非常矛盾;有一次,她想起了一首特别的歌:“这么痛苦的事情怎么能成为一种快乐的方式?”在致谢中,你提到了一些你为之创作的音乐,包括我也喜欢的misfits乐队,但他们的恐怖风格总是显得有些做作。听一个乐队的专辑叫野蛮的遗产一边写着,令人痛苦的细节,关于一个真实的野蛮遗产?
怀特海德:我工作的时候会循环听2000多首歌,都是我喜欢的歌,从Kraftwerk到Stevie Wonder,从Minor Threat到Funkadelic,我从来没有把工作和音乐联系起来,除非听Peggy Lee的《Is That All There Is?》来吧。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6年9月14日。已更新以反映新的事件信息。]

史蒂夫Haruch住在纳什维尔。他的文章发表在NPR的Code Switch,《纽约时报》,以及纳什维尔的场景他是美国的特约编辑。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