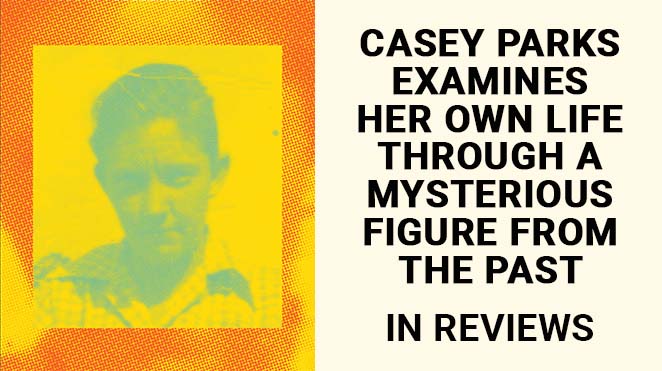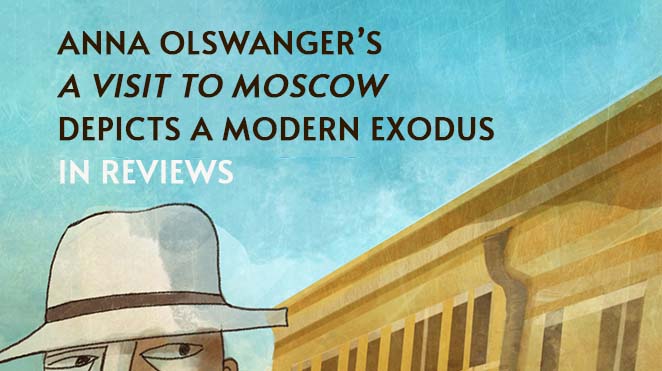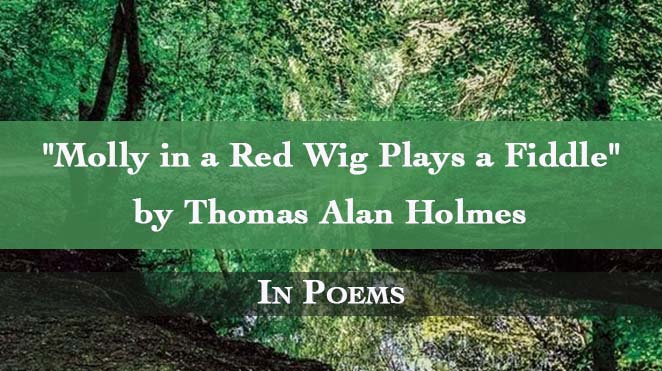小亚伯·琼斯,爱丽丝·兰德尔小说的死后主角叛军大喊,是对那个太不可能的角色的悲剧性模仿:黑人保守派。琼斯比现实生活中的谢尔比·斯蒂尔和克拉伦斯·托马斯略年轻一些,他先后担任过外交官员、中央情报局特工、纳什维尔的银行家,死后还担任过小布什政府在五角大楼的“特别顾问”,这个虚构的职位把琼斯置于伊拉克战争的中心。
琼斯的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兰德尔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宣布了。在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白人)和她的孩子们度假时,琼斯在Rebel Yell(一家集餐厅和内战重演演出于一体的演出——想想《蓝灰》里的《中世纪》)里的马靠得太近,导致致命的过敏性休克。
 对琼斯来说,这是一种特别讽刺的方式,他的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纳什维尔一位热情的民权律师。事实上,琼斯是一颗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幸运的地位和良好的时机,他能够在种族隔离后的白人体制中成功,几乎没有种族包袱。他就读于哈佛大学(Harvard),然后顺利进入美国的外交和情报精英阶层。尽管琼斯被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但他并不是一个煽动者;就像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一样,他的保守主义更多地植根于性情,而不是怨恨。从远处看,他是一个完全无拘无束的人,从一个成功跳到另一个成功,似乎毫不费力。
对琼斯来说,这是一种特别讽刺的方式,他的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纳什维尔一位热情的民权律师。事实上,琼斯是一颗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幸运的地位和良好的时机,他能够在种族隔离后的白人体制中成功,几乎没有种族包袱。他就读于哈佛大学(Harvard),然后顺利进入美国的外交和情报精英阶层。尽管琼斯被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但他并不是一个煽动者;就像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一样,他的保守主义更多地植根于性情,而不是怨恨。从远处看,他是一个完全无拘无束的人,从一个成功跳到另一个成功,似乎毫不费力。
兰德尔,是风已逝(2001)和普希金和黑桃皇后(2004),主要通过琼斯的第一任妻子霍普(Hope),在书中花了大部分篇幅来阐述和复杂化这种第一印象。霍普是黑人,但她和前夫之间的差距很大:尽管她跟随他去了第一次海外部署,在马尼拉,然后是马提尼克岛,但她不太了解他,尤其是他拒绝享受他已故父亲的自由主义荣耀。
兰德尔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但部分否定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个人化的、伪弗洛伊德式的:琼斯恨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同辈,因为他们拒绝让他先做一个男孩,然后再做一个男人。兰德尔在开篇的前奏中不无道理地讲述了1963年琼斯一家南下伯明翰,参加在16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中遇难的四名女孩的葬礼。年轻的琼斯把这些女孩——事实上,他是受其中一个女孩母亲的指示,把她们看成是成年人鲁莽游戏中不知情的受害者。
琼斯几乎不是一个煽动者;就像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一样,他的保守主义更多地植根于性情,而不是怨恨。从远处看,他是一个完全无拘无束的人,从一个成功跳到另一个成功,似乎毫不费力。
琼斯的父亲未经讨论就把他拉进了民权战争,然后在他面对种族主义表现出恐惧时惩罚他,甚至打他,比如有一次他在三k党成员在他家草坪上放火烧十字架后尿湿了裤子。结果,琼斯“憎恨那些他非常信任的人,以至于他没有剩下的仇恨来憎恨三k党。”琼斯断定,他的父亲并不勇敢;他是弱。不然他为什么要让一个孩子去做大人的工作?“他会找到强壮的人,”兰德尔写道。“他会让所有软弱的人、所有邪恶的人、所有软弱和邪恶的人付出代价。”
但这不是真正的答案,至少不是全部。剩下的钱来自琼斯的儿子阿贾伊。阿贾伊(阿贝尔·琼斯四世的简称)与父亲关系半疏远,与母亲和她的新丈夫生活在一起,他是自由主义母亲和保守主义父亲的结合,融合了黑人的骄傲和主流头脑。兰德尔写道:“霍普和韦克罗斯(她的丈夫)培养出的阿贝尔的天性造就了一个身材匀称的铜像男孩,他留着整齐的辫子,举止老派,词汇从‘操’到‘仇外’都有。”阿贾伊庆祝自己的黑人身份,即使他在白人文化中、在白人文化中、在白人文化中游移自如。霍普在书的最后意识到,他不像他的父亲,更像民权运动后的另一位黑人公职人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个来自阿贝尔宇宙的另一端的人”。
另一方面,琼斯无法调和他作为一个黑人的个人和集体过去与他周围的非黑人世界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他把这种不足归咎于他父亲那一代人。一旦黑人南方以外的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他就逃离了,认为自己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卖自己。兰德尔写道:“亚伯会为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感到羞耻,也会受到鼓舞,因为他做了亚伯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
阿贾伊庆祝自己的黑人身份,即使他在白人文化中、在白人文化中、在白人文化中游移自如。霍普在书的最后意识到,他不像他的父亲,更像民权运动后的另一位黑人公职人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个来自阿贝尔宇宙的另一端的人”。
作为对黑人保守派的控诉,这是有点不公平的——毕竟,马丁·路德·金梦想的推论,即不应以肤色,而应以“品格的内容”来评判男人和女人,认为同样是这些男人和女人,可以自己决定肤色在他们的人格中扮演什么角色。然而,作为一个关于一个人的故事,叛军大喊令人信服的;琼斯虽然已经去世,但在书中却非常活跃,尽管她的写作有时会转向cliché,兰德尔设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物肖像。
但真正重要的是叛军大喊是一种针对个人和集体之间某处的批判。兰德尔并不打算把一个人拉下马,她也不满足于砍掉黑人政治光谱中的一个分支。她所传达的不下于是一种情感的报告,在后民权时代的大多数黑人可能——尽管很少有人像琼斯那样直率——默默地接受这种情感:面对美国白人残余的权力,以及它向黑人伸出的手,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背弃自己的过去,拒绝跨越一种、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挑战。
现在奥巴马为这条特殊的隧道提供了一束光,兰德尔的书恰逢其时。叛军大喊应该由黑人和白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如果是这样的话,兰德尔将不仅仅是写了一本好书——她将为美国黑人传奇的下一篇章做出重大贡献。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