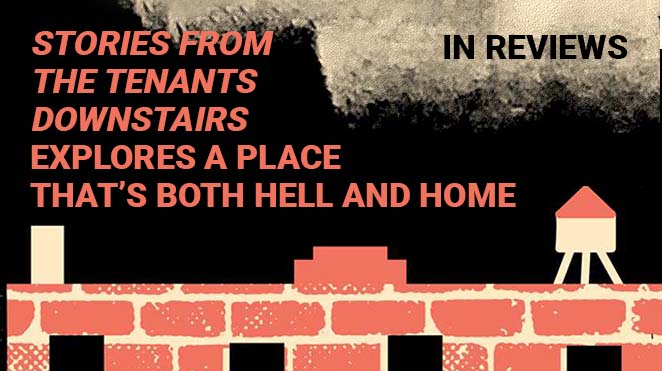我今天休假并不是出于迷信。我都没注意到今天是13号星期五。我只是想从我的日常工作中休息一下,其中包括我在“世界危机”(Worldcrunch)的工作,这是一家国际新闻机构,恐怖主义是日常话题。我期待着能有机会放松一下精神,和一位来自纳什维尔的好朋友一起享受一顿悠闲的午餐。我们在巴黎第六区相遇,在圣叙尔皮斯(Saint-Sulpice)附近一家迷人的意大利餐厅碰面。之后,我们逛到一家著名的糕点店吃甜点,仍然不停地聊天。
 这是我几乎从未有过的一天。我家乡的朋友想象我坐在咖啡馆里,翻开一本书,或者沿着Champs-Elysées购物,或者在杜伊勒里花园放松。但巴黎的生活可不是这样的。这是通勤、工作、家庭作业、生日派对、洗衣(没有烘干机)和铲猫箱。它是支付账单,预约儿科医生,和乖戾的邻居打交道。当然,我们已经享受了巴黎的许多文化和美景,但我们不是在度假。
这是我几乎从未有过的一天。我家乡的朋友想象我坐在咖啡馆里,翻开一本书,或者沿着Champs-Elysées购物,或者在杜伊勒里花园放松。但巴黎的生活可不是这样的。这是通勤、工作、家庭作业、生日派对、洗衣(没有烘干机)和铲猫箱。它是支付账单,预约儿科医生,和乖戾的邻居打交道。当然,我们已经享受了巴黎的许多文化和美景,但我们不是在度假。
上周五是神奇的,因为我感觉像一个游客,像一个可以带着敬畏之情环顾四周的人,她没有查看她的手表或打破它在火车上的某个地方。我没有带笔记本电脑、背包或杂货。我涂了口红,裤子也没皱。
将近三个小时的午餐过后,我依然容光焕发,我去学校接儿子回家。周末到了,是时候吃披萨、看电影、放松一下了。男孩们有他们的战队我把他们哄上床,就在那时电话开始响了。我的同事们打电话来确认我们是否都没事,我丈夫也在和他联系,来自家乡的信息开始涌入我的收件箱。我们打开新闻,发现几个疯子制造了法国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我看新闻,午夜过后很久才回复邮件。我终于上床睡觉了,想着我该怎么跟我那些眼神天真的孩子们说。
 我们在将近五年前搬到巴黎,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成为世界公民,学习另一门语言,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上学,在美国的常规生活所不能允许的范围内,更多地了解世界。一份工作让他们有可能放弃在纳什维尔已经很好的生活,但离家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不是工作机会。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儿子们,给他们我们从未有过的东西的机会。
我们在将近五年前搬到巴黎,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成为世界公民,学习另一门语言,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上学,在美国的常规生活所不能允许的范围内,更多地了解世界。一份工作让他们有可能放弃在纳什维尔已经很好的生活,但离家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不是工作机会。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儿子们,给他们我们从未有过的东西的机会。
但正是巴黎的中心地位和象征意义,现在让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去年,我两次试图让我的孩子们了解可怕的暴力和死亡。星期六早上,他们从房间里出来,穿着香甜的史酷比和巴塞罗那睡衣,爬到床上,像往常一样拥抱我们。我睡眼惺忪,但该是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了,他们会在周末从朋友那里听到,周一在学校里也会听到,那时课间休息和平时的外出活动都将暂停,直到另行通知。
我只睡了四个小时。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最好的父母向孩子传达悲剧的方法,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查理Hebdo今年早些时候,那里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我简单地告诉孩子们,一些非常坏的人在晚上伤害了很多人,无辜的人被杀了。我没有提到人质,自杀背心,或者伊斯兰激进主义。我告诉他们,他们会注意到学校再次发出警告,周末我们可能会待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无论对错,没有戏剧性,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眼泪。我不想吓到他们,也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心神不宁。
做了很多好事。几天后的晚上,我们六岁的孩子醒了过来拿杯水。看到爸爸还没回家,他哭了起来。“爸爸在哪里?他哭喊着,抽泣着奔向我的怀抱。“他死在地铁上了吗?”他死在地铁上了吗?”
 这是悲惨的。我给他看了爸爸在回家路上的短信,但过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我们很幸运没有在周五晚上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伤害。但这里发生的事情让我的孩子们产生了一种持久的恐惧,他们太小了,还不应该有这种感觉。请注意,我并没有对他们说过在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地铁上感到害怕,或者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亲爱的儿子的恐慌如此痛苦。不是别人给他灌输的东西。这是他自己非常真实和现实的恐惧。
这是悲惨的。我给他看了爸爸在回家路上的短信,但过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我们很幸运没有在周五晚上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伤害。但这里发生的事情让我的孩子们产生了一种持久的恐惧,他们太小了,还不应该有这种感觉。请注意,我并没有对他们说过在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地铁上感到害怕,或者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亲爱的儿子的恐慌如此痛苦。不是别人给他灌输的东西。这是他自己非常真实和现实的恐惧。
所以,是的,恐惧是存在的,而且大部分是非理性的。每当我听到办公室的警报声,每当我的窗外有很大的噪音,还有我说它——当我和一群阿拉伯年轻人在地铁车厢里时。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国总理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储备了有史以来第一批毒气解毒剂。
但让我充满希望的是,这里有比恐惧更多的东西。在我奔跑的公园里,有美丽的飘落的黄叶;我的小家伙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刚刚在拼写测试中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市场上华丽的农产品;尽管我们感到严重的不安,但我们都感受到一种压倒性的团结和团结。
周一午餐时,我和一些同事步行到巴塔克兰剧院,向一周前在剧院被屠杀的89人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刚到那里,一个音乐家就骑着自行车出现了,他拉着一架黑色钢琴,钢琴顶上喷着和平标志。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他演奏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想象》(Imagine)。于是我们说"所有人都为今天而活"

Liz Garrigan是一位资深编辑Worldcrunch为英语读者提供全球新闻报道。以前的编辑纳什维尔的场景加里甘现居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