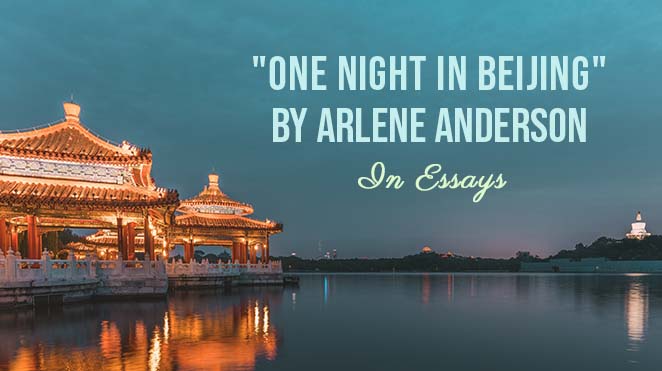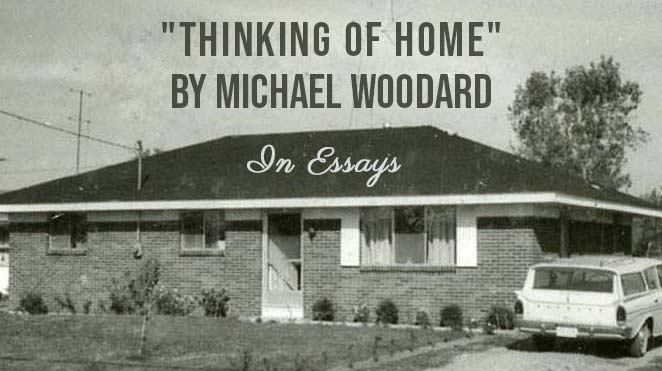多萝西·艾利森(Dorothy Allison)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生活在南方的工薪阶层。她以短篇小说集开始她的职业生涯垃圾(1988),由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出版社Firebrand Books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卡罗莱纳的混蛋(1992),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和推崇。从那以后,她写了一本随笔集,皮肤:谈论性,阶级和文学(1994);关于讲故事的沉思,有两三件事我可以肯定(1995);第二部小说,Cavedweller(1998)。每一部作品都不断获得评论界的成功,并拥有大批粉丝,他们欣赏她的创作技巧,也欣赏她愿意写边缘人物的性格。多萝西·艾莉森的作品探讨了性别、家庭、暴力和性虐待。
 艾莉森目前是戴维森学院的麦基写作教授。
艾莉森目前是戴维森学院的麦基写作教授。
米兰:你的很多作品都有自传体元素,但都被归类为小说。我很好奇你对回忆录的看法:你认为这两种类型有什么不同?
艾莉森:我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讲故事的,我认为好的写作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如果你写回忆录,你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间的位置上,因为回忆录是你当时所理解的故事。我喜欢它,我认为我们需要大量的它,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对文化的体验。我只是觉得我不太确定我知道任何时候发生了什么。它在记忆、解释和讲好故事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两三件事我可以肯定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而是对讲故事的思考,探讨了我家里发生的很多故事——我很早就发现,我的家人喜欢好故事甚于真相。我会去研究细节,发现他们刻意夸张了。或者有些事情完全是虚构的,但听起来太好了,我的家人会重复它们,然后它们就会被奉为圣典。我怀疑自己也有这种倾向。所以我写小说。我也写小说,因为我想创造一种特定的故事。我想制造某种情感上的冲击。在小说里我能做得更好。
那么,小说和回忆录在写作技巧、语言和设计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必须达到同样水平的质量,质地和理解。但如果我读到一些东西,我被告知这是一本回忆录,这是真的,我需要绝对信任叙述者。如果叙述者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他们说错了,我需要他们承认这一点。当我读回忆录,后来发现那不是真的,我对现实的把握就动摇了。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行。
我在埃默里大学教书时,一个大丑闻爆发了,不仅是弗雷的丑闻,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玛格丽特·琼斯),她假装是洛杉矶黑帮成员,结果却是来自俄勒冈州的中产阶级孩子。我试着和年轻的作家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嗯,如果这是一个好故事,那就可以。”我说,“不可以。”你不能把所有的故事都混为一谈。你需要区分哪些是你认为真实的故事(回忆录),哪些是你为了情感影响而创作的小说。”
我很早就发现我的家人喜欢好故事胜过真相。
米兰:有没有可能真实故事的整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概念?
艾莉森:是的。总有人讲故事是有原因的。我最喜欢的可能是玛丽·卡尔(Mary Karr)和马克·多蒂(Mark Doty),他们两人都写了一种文学回忆录,总是以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为背景,两人都以承认他们对以前写过的东西进行了新的描述而闻名。当马克·多蒂(Mark Doty)在写他妹妹的时候,他说他二十多岁时所理解的东西和他现在所理解的不一样,他讲述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这是一件非凡而美妙的事情。但通俗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社会和非历史的,我觉得这很可疑。这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不安。
米兰:我想知道你能否谈谈在你的工作中灵感与工艺的问题。你认为它主要是由一个或另一个主导的吗?它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艾莉森:我从灵感开始。我有时不得不重新创造灵感。和工艺?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季度的。我的意思是,我出生在工薪阶层。我是家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人。在美国文化中,我是一个可疑的人,而不是那种应该成为作家的人。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创造一种合法性。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格外小心。我必须写得好,才能让人读。 And I think that is a salvation. That’s why I’m a slow writer. If I write sloppy, I’m dead, because they’d love to bury me. I think that’s true for any of us who push toward the edge of acceptable categories of “writer.” And that’s always shifting. We’ve even come to a moment when middle-class white boys are having a hard time.
米兰:我知道你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男女同性恋作家,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将小说写作视为一种政治行为的。
艾莉森: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我认为很多小说家不相信这一点。有一种隔离,尤其是文学小说。我们可以假装它没有任何政治影响。但我长大后成为了早期妇女运动的作家。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家是格蕾丝·佩利(Grace Paley)这样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认真对待自己,认为自己既是作家,也是公民,并将这些责任视为同等重要。
 我不可能不这么想的。但也有一些是天生的。我是那种边缘人。我总是会注意到我的人民,我的部落不被允许参与讨论。当我去大学做阅读时,当我和学生交谈时,总会发生一些事情。不管是人多还是少,后面都会有孩子,也会有年轻人等着和我说话,直到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他们是年轻的酷儿作家。他们是获得奖学金的年轻学生。他们是年轻的南方孩子,他们想写作,但又害怕。作为一个政治家,我的目的就是站在那里,成为他们的榜样。 There’s not a whole lot I can tell them. I can’t impact them immediately, but my job is to model; my job is to say, “You have a right to your territory.” That’s political.
我不可能不这么想的。但也有一些是天生的。我是那种边缘人。我总是会注意到我的人民,我的部落不被允许参与讨论。当我去大学做阅读时,当我和学生交谈时,总会发生一些事情。不管是人多还是少,后面都会有孩子,也会有年轻人等着和我说话,直到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他们是年轻的酷儿作家。他们是获得奖学金的年轻学生。他们是年轻的南方孩子,他们想写作,但又害怕。作为一个政治家,我的目的就是站在那里,成为他们的榜样。 There’s not a whole lot I can tell them. I can’t impact them immediately, but my job is to model; my job is to say, “You have a right to your territory.” That’s political.
这也是作家写作的本质,无论我们的政治背景或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如果你是一名作家,你会试图鼓励最广泛的声音。你想知道不为人知的故事。你希望坐在教室后面的孩子们继续前进,即使你没有政治分析,不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很重要。
米兰:一些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者等等的作家发现这些分类有点限制性。
艾莉森:是的,他们可以。你必须抵制它们。你必须抵制空喊口号。哦,天哪,你得试着不要太陈腐。
米兰:你是否感到在特定问题上说话的压力,以特定的方式说话?
艾莉森:是的,但它一直在变。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我的内心。前几天晚上我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小大学吉尔福德学院做了一个项目。这是一所贵格会大学——优秀的学生,非常优秀——对社会负责,积极参与,有趣,富有实验性。但这是一次公开阅读。所以在房间的后面,我能看到一些年长的、蓬头垢面的、头发花白的女士们怀疑地盯着我,其中一些是退休到教堂山地区的教条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他们看着我,好像在说:“她到底会不会说些政治上的东西?”我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并不是我那天晚上的目的。我没有办法真诚地取悦他们,但我也没有办法避免承认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在做着令人着迷的工作。 They’re semi-retired, irritable. … I like people like that. They make me feel safer in the world, even though they sometimes chew my butt.
米兰:似乎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到让自己感觉舒服,这样你才能知道作为一名作家你的愿景是什么。
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家是格蕾丝·佩利(Grace Paley)这样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认真对待自己,认为自己既是作家,也是公民,并将这些责任视为同等重要。
艾莉森:是的,你必须非常实事求是,意识到有些人会生你的气。但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更容易接受了。除非我今天过得很糟糕。你也有过糟糕的日子,即使他们爱你,你也不信任他们。
米兰:我对那本新小说很好奇。它被称为她你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的事情就太好了。
艾莉森:啊,是的。这总是最难的部分,不是吗?已经很晚了。花十年时间写一部小说是很尴尬的。但我不能否认。我开始写关于暴力的文章。但我想写的是暴力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想写的是在家庭中发生的事情,人们在暴力中幸存下来,并被它彻底改变了。所以我写了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我称她为“金童”之一,一个即将毕业并前往纽约的斯坦福年轻学生,她的母亲很崇拜她。 She’s political and she’s lesbian and she’s one of these kids I’ve met, these golden children who are so beautiful and so smart and so politically engaged and generous and wonderful, and I adore them, and I’m terrified of them, and I’m jealous of them.
我对待这些优秀的孩子,和我一起工作的孩子,我的一些学生的方式,我必须找到一种爱他们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所以我把她放在了一个故事里。我把她从停车场顶扔了下去。我让她昏迷了10个月,我问自己:如果她必须过着我的堂兄弟、侄女和侄子一直过着的那种生活,她会像我一样幸福吗?他们不被爱,世界支离破碎。我从这里开始,沿着它走到另一边。她的母亲变成了一名反暴力组织者,干劲十足,令人讨厌。她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隐士,不想和她的母亲打交道,只能勉强与世界接触。这是一部长篇复杂的小说。真高兴我马上就能看完。
米兰:它有多大?
艾莉森:天啊,我已经写了几千页了。我已经可以超越迈克尔·夏邦的最长小说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它改变了。我的文件柜里都是没人会看到的东西。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件事吗?工艺?我写了三页,扔掉了两页。这是一个非常烦人的习惯。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