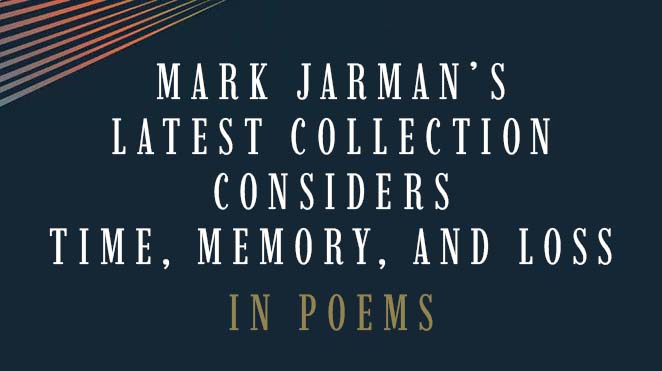大卫·詹姆斯·泊桑特在书中写道:“有人关注,有人不关注。动物的天堂.“还有一些人看得太多了。如:听着,我很舒服,我可以盯着它看。这里的“它”是一个十几岁女孩的义肢。但这也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渴望和失落感,它们标志着波桑特笔下人物受挫的生活。秉承雷蒙德·卡佛和理查德·福特的传统,泊桑特创作了一部微妙、严肃、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集,讲述了不幸的人在当代美国荒凉的环境中寻找救赎的故事。
 虽然福特和卡弗是最容易拿来作比较的人物,但这些引人注目的故事中有许多都让人想起了老一辈的声音。我很快就想到了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这要归功于波桑特喜欢研究外表不起眼的人的生活,他喜欢利用古怪而令人难忘的幻想来构建主人公通往顿悟的旅程。
虽然福特和卡弗是最容易拿来作比较的人物,但这些引人注目的故事中有许多都让人想起了老一辈的声音。我很快就想到了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这要归功于波桑特喜欢研究外表不起眼的人的生活,他喜欢利用古怪而令人难忘的幻想来构建主人公通往顿悟的旅程。
在《蜥蜴人》(Lizard Man)中,丹(Dan)是一名短期厨师,也是一名正在戒酒的酒鬼,他和邻居小卡(Cam)一起旅行,解决小卡疏远的父亲的遗产问题。他们一到家,就在后院的游泳池里发现了一只鳄鱼宠物,这是小卡父亲死后被遗弃的。影片中出现了一场略带喜剧色彩的营救行动,同时闪回了丹是如何在一次不幸的酗酒暴怒中失去家人的。小卡将短吻鳄放归佛罗里达沼泽,以结束与父亲的矛盾关系,这也成为了丹发现自己需要救赎的契机:
他动作敏捷,身体强壮,我很高兴天气寒冷,还下着雨,这样小卡就看不到我脸颊上的泪水,也不会知道我颤抖是因为抽泣。小卡放开了我,我以为我会掉下去,但我却在跑。运行!我又笑又叫又跳。我把拳头举到空中。我尖叫着:“走!去吧!”就在鳄鱼快要游到水里的时候,我冲了过去,我的指尖追踪着它尾巴上最后的隆起和鳞片在我面前舞动。
 当然,任何一个南方人写的包含假肢的故事都不能与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好乡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相提并论。在《截肢者》中,独臂女孩莉莉(Lily)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妖女出现的,她把自己献给了布里格(Brig)。布里格是一个悲伤的药品推销员,是一个堕落的摩门教徒,在婚姻结束后移居到亚利桑那州。但波桑特扭转了奥康纳的情节,让推销员得到了必要的优雅时刻:诱惑者原来是无辜的——一场悲剧的受害者,迫切需要与人接触。当莉莉消失后,布里格开始思考他的困境,并得到了他自己的顿悟:“如果你足够努力地希望,你可以希望一个东西存在。他曾经相信过。他想再相信一次。闭上眼睛,希望——这是他能祈祷的最接近的地方。”
当然,任何一个南方人写的包含假肢的故事都不能与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好乡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相提并论。在《截肢者》中,独臂女孩莉莉(Lily)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妖女出现的,她把自己献给了布里格(Brig)。布里格是一个悲伤的药品推销员,是一个堕落的摩门教徒,在婚姻结束后移居到亚利桑那州。但波桑特扭转了奥康纳的情节,让推销员得到了必要的优雅时刻:诱惑者原来是无辜的——一场悲剧的受害者,迫切需要与人接触。当莉莉消失后,布里格开始思考他的困境,并得到了他自己的顿悟:“如果你足够努力地希望,你可以希望一个东西存在。他曾经相信过。他想再相信一次。闭上眼睛,希望——这是他能祈祷的最接近的地方。”
大多数故事都遵循一个熟悉的模板:穷困潦倒、运气不好的人物面临着奇怪、不寻常的环境,通常涉及到动物,这些环境引发了突然的意识——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希望,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有《蜥蜴人》里的短吻鳄,《截肢者》里失踪的猫,《最后的陆地哺乳动物》里一头猛冲的野牛,还有《狼想要什么》里的... .你懂的。
在《亚伦的结局》(The End of Aaron)一书中,一位年轻女子描述了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友在疯狂和清醒之间危险地徘徊;对蜜蜂过敏就像众所周知的契诃夫之枪,预示着一个悲惨的结局。在《绝望的几何》(The Geometry of Despair)一书中,一对失去婴儿的夫妇在院子里遇到了一小群鹿,引发了另一场由衷的反思:“鹿跑到我们院子的边缘,跑进了灌木丛。”丽莎从窗户上掉下来,滑到地板上。她背靠着墙坐着,抬头看着我,脸上湿漉漉的。我觉得我在葬礼后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眼睛,我既害怕又羞愧,但又充满了希望。”
用动物作为人类发现的工具,在能力较差的人手中可能会显得乏味和做作。大卫·詹姆斯·波桑特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天赋将这些故事从公式的表面上提了出来,他情感上的诚实赋予了它们真正的重量和分量。在这本合集的最后一个故事《动物的天堂》(the Heaven of Animals)中,他最巧妙地展示了这种天赋。在这个故事中,他再次介绍了《蜥蜴人》(Lizard Man)的主人公丹(Dan),他穿越全国,与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的成年儿子最后一次团聚。在旅途中,丹必须面对生命的悲剧性徒劳和继续活下去的需要:“这是一个奇迹,一个恐怖——这个世界和他的儿子消失了,从存在中消失了。杰克死了,豆子还是会被晒干、压碎、用水过滤,男男女女会举起杯子读当天的新闻,列购物清单,担心优惠券,担心他们的轮胎是否需要转动。”
从这些故事中学到的教训并不简单。世界动物的天堂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残酷无情。他们所提供的安慰是对私生子的同情,这使得这部美好的处女作既可爱又难忘。

Ed Tarkington拥有弗曼大学的学士学位,弗吉尼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博士学位。他的处女作,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碎,阿尔冈昆图书公司(Algonquin Books)即将出版。他住在纳什维尔。
标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