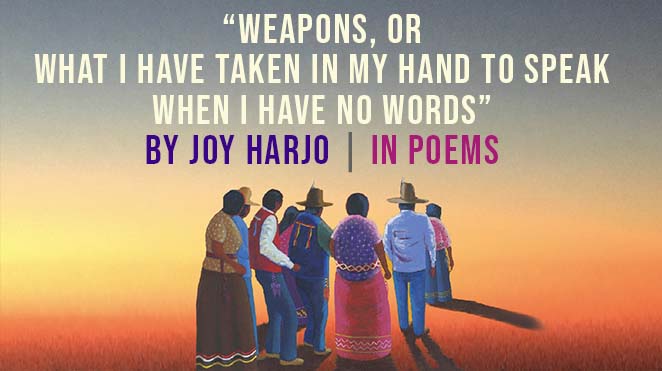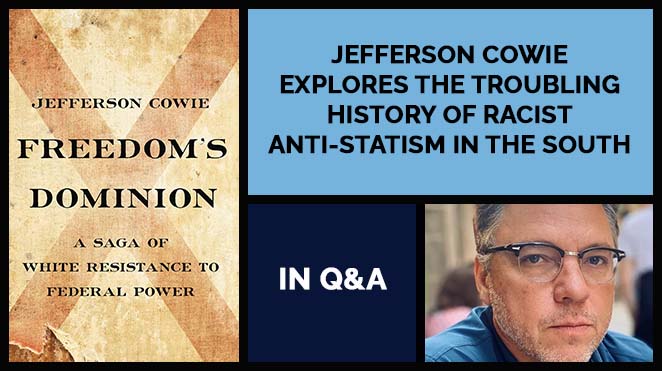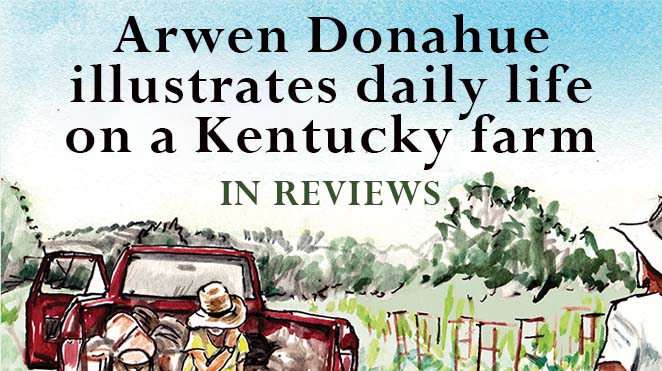当马歇尔查普曼在车站上酒店两个星期前,她不可能看起来更写标题。她整个night-barefoot赤脚行走在酒吧里宽松的牛仔裤,赤脚在什么看起来像一个男人的纽扣的衬衫,赤脚在舞台上。她的头发是疯了,被风吹的,half-clipped头上像鹅卵石。你无法想象那么拘谨表演者。然而,与一系列放松后无防备的个人细节,她的声音听起来几乎道歉。
 “明顿的火花让我这样做,”查普曼说,靠她在靠近麦克风瘦长的框架。“我看到她在这里,我认为,“他妈的,我不像我以为我是免费的。’”
“明顿的火花让我这样做,”查普曼说,靠她在靠近麦克风瘦长的框架。“我看到她在这里,我认为,“他妈的,我不像我以为我是免费的。’”
有趣,我正坐在一个酒吧高脚凳思考同样的事情。随着查普曼讲述一个故事关于威利纳尔逊的旅游巴士里(你怀疑什么),我看了看四周的火花,开启了他下一尺高阶段几分钟前,一屋子的热烈的掌声。她在她的米色clip-clip-clipped复古高跟鞋旁边的窗帘后面酒吧,从视野中消失。
也许明顿(生于吉尔Webb)改变了衣服,只是把隐身塞进一群denim-clad陌生人。她说这个名字她发明的拼凑出她祖母的少女和已婚的名字不再感觉她扮演一个角色,但她的人。“叫我明顿,”她告诉面试官,可能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调查。
但现在我看到她穿上展示我从未亲眼目睹,我怀疑她可以轻易地消失。50分钟前,她打开了她与她确认为“一个快节奏的葬礼的诗。”她结束的时候,听众的反应像爱丽丝可能如果她被推迟到兔子洞:惊讶,稍微感到不安寻找地球上的一切都沿着她离开。
火花开始表演让一群人聊天。一长排蜿蜒从酒吧,一些坐着从她背上被拒绝了。在七分钟内,整个观众在她的束缚,包括一个人从后门。他转过身来,盯着火花开始背诵一首诗叫做“薇琪泡菜的妈妈。“大摇大摆地穿过舞台,把她的衣服和裙子的骗子的手里拿着一个钱包她手臂商标的一个道具的能指identity-she与夸张的口音说话声音沙哑:
我第一次看见
薇琪泡菜的妈妈,她昂首阔步的小吃店,
——两件套
豹纹泳衣。
十个俯卧撑
在旁边的混凝土池
吸引男孩的眼睛像苍蝇
卷曲的炸薯条和co-cola之前订单。
她旁边坐着她杰出的伴奏,约翰杰克逊,他总是在显示,移动音乐。他一直保持一种谈话与她的吉他,但它不是键的内容的话,他们的声音和力量。火花所有正确的,微妙的动作,但真正的活力在她的声音。她说话的声音的音色,连同她的面部表情和控制另一只空闲的手,与每个角色改变她的名字。
演出结束的时候,观众为她感觉有点疲惫,累坏了有陷入了一片后,接下来,打在每一个情感层面。“那是什么?“我听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问他的日期后火花了。
 “那是一大堆的生活,”她回答说,她的话陪我很久之后。
“那是一大堆的生活,”她回答说,她的话陪我很久之后。
我意识到,我觉得是非常明顿告诉我期待什么。“后看到我的表演,”她说,当我们两人在咖啡店一天早上前一周,“人们感情疲惫不堪。像在纽约,她刚刚完成,人已经在观众会说,‘哦,我的天啊。不是因为它是非凡的;他们只是感情疲惫不堪。”
她喝了一小口的水。“他们会再来!我认为人们想的感觉。”
显然,他们做的,。今年4月,在这里还有她最近的专辑后,巧合的是标题住在车站旅馆——她会回到执行给定8月25-Sparks荣幸在著名的会议上没有先例南方文学在查塔努加。敦促的火花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作家多萝西埃里森,南方作家的奖学金这里还有给了她第一个奖在其twenty-four-year历史奖本质上只是为她创建的。“我认为明顿的精神我妈妈的女儿,每一个绝望的福音歌手在黑暗中我所听的夜晚,”她Allison在引文奖。“她的人是我的人,固执,惭愧,拒绝受羞辱,固执的,但真正的公义,和总是在最好的纯口语用的日常诗歌hard-used人们说自己的生活。她电话扬声器/词曲作者,这是一个温和的避免的范围和权力她口语。传记、散文家、讲故事、人种、性能的诗人,巴克舞者,和完成的骗子,这个演讲者/作曲家暴露她的家人和她的部落的世界。…她与杰宁斯合作,打开等艺术家Nanci格里菲斯和约翰Prine。她知道她是谁。”
然后,上个月,火花在背靠背的周末在纽约曼哈顿剧院源。节目在制片人安德鲁·莱文的要求下,他的作品包括最近大卫马梅的百老汇加速前进。公司飞行机器制作,生成新的百老汇音乐剧作品,之后看到火花在纽瓦克去年美术馆作为躲避诗节的一部分,他走近她关于发展中很难进行归类定义艺术进入生产阶段。她目前正在治疗。“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把我的角色/故事在更广泛的方向,”她说。
但火花自己都会告诉你,最好的方法经验的混合性能诗歌,音乐,和独白艺术活的特别在车站酒店等场所,在那里她和杰克逊把法术对人可能听到自己的亲戚,历史,和家庭秘密反映在她的作品。在音乐行拒绝创新的城市,即使它占据了领导的景观,火花可能是最原始的声音操作的周边国家。
“我呆在乡村音乐协会的成员,所以每年我可以画一个小盒子在年度最佳艺人和列出的名称写在明顿火花检查旁边,“马歇尔查普曼说。“她是,年复一年,最有趣。我觉得她是我妹妹。”
世界上也许没有人写过,或有利,对火花查普曼,她再三火花和恰当地描述为“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私生子和汉克·威廉姆斯。”她的声音,而且看起来它。“火花走在舞台上,”查普曼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花园和枪,“看起来像一些女人拐错了弯从田纳西州女士辅助会议在农村1950年前后,手里拿着一根骨头钱包包含只有上帝知道什么。”
 多年来,看起来已经进化。因为她的第一张唱片,2001年的Middlin的姐妹是她祖母的“情书”,火花用于执行穿着她祖母的衣服。现在她只穿裙子,祖母会批准的。适度的高领,他们都只是膝盖以下,和经常地绕在腰部的细皮带,其最小大小。
多年来,看起来已经进化。因为她的第一张唱片,2001年的Middlin的姐妹是她祖母的“情书”,火花用于执行穿着她祖母的衣服。现在她只穿裙子,祖母会批准的。适度的高领,他们都只是膝盖以下,和经常地绕在腰部的细皮带,其最小大小。
在舞台上她带着两个钱包,她最喜欢的属于她的祖母,在她将离开它的火花。还是充满了她的财产,“尘土飞扬的虽然他们可能。“火花有特别的亲和力为妇女的钱包,例证的块”她的钱包。”“我的母亲,”她说,“可以拿出画笔,紧凑,口红,一些多汁的水果口香糖,一个小吹风机,面巾纸,好运的七叶树,乳液,支票簿,一个钱包,方向代托纳海滩,佛罗里达州,塑料手铐,一个狗项圈,口琴,吨零钱,野营刀叉,继续。”
她让观众成员持有它,和她的钱包已经知道回到她失踪的事情。关于节目的火花忘了带钱包,杰克逊冷静地说:“你会认为她不能说没有它。“主要是火花,用一只手握着麦克风走近她的嘴,温柔的拳头与其他,并让钱包悬在她的手肘的骗子。“在我的家人,”她说,“女人的钱包从未失去人类接触。他们似乎禁止和神秘”。
,也可以描述火花出现在舞台上。她有完美的姿势和朗诵,风格的头发,干净的指甲,所有这些声音不合时宜的作家的专业是旧时代的南部农村家庭生活rail-whiskey, Bible-beating,美丽的肮脏。支持的但是她的天赋,她锋利的细节,往往压制任何怀疑人们对她的真实性。
台下,火花在谈吐、亲切。“我不能做这个工作没有妇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像马歇尔(Chapman)和多萝西埃里森,”她说。“这是支撑在我的社区的肩膀上。友谊是我的工作中心在世界上。人们给我他们的联系,因为我不是在那个世界。”
你的世界是什么?,我问。
“我是抚养孩子,”她说。“我去神学院,我是治疗师许多年来,和我教心理学13年。我以前大约一百个工作岗位。”
现在在她四十多岁后期,火花不“找工作”,直到她三十六岁。她写她所有的生活,和她的诗歌有一些小发布成功。(她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白色的闪电(托马斯·纳尔逊,2008)绝望的赎金[2007]托马斯·纳尔逊。)但直到1999年,当她开始表演与音乐,她发现了一个更广泛的观众对她的工作。“我希望站在自己的写作,”她说,“但是当你执行它,实际上就像8000其他层和音乐的情感。”
然而,她的作品的音乐性,即使没有音乐。她的写作告诉真相x射线说出真相的方式;没有隐藏。看内使一些人不舒服,但没有威慑的火花。你想象她的书桌上可能有一个以上符号,像从一个幸运饼,阅读,“舒服不舒服。”
除了火花不写在桌子上。“我用我的车,”她说,解释说,如果她试图写,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要走,我将使用我的电话短信自己指出的那样,像这一个。”她向我展示了一个神秘的,两个单词短信:奇迹冰棒。“我有小纸条无处不在,”她说。“当我写在我的车,我将我的女性亲属。我给它。我没那么伟大的作家。”她停顿了一下。“这不是像我莎莉麦克琳;“频道”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是我写的是给我的。”
然而,明顿火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占卜板,制造实验和家庭鬼魂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很难定义什么是她,没错。“我在做什么不是一个流派,”她说。“这里还有我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横跨音乐世界,但它是进化而来的。嗯,我不知道。让我想想。”她认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作曲家,就像我真的是一个作曲家。我不想要分开的音乐,因为,你知道,安妮·塞克斯顿乐队。”
 她解决“speaker-songwriter”,是和是不准确的。或者,更确切的说,她说她写歌,但她也更多。“他们的歌曲,”她澄清。“这不是一些爵士音乐奏你后面当你阅读。这是诗歌与音乐的谈话。“听她的四个专辑,包括记录在车站住酒店,就像开关从调频收音机。火花的不同频率。
她解决“speaker-songwriter”,是和是不准确的。或者,更确切的说,她说她写歌,但她也更多。“他们的歌曲,”她澄清。“这不是一些爵士音乐奏你后面当你阅读。这是诗歌与音乐的谈话。“听她的四个专辑,包括记录在车站住酒店,就像开关从调频收音机。火花的不同频率。
记住旧剧院规则,如果有人带枪在舞台上表现,引发的枪必须的节目吗?火花的话语选择如此精确,台词太紧,甚至被部分建立一个类似的紧张。诗人玛丽豪曾经这样形容一次“非常像,行驶在糟糕的冰,你你的车可以旋转时,就在慢慢地开始旋转。“这就是喜欢听明顿火花执行她的口语歌曲,唯一的区别是,火花冰面上的轮子和旋转的目的。诗她,一样熟练地狙击步枪射击,造成表面损伤她不感兴趣。或者,换句话说,肤浅的东西。
“女性在我的家人,”她说在车站酒店引进一个新的块,“我们没有参与缠足,但我们确实有一些stove-tying。”这首诗,激烈,家族之间的战争欲望对附件和自由,以母亲的口语词汇点缀着她的不言而喻的真实的内在的声音:
“你以为你是谁啊?”
女孩,别跑了,离开我,
“我应该在你混蛋一个结。”
-我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永远不会等于零。”
主-哦,孩子,请不要从我身边经过。
“Stove-tying”让人想起一些回忆录,由女性,探索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复杂的动态。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后给我翻阅本维维安Gornick回忆录激烈的附件,直到我来到这段关于她母亲:“她没有明白上学意味着我将开始思考:条理清楚地和大声。她被暴力惊喜…。“你在说什么?“她会喊我。“你在说什么?请说英语!我们都说英语在这所房子里。说它!”她的反应震惊了我。我没有得到它。 Wasn’t she pleased I could say something she didn’t understand?”
Gornick的书,女儿的愧疚让她有权返回失败她母亲的束缚,他们的整个生活。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解决母女债券的回忆录中,卡洛琳凯Steedman等一个好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很容易死亡。火花,如饥似渴地妇女研究非常感兴趣,解包女性亲属之间的关系以类似的方式,利用音乐和更少的单词。在她的工作和谈话,她传达了深开车去探索创新,音乐形式可以捕获真理却只是她自己的真理,但母亲的女儿,姐妹,阿姨,老朋友。她带来了同情和幽默,最重要的是,她生活主题。
另一块”,填补了她,“告诉从女儿的角度,描述了“妈妈”在一个加油站工作。充满性暗示和混乱,它关闭这些线:
上帝知道她是玩火。
多年来,我燃烧
跟我学
孟菲斯市郊的。
一个年轻的女孩不能理解
一个女人知道。
在谈话中,我告诉她我的曾祖母曾经说过:“女人只能有三个四件事:婚姻,事业,孩子,和自己。”我问火花如果她是她自己的生活中发现这是真的。“嗯,我完全是一个妈妈,”她回答。“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会说些什么,但这是我的主要焦点。和写作。所以他们都在。我认为这是如此重要的找到你的工作。我妈妈没有发现她工作,我只是看。它是如此重要。”她提到她的丈夫和十几岁的孩子的支持。
 “我的故事都是关于妇女和救赎,“火花说。“我在我的第五个记录和我不能做同样的事情。我的节目总是改变,因为它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年长的故事我还告诉仍然觉得治愈的故事。我做了大量的个人治疗工作,我离做。“加上人们叫她分享自己的故事,常常前缀,“你不会相信这一点。”
“我的故事都是关于妇女和救赎,“火花说。“我在我的第五个记录和我不能做同样的事情。我的节目总是改变,因为它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年长的故事我还告诉仍然觉得治愈的故事。我做了大量的个人治疗工作,我离做。“加上人们叫她分享自己的故事,常常前缀,“你不会相信这一点。”
台上站客栈,火花穿着below-knee-length粉彩花的裙子,和她的浅棕色的头发卷曲在她的脸。她旁边坐着吉他手杰克逊。火花形容杰克逊的伴奏是微妙的,它是,因为听到她almost-songs从来没有调到的嗡嗡声或其他任何困在你的头比她的歌词。但是音乐本身的工作在不同的层面上,在融化你,使你听到和接收的话。后和她七年的表演,”杰克逊说,最好的伴奏者与鲍勃·迪伦的作品包括工作,谢尔比琳,和露辛达威廉姆斯,“我可以说没有人做任何接近我们所做的,和她是最好的。”(现在有collaborator-complementary和免费。)”我试图做的,”他说,“是设置的情绪提高她讲述的故事。“他的演奏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潜台词火花的叙述,更令人紧张的是,幽默,黑暗中,她在房间里蔓延。
Middlin的姐妹都是关于她家庭的女性,特别是火花的祖母和她的姐妹们。她随后的专辑有开采相同的领土,令人惊讶的是新鲜的结果。“我不写信给任何人,”她解释说。“我写信给我的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历史记录。“她的一些作品,她不能相信她的表现在公众面前,但她决定写他们好像没有人会听到。
“家庭生活最终会过去,”她说,“但是我将写我的余生。“胳膊休息一会儿在金属表,但是他们不呆在那里的时间比几秒钟。这并不是说她与她的手,但她似乎总是移动。她坐。她向后靠了靠。“我不知道如果我永远是表演,”她若有所思地说,“因为你无法控制人们是否想见到你。也许我会做邻居。“一两分钟,她引导谈话对我当我试图引导它回来给她。但在这场比赛中我没有祷告。我坐在对面的人磨练上浆的艺术人目光,转移他人的好奇心而自己冷静的目光静静地文件信息。
她看起来我的眼睛和微笑。“你的故事是什么?”
标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