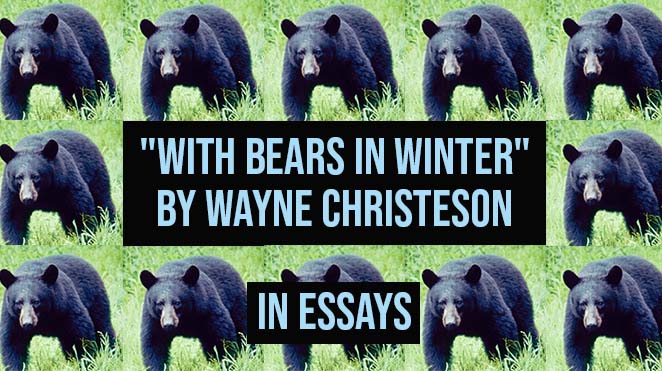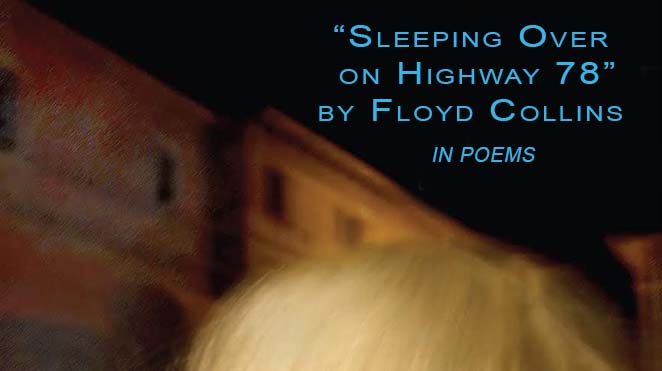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奴隶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维恩塞克(Henry Wiencek)写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就此打住,因为悖论可以提供一种令人欣慰的道德假死状态。”Wiencek含蓄地指出,我们怎么能援引开国元勋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时代,而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奴隶主,甚至那些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人也容忍奴隶制?这种矛盾在我们对托马斯·杰斐逊的崇敬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同时是这个年轻国家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最伟大的自由捍卫者,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实践者,杰斐逊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可恶的商业”和“恐怖的集合”。与山之主, Wiencek提供了一个及时而令人不安的描述,描述了杰斐逊——这位最常被称为新世界“指导精神”的国父——如何将他在《独立宣言》早期草案中提到的一个机构的终身实践合理化,称其为“一场针对人性本身的残酷战争,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权利”。
维塞克以蒙蒂塞洛的形象开始了他对托马斯·杰斐逊参与奴隶贸易的描述,这座庞大的豪宅坐落在山顶上,“就像柏拉图式的房子:一个存在于缥缈领域的完美创造,实际上是在云层之上。”他将这一形象与彼得·福塞特(Peter Fossett)的故事放在一起,彼得·福塞特是赫明斯家族的后裔,他是杰斐逊最受宠爱的奴隶。(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么是杰斐逊妻子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要么——据说——是杰斐逊自己的后代。)福塞特后来写道,作为海明斯家族的一员,“我们不需要知道自己是奴隶。”后来杰斐逊去世了,11岁的彼得、他的母亲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在蒙蒂塞洛被长期解散的过程中走上了绞刑台,这是由于杰斐逊留给女儿玛莎的巨额债务。尽管福塞特最终被“夏洛茨维尔的某些人”买断了奴隶身份,但他又被奴役了24年,用维恩塞克的话来说,这证明了“蒙蒂塞洛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幻象”,当山之主不再在那里支持它时,它被粉碎了。
 蒙蒂塞洛是维塞克新研究的中心主题,他研究了杰斐逊对奴隶制制度矛盾演变的态度。这所房子本身似乎就是为了帮助杰斐逊向他的来访者隐藏令人不安的真相——或者,甚至是对他自己。在蒙蒂塞洛设计的众多巧妙特征中,有隧道和旋转门,使他的奴隶们能够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运输食物、饮料和其他物资进出房子。桑树街,一条由小屋组成的长巷,构成了这个小村庄的“主街”,住着大约600名奴隶,坐落在豪宅附近,但从窗户看不见。然而,奴隶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每天早上在屋顶露台上来回踱步,“一个非常壮观的身影映衬着他豪宅宏伟的建筑特色。”
蒙蒂塞洛是维塞克新研究的中心主题,他研究了杰斐逊对奴隶制制度矛盾演变的态度。这所房子本身似乎就是为了帮助杰斐逊向他的来访者隐藏令人不安的真相——或者,甚至是对他自己。在蒙蒂塞洛设计的众多巧妙特征中,有隧道和旋转门,使他的奴隶们能够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运输食物、饮料和其他物资进出房子。桑树街,一条由小屋组成的长巷,构成了这个小村庄的“主街”,住着大约600名奴隶,坐落在豪宅附近,但从窗户看不见。然而,奴隶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每天早上在屋顶露台上来回踱步,“一个非常壮观的身影映衬着他豪宅宏伟的建筑特色。”
亨利·维恩塞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揭穿这样一种观念,即杰斐逊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人”,他不情愿地参与奴隶贸易。利用各种文献和以前出版过的传记,维塞克构建了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在年轻时感受到奴隶制的残暴,但当他发现自己可以很容易地从中获利时,他就接受了这种做法。直到1774年,维泽克写道,杰斐逊“不仅为奴隶设想了自由,而且还设想了他们的‘选举权’,将他们纳入公民行列。”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他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建议奴隶制是“未来的投资策略”,并在写给开国元勋中唯一解放自己奴隶的奴隶主乔治·华盛顿的信中吹嘘,他每年从出售奴隶的孩子中获得4%的利润。维泽克写道,杰斐逊的商业计划“威胁到一种令人宽慰的观念,即他对自己在做什么没有真正的意识,他被‘困’在奴隶制度中,这是一种过时的、无利可图的、沉重的遗产。”
Wiencek还费力地解构了杰斐逊的作品中臭名昭著的段落关于弗吉尼亚州的注释(维切克称之为“每一位杰斐逊传记作者迟早都要试图穿越的阴暗沼泽”),杰斐逊在书中生动而令人作呕地论证了非洲人的劣等性。长期以来,这些段落一直被辩护为,从上下文来看不那么冒犯,而且是为了改善新生美国的形象而提出的一种修辞(可能是不真诚的)论点,主要是针对对一个同时颂扬自由和实行压迫的新国家持怀疑态度的法国观众。但是根据Wiencek早期的揭露,杰斐逊令人作呕的结论显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他深爱但有缺陷的祖国的务实的辩护,而是对这位伟人真实信仰的真诚表达。
 山之主甚至剥夺了杰斐逊“时代人物”的辩护。即使在他的同僚中,杰斐逊也不合拍。根据Wiencik的研究,就在杰斐逊为奴隶制在新世界暂时延续而撰写文章的同时,许多弗吉尼亚人——尤其是乔治·梅森——正在积极地为旧自治领奴隶制的终结而努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杰斐逊打破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构建了一种黑人作为他者的形象,一种在美国社会中没有地位的存在,”维泽克写道。“杰斐逊给奴隶主的合理化披上了学术的外衣,使自己成为反动派的理论家和发言人。”
山之主甚至剥夺了杰斐逊“时代人物”的辩护。即使在他的同僚中,杰斐逊也不合拍。根据Wiencik的研究,就在杰斐逊为奴隶制在新世界暂时延续而撰写文章的同时,许多弗吉尼亚人——尤其是乔治·梅森——正在积极地为旧自治领奴隶制的终结而努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杰斐逊打破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构建了一种黑人作为他者的形象,一种在美国社会中没有地位的存在,”维泽克写道。“杰斐逊给奴隶主的合理化披上了学术的外衣,使自己成为反动派的理论家和发言人。”
维泽克对杰斐逊与他的奴隶之间的情色历史的描写比预期的要少:即他与私人女仆莎莉·海明的关系——这是一部复杂的杰斐逊传记中长期存在争议但现在或多或少被接受的方面。维泽克拒绝了这位辩护者的论点,即杰斐逊奴役奴隶,并为奴隶制辩护,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与莎莉·海明斯的不正当恋情。维泽克认为,事实远比这令人不快。历史记录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流行的观点,即杰斐逊和莎莉·海明斯是恋人,他们被禁止的结合被奴隶制掩盖了;相反,莎莉·海明斯似乎为了他们的后代抵押了自己的生命。“她每天都打扫他的卧室,”Wiencek写道。“他们的儿子麦迪逊每天都在数着他离开那个地方和那个人的日子,他的父亲是奴隶主和奴隶。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当这段令人遗憾的历史呈现在公众面前时,杰斐逊的声望上升了——因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一直希望杰斐逊不可改变的象征作用是他使奴隶制安全。”
尽管Wiencek的大部分论述基本上都是谴责的语气,但他似乎并不打算损害杰斐逊的声誉,而是想要爆炸我们自己naïve的冲动,要么从我们对他的叙述中忽略他个人历史中更令人讨厌的方面,要么将它们合理化,就像杰斐逊为他持续的道德违法行为合理化一样。最后,杰斐逊似乎只是另一个好人,被他自己认为是必要的东西毁掉了,但实际上,那是自满和贪婪。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杰斐逊(而不是华盛顿)是革命时代伟大的道德典范,Wiencek观察到这一奇怪的事实,他认为华盛顿晚年对奴隶制的拒绝,使他在功利主义和道德模糊的未来中不那么有吸引力。“华盛顿解放奴隶的行为不是对他那个时代的致敬,而是对他那个时代的谴责,”维泽克写道,“他宣称,如果你声称自己有原则,你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维恩塞克认为,人们始终需要将杰斐逊的才华横溢、但却存在严重缺陷的人生放在一边,这既是他的耻辱,也是我们的耻辱。
Henry Wiencek将会讨论山的主人: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奴隶在纳什维尔的南方书香节10月12日下午2点,在立法广场12号教室。所有节日活动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标记:非小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