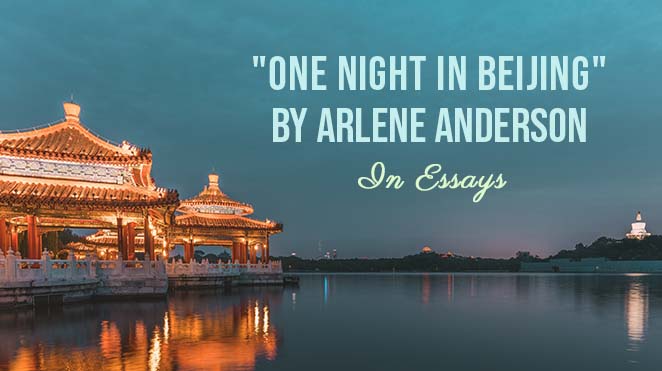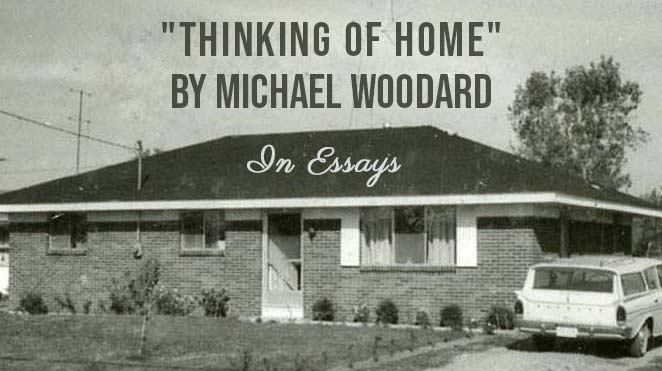我在纳什维尔长大,一直在努力寻找成为作家和读者的道路。这些年来,南方书节给了我很多礼物。有的我马上撕开,有的似乎在自己甜蜜的时候打开了。那年10月的第二个周末,我来到立法广场,那年我17岁。那时,我已经花了大半生的时间在涂鸦上,但我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我以一种即兴的、随意的方式阅读小说和诗歌——本能地在戴维斯-基德书店的过道里穿行,翻阅我上大学的哥哥留在房间里的诺顿选集。那些作家看起来就像那本选集薄薄的书页一样遥不可及,毫无形体。大多数人早已去世,那些没有死的人住在像纽约这样的大而复杂的城镇——这些城市让人感觉像“伟大的彼岸”一样遥不可及、令人生畏。无论他们的作品多么发自内心,多么激动人心,作家们的思想始终是静态的、抽象的。
_0.jpg) 有一年,奇迹般地,我的高中开设了一门创意写作课。我们的老师,既体贴又有创造力,让我们离开课堂半天,赢得了英雄的分数。她带我们去市中心参加南方书节。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情景。三位有血有肉的、会走路的、会说话的诗人在诵读前站在各自的位置上。我惊呆了:诗人真的存在。当他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他们赋予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写作是你可以学习的东西,写作是你可以走的一条真正的道路。就在我面前的是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现在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小镇。
有一年,奇迹般地,我的高中开设了一门创意写作课。我们的老师,既体贴又有创造力,让我们离开课堂半天,赢得了英雄的分数。她带我们去市中心参加南方书节。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情景。三位有血有肉的、会走路的、会说话的诗人在诵读前站在各自的位置上。我惊呆了:诗人真的存在。当他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他们赋予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写作是你可以学习的东西,写作是你可以走的一条真正的道路。就在我面前的是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现在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小镇。
有一年我在大学里浏览节日帐篷时,我拿起了一本牛津美语这本杂志我以前从未读过。我坐在战争纪念碑的台阶上,开始阅读。那时,我已经爱上了尤多拉·韦尔蒂、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和弗兰纳里·奥康纳。我爱他们,因为他们的文学力量,也因为他们向我展示了我最熟悉的世界——南方——是文学的沃土。但是在牛津美语,我认出了一种不同的亲缘关系。第一次,我所看到的我的南方,以其迅速变化的面孔和持久的陌生,回望着我的印刷。我查了一下节日的日程安排,发现下一节有杂志上的一位作家在看书。我从台阶上爬起来,向国会大厦走去。
2010年,我参加了书展,当时我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快写完了。我已经走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十字路口,这可能会发生在一份草稿上。你喜欢每一个角色。你已经有了叙事的声音。人们说他们喜欢你最后给他们看的那几页。但你内心知道这不是小说。在你写的那些可爱的书页里,没有故事。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听汤姆·富兰克林读取歪字母,歪字母也许是得出这个可怕结论的最佳时机。当然,我的喉咙嘶哑了。我测量了到最近的紧急出口的距离。但富兰克林把你拉进他编造的故事的天赋是不可否认的。我别无选择,只能听。第二年夏天,当我看到富兰克林将在一个由牛津美语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怀疑他的教学将与他的小说已经向我展示的东西相呼应:角色可能有迷人的内心生活,但迟早,他们必须站起来做点什么。
我还记得几年前另一个不安的十月。当时我23岁,对我的小说可能走向的方向感到焦虑,埋头申请艺术硕士课程。我记得我跌进了理查德博士伦的阅读。在问答环节,鲍许向房间里的作家们讲话,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写作是一种值得我们度过一生的方式。他鼓励我们只把精力集中在今天的工作上,别想别的。我的肩膀放松了。我注意到我周围很多人的肩膀也是这样。十年后,我成了他的学生塞瓦尼作家会议.我听到他提出同样的忠告,语气同样坚定。我的肩膀又松了下来,我环视了一下桌子,我的同学们都在听他的话。想象着我们所有人回到家,重新专注于我们的工作,我会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个节日,对我认识的所有有血有肉的作家充满了惊叹和感激。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些会走路、会说话、有血有肉的作家,这个周末和我一起吧。在我还不知道有作家生活在我身边之前,这个节日就为我召唤出了他们,这是一个由帐篷和魔法组成的三环文学奇迹。多年后,它仍然拥有迷人的力量。我希望你能去战争纪念广场和那几排帐篷由小出版社、书店和文学杂志经营。我希望你能亲眼目睹你所钦佩的作家——还有一些你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冒险表演他们自己的高空走钢丝。到周末结束时,我敢打赌你会准备好离家出走,加入他们。

艾米丽·乔特拥有莎拉·劳伦斯学院的艺术硕士学位,她的作品曾出现在Yemassee而且田纳西州库即将在《佛罗里达评论》.她住在家乡纳什维尔,在那里她正在写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