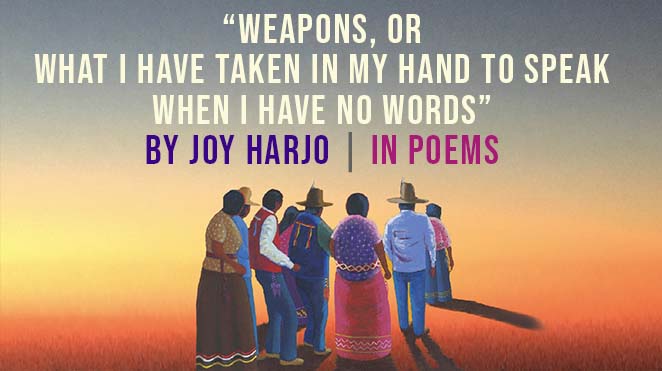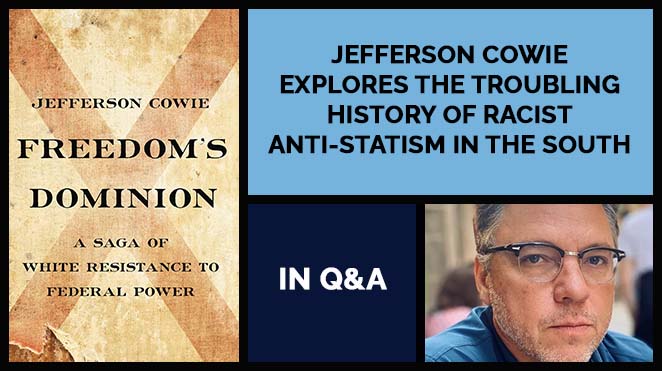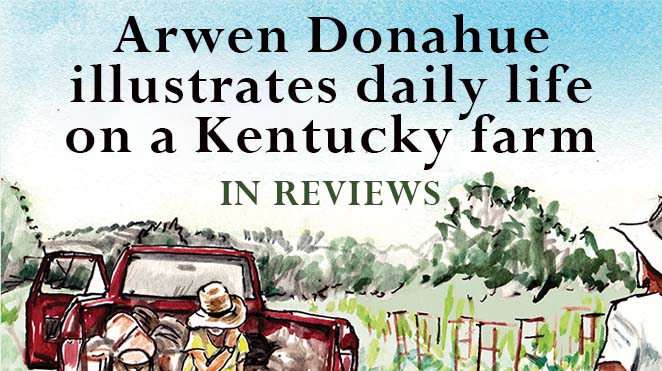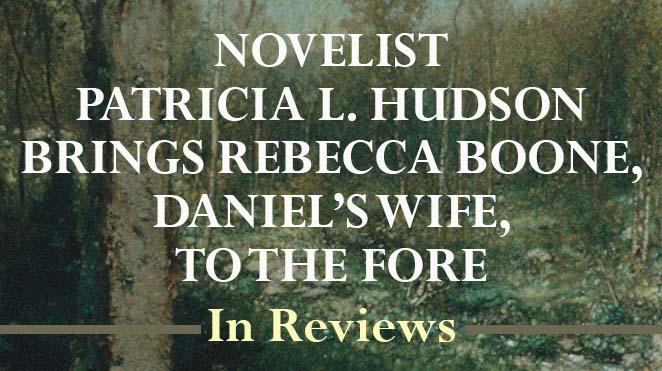在她的最新系列中,在我儿子康复的几个月里在美国,诗人凯特•丹尼尔斯(Kate Daniels)调查了成瘾的难题,这一困扰似乎和人类一样古老,但却不断让我们再次困惑。丹尼尔斯之前已经出版了四部广受好评的诗集,她从自己滥用药物的经历中写下了这些——不是作为一个瘾君子,而是作为一个深受家庭成员毒瘾影响的人。
 尽管通过这些诗说话的女人不是丹尼尔斯本人,但她面临着丹尼尔斯所知道的同样的困境:你如何帮助你所爱的人,而不被卷入他疾病的毁灭性漩涡?与此同时,丹尼尔斯的叙述者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引导着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化。
尽管通过这些诗说话的女人不是丹尼尔斯本人,但她面临着丹尼尔斯所知道的同样的困境:你如何帮助你所爱的人,而不被卷入他疾病的毁灭性漩涡?与此同时,丹尼尔斯的叙述者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引导着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化。
的诗歌选集在我儿子康复的几个月里已由公牛城出版社出版三个音节描述成瘾这本手册包括匿名戒酒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和其他康复计划中熟悉的“十二步”(Twelve Steps)。丹尼尔斯他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埃德温·米姆斯英语教授和创意写作主任,在纳什维尔和其他地方举办了“为恢复而写作”社区研讨会。她回答了来自米兰通过电子邮件。
米兰:在我儿子康复的几个月里关注的是一位母亲对孩子上瘾的经历,但它也是一部关于衰老的文集,也是一部试图与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损失达成和解的文集。你能谈谈这两个主题在你的书中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吗?
凯特丹尼尔斯:在最普遍的层面上,我想这两个主题都是关于失去的,不是吗?当然,就像你说的,衰老。但是上瘾也一样。即使你上瘾的爱人没有死于痛苦,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也总会有损失:失去信任,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失去希望和潜力,失去健康,失去关系,失去相互爱和关心某人的情感亲密。上瘾使人们远离自己,也使他们与爱他们的人分离,从而扼杀了互动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逃避、失去和拒绝的循环,一次又一次。
当然,变老似乎几乎完全意味着失去:身体崩溃、精神衰退、朋友和家人的离世、失去我们可能努力获得却又不愿摆脱的早期身份。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发现变老是令人痛苦的,但它也有点引人入胜。这是最可预测的,clichéd的东西,也是全新的。你的一生都在攀登一座山,朝着一个遥远的目标前进。(至少我60岁之前的生活是这样的。)也许当你真正到达顶峰时,你会注意到,但我认为很多人太忙了,他们没有注意到,然后突然之间,攀登结束了,他们在往下走!“因为我不能为死亡而停下,”艾米丽·狄金森说,“他好心地为我停下——/车厢里只有我们/和永生。”
也许这很奇怪,但我发现这个新的视角在各个方面都很吸引人。有时我觉得自己从五岁起就是个小老太太了,一辈子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一方面,变老似乎是一件惬意而诱人的事——没完没了地喝茶、读书,而且(一旦我在四年后退休)不用对别人那么负责,我的时间都被大学占据了。作为一个女人,不再受交配游戏的控制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不再觉得自己有多“有吸引力”是基于他人评价的外部标准。
另一方面,你爱的人因死亡或痴呆而消失是非常可怕的。没办法。不断有人失踪。点名时间越来越短了。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的团队或群体——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与我共度一生的爱人,以及那些可以被称为同行者的人(对我来说,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诗人,以及我们前面的那一代作家)——正在一个月一个月地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简,这个过程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是无情的,不能以任何方式逆转或改进。
真的,那太糟糕了。另一方面,我继续被情感上的韧性和精神上的坚忍所吸引。人类是如何度过必须要度过的难关的?为什么有些人直接面对挑战,而另一些人似乎不能胜任任务,或不够坚强?我的小弟弟在49岁时死于严重的酗酒。为什么对他来说是这样?为什么他不能熬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十二步康复法将酒精中毒和成瘾视为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疾病以上瘾的脑化学有机形式在身体上表现出来,并由此而来的所有生活破坏。治疗需要医疗、精神和心理干预。 I totally agree.
在我看来,任何形式的上瘾都是一种保护自己不受痛苦的尝试——尽管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孩子的神奇想法。可悲的是,我的原生家庭里到处都是沉迷于各种瘾的人,他们无法聚集足够的资源来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快乐”或“玩乐”。任何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肯定会感到失望。对一些人来说,酒精和毒品似乎暂时带走了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不适感,把他们置于一个“快乐的地方”。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需要它。谁知道为什么?我试着不去管它。否则,我就会想个没完。
 米兰:成瘾是大量社会、医学和政治话语的主题。在一片嘈杂声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很困难?
米兰:成瘾是大量社会、医学和政治话语的主题。在一片嘈杂声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很困难?
丹尼尔斯:多么有趣的问题啊!直到现在我才想到这一点。谢谢你问这个问题。你是对的:目前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关于阿片类药物流行的“闲言碎语”。对我来说,主要的“文本”是我内心的对话(这是如此可怕,我几乎在可能的时候关掉它),我在我经常参加的十二步会议上听到的内容,以及我在媒体和教育材料上读到的与成瘾有关的内容。两年后,当我终于能够写诗时,所有这些都最终为我的诗提供了素材。
我想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不同来源之间的冲突。因为我是一个叙事诗人,我习惯于将信息融入诗歌,并获取不同的来源:我自己的第一人称声音在我的诗歌中与研究过的事实或其他角色的叙述一样重要。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我每天都写点东西,并不总是写诗,但总是为了倾听自己,寻找自己,与自己接触而写作。
面对如此深刻的痛苦和精神错乱的生活状况,如果我没有写诗来处理它,读别人写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诗,并大声与有类似情况的人分享我的想法,无论是在写作工作室还是在十二步小组,我想我根本无法说话。我也马上开始了心理治疗。我想这是另一种吵闹的声音。
所以,是的:开始写这方面的东西确实很难。有好几年我都不能写这事。我确实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东西,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在日记里写的东西时,我非常害怕,身体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我开始颤抖和哭泣。我在不知不觉中就知道情况有多糟,实在无法忍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能活在当下,继续呼吸、吃饭、睡觉、开车、教我的学生。我花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多时间,才忍受得了主题的重压,真正开始写诗。
米兰:公牛城出版社的合集,三个音节描述成瘾,是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诗歌集中关注上瘾。你总是把这些诗想象成一个统一的集合吗?那个写书计划是怎么来的?
丹尼尔斯:三个音节描述成瘾是一本诗集——很短,我想只有十六首诗。这发生在整本书的手稿已经被接受之后。我开始教授康复写作课程门廊(我现在还在做这件事)以及在纳什维尔以外的地方,当我四处旅行的时候,我做了阅读。我突然想到,当我和那些首先对恢复感兴趣的团体(而不是那些主要以作家为身份的人)一起工作时,如果有一本完全专注于恢复的简短合集,将会很有帮助。布尔城出版社对此很感兴趣,并且愿意在完整版出版之前立即出版。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很好心地同意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我能在这里介绍一下我将于六月底在科德角的普罗文斯敦的美术工作中心教授的写作和恢复讲习班吗?我希望能有田纳西人加入。这是一个度过一周的好地方,和一群作家和艺术家一起写作,并逃离田纳西州的炎热!顺便说一下,封面上的那篇三个音节是罗伯特·亨利的作品,他住在科德角,在美术工作中心教书。我就是这样发现他的。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家。
米兰:我怀疑有哪个年过五十的女人不会在《她野蛮的咆哮》(Her Barbaric Yawp)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它唤起了绝经后女性的所有悲伤和矛盾。你能告诉我们这首诗的起源吗?为什么你选择用它作为这本诗集的开篇?
丹尼尔斯:这首诗的起源非常古怪——也许有点恶心——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几十年。20世纪70年代,我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读大四,当时我和三个朋友去看一套校外公寓,我们想在来年租房住。它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的顶楼。它有四间大卧室,当我走进我想要的那间时——一间角落的房间,两面墙上都有窗户,天花板很高——我看得出来,住在里面的是一个我想结识的女人,我立刻感到与她团结一致。
我知道她叫格雷琴,看得出她穿着牛仔靴和热裤。读着她随身物品上的“文字”,看到凌乱的房间,还散落着润肤露和梳子,看到一架子来自我们现在称为第二波女权主义(当时我们只称其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热门中心的书,我对她产生了共鸣。她的遗物表明我们在为同一件事而战。
当我差点踩到一个随意扔在角落里的隔膜时,那种感觉变成了惊讶,它软软的、灰色的、没有洗过!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个时代一个相当体面的解放女性,但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被震惊了,我一下子意识到,要从社会强加的有关性别合适行为的观念中获得个人自由,我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
我以为我被“解放”了,因为我觉得我(足够)自由地进行婚外性行为并采取避孕措施。我也用了隔膜,但用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几乎是秘密的方式。把它藏在小塑料壳里直到最后一刻,在黑暗中最后一刻把它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来。还会偷偷地清洗,晾干,撒上粉只要说明书上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生效。这就是1973年20岁的我作为一名妇女解放斗士的意义。所以当我看到格雷琴完全不自觉的自由时,我有点被击垮了。
那个小小的戏剧性时刻——看着一个我想搬进去、想住进去的房间,首先感到与它的居住者团结一致,然后震惊地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陪伴了我近四十年。它把我向前颠了颠。这个自传体的时刻就是这首诗的起源。
至于用它来开篇,我决定整本书的重点应该放在标题中的女性主角身上,在我儿子康复的几个月里,而不是儿子的性格。毕竟,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从所爱之人的毒瘾所带来的附带伤害中恢复过来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关于酒精或毒瘾本身的故事。(比如卡瓦·阿克巴、谢丽尔·圣·日尔曼或尼克·弗林等作家的一些诗歌。)一开始我以为整本书会是关于上瘾和康复的诗。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让这个女人的主要角色在我们看到她被家庭中的毒瘾打倒之前,成为一个有自己权利的角色。我想在她的“问题”出现之前,让她成为一个有自己权利的人/角色。
原稿上还有一首诗,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不让我用,叫做《她的诗人Cento》。这是一首很长的被子诗,由79位女诗人的单句诗组成,她们的作品对我很重要。这是一首充满活力和女权主义的诗,我觉得它和《咆哮》很配但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对诗歌的合理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带有注释的俏皮笑话!-所以即使这首诗已经发表在约翰·霍彭塞勒的诗歌集会他们不会把它写进书里。
我对此感到遗憾,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诗歌一直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性别,女性的性别,尤其是女性团结的必要性。我写那首诗是为了向所有对我很重要的女诗人致敬。当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不让我用它的时候,我把厌食症诗放在了它的位置上——这是另一首关于性别问题的诗,我认为它有助于定义这本书的叙事角色。
 米兰:我被《无神论者厨房里的顿悟》打动了。这是来自精神体验前线的原始报道。选集中还有来自神学家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和深受毒瘾折磨的精神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的题词。你自己的精神关怀是如何塑造你的作品的?
米兰:我被《无神论者厨房里的顿悟》打动了。这是来自精神体验前线的原始报道。选集中还有来自神学家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和深受毒瘾折磨的精神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的题词。你自己的精神关怀是如何塑造你的作品的?
丹尼尔斯作为一个皈依天主教的成年人,我的精神关怀和宗教信仰一直是我诗歌和生活的中心。我生来就有信仰,它一直伴随着我。谁知道为什么?我尽量不花太多精力去想这其中的奥秘……我确实认为,我对人生意义的坚定信念,以及我对人生之初有一位仁慈的神的信念,自然地使我能够利用“十二步计划”——尽管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绊脚石。但我毫不费力地接受了“更高的力量”的概念,也毫不费力地接受了如何在所爱之人的毒瘾中明确地使用它,这种毒瘾是如此痛苦,以至于我以为自己会在这种痛苦中死去。我的信仰、我的朋友和十二步舞是帮助我度过难关的东西。
米兰:你清楚地表明,这些诗中的叙述者“与我自己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但这里的材料对你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在将个人经验转化为艺术的过程中,你的指导方针是什么?
丹尼尔斯:从我20多岁开始,当我开始极其认真地写作和出版诗歌时,我明白了我是在写自传(如果你想这么想的话,我的“缪斯”),我的参照框架和指南针就是家庭。我的家人。首先是我的原生家庭,然后是我通过婚姻和母亲身份建立的家庭。当然,我写的诗对我的家庭成员来说是痛苦的,我为他们感到痛苦而感到遗憾。但我从来没有为了“报复”任何人而写信,或者以报复的方式。(那些东西是留给我的心理医生办公室的!)
虽然我从来没有为了羞辱或揭露家里的任何人而写作,但我试着给自己无限的许可和尽可能多的自由去写一开始就出现的任何东西。但一旦我有了一份像样的草稿,我总是会问自己,我所写的东西是否属于我。如果是我的,我可以继续。如果我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挪用别人的经验,我就不能继续前进。我不会的。尽管这听起来很自负,但我总是在写我自己和我的经历,即使我的主题经常是我的家庭,即使我的诗里有来自我家庭的人物。
我写作的目的是试图解开家族关系的核心和人类亲缘关系中异常强大的纽带的某种神秘,以及人类心灵深处的裂缝、纠结和曲折。在我看来,诗歌不能被用来做坏事——如果你那样做,它只会变成诗歌化的宣传,这是诗歌的对立面。
对于这本特别的书,它的素材不仅对我来说是“热门”的,对我的家庭成员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同样受到了这种情况的影响。在寄出手稿之前,我先把它传阅给我的直系亲属,请他们要求修改或删除等等。有一些小的要求,但仅此而已。我很感激他们愿意在诗中表现自己,即使是间接地、匿名地。上瘾毕竟是“家庭疾病”,所以这既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读…的节选在我儿子康复的几个月里,点击在这里.]

玛丽亚·布朗宁是第五代田纳西人,在埃林和纳什维尔长大。她的作品已刊登在格尔尼卡,仍然,海马体,洛杉矶书评.她是杂志的总编辑米兰.